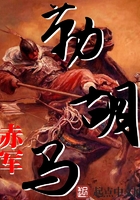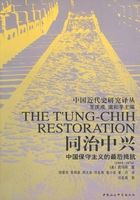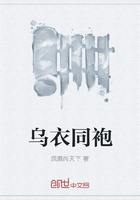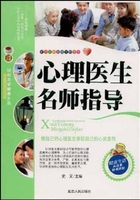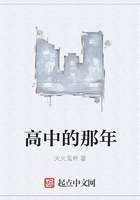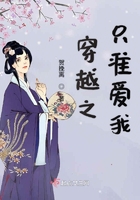情势的发展往往比人的预料要快,当皇帝和朝臣们还在盘算怎样息事宁人的时候,宫外的禁军将士似乎已经按捺不住。而永寿宫里,内侍宫监们的尖呼厉叫,一声盖过了一声,吵吵嚷嚷的都是“大事不好!禁军造反了!禁军造反了!大事不好了!……”,随着他们的疾奔飞跑,这凄厉张惶的声音响彻内廷里外,回旋荡漾在每个人的心上。
王守礼也在这时慌慌张张的跑回了悟道堂,他哭丧着脸,结结巴巴的说:乱军向城楼上胡乱放箭,要不是老奴腿脚快,差点就回不来了……
皇帝霍然起身,瞪圆了眼睛,惊怒交加:“乱兵果然真的想造反?南营呢?南营也跟着一同作乱?”
王守礼拼命点头,直着嗓子叫道:皇上,现如今守住丽景门最是要紧,贼兵要是进宫犯驾,那可是大事不妙……
座中朝臣们的脸色都有些惊疑不定,宪源说:请皇上早定大计,安抚人心,否则久拖必变,祸恐难测。
皇帝不敢迟疑,吩咐陆怀将内廷的侍卫都派到丽景门上去,又命王守礼聚集宫里的内侍,挑出其中身强力壮的,给他们配发刀枪剑矛,以拱卫后廷的各处紧要。
汪皇后没敢在景明楼多呆,这会儿也赶到悟道堂,顾不上定定神,喘会气,张口便说:臣妾敢请陛下御临丽景门,当此危难之际,皇上应设法安定军心……
皇帝怔了一怔,道:御临丽景门?
汪皇后说:皇上御丽景门,禁军将士得已叩见天颜,当不至于为非作歹,惹事生乱,而皇上亦可借此体察下情,俯允民意。
陈从圣立时附和道:娘娘所言极是。事态紧急,皇上宜明断。
皇帝沉吟了片刻,吩咐说:备驾,朕御临丽景门。王守礼,快将朕的武定甲取来,侍候朕更衣……
汪皇后却说:事急从速,皇上不必更换甲衣。妾身以为,士兵臣民朝见至尊,应当不至于无礼无状。
丑时刚过,皇帝领着朝臣终于站到丽景门上,城楼底下人山人海,黑压压的全是攒动着的人头,皇帝默默的看着,头脑里油然想起了四月十六日皇后千秋节时的热闹场面,那时节的升平景象,赏心乐事,至今犹在眼前,然而时过境迁,好景不再,当皇帝再次登临其上,触目所见全是这些乱军和暴民。
“皇上驾到,军民人等噤声接驾……”随着司礼太监在城楼上敞亮的哟喝一声,数十位内侍训练有素的同声哟喝。
城楼底下这才慢慢安静了下来,人人都仰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皇帝。而皇帝这时候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城楼底下既没人跪拜磕首,也没人山呼万岁,有的只是一张张仰起的面孔,火光明灭,那一张张沉默坚毅的面孔,黑黝黝的一眼望不到头。
皇帝不习惯这样面对他的臣民,这些忤旨抗命的乱兵刁民,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有朝廷和王法么?
皇帝费力的咽下一口唾沫,冲着城楼下那仰起的一张张人脸说:朕已罢太宰之职,其罪朝廷自会议处,军民何故不肯散去?禁军诸将士身受国恩,却夜聚宫门,抗旨违命,究竟意欲何为?
汪皇后跟在皇上的身后,听到皇上冲口而出的这句话,心里直道一声“糟糕!”,但是皇上的话已经出口,皇后因此只能在背后扯动他的袖子。
忠义郡王宪源还算机灵,当即俯下身子对城楼下的军民说道:圣上在此,军民百姓目睹至尊天颜,若有事便可呈奏,无事自当散去。宫闱重地,向不许闲人窥探,或有呈奏,应由有司转呈。不过转年以来,江南叠遭水旱,百业凋敝,民生艰困,其或有愤怨不平之心,亦在所难免。今日之变,归根结底乃太宰周如乐措置无方,欺君误国所致,皇上现已洞察分明,对此已与严谴重责,并将其下狱治罪,不日朝廷将彰显其罪迹,诏告于天下。今日之事,罪在太宰,朝廷自有公论,军民言行或有不敬不当之处,实属情非得已,皇上亦感同身受,故特旨予以赦免宽大。至于禁军将士皇上除另给赏赐之外,亦将照金吾卫之例,加食双俸,以资养济。军民百姓如无呈奏,应即散去,不可持势逞强,陷自身于不忠不义、无礼无状之地。
城楼下一众人这时都应声大喊:请皇上诛国贼,除奸佞,安天下。太宰不死,国难未已。
皇帝见状,亦只能点头说:奸佞不死,国难未已,太宰负恩误国,罪不容赦,朕定当处置元凶首恶,以纾国难,以解众怒。
好说歹说,聚集在永寿宫外的军民百姓陆续有人散去,帝后群臣彼此相顾,绷紧的心弦至此方才稍松些许。然而定下神查点左右,朝臣皆在,独独不见了罢职待罪的太宰周如乐。
汪皇后说:莫非周相爷是去了体仁阁搬取救兵?唉,这时节,谁能够救得了谁!到是先稳住人心要紧!
皇帝阴沉着脸,默不作声,皇后还想说什么时,皇帝却一拂袍袖,当先下楼,汪皇后走了两步,却又回头,吩咐王守礼说:天亮之前一定要把相爷给找到……在这节骨眼上,少了他可不行!
踯躅在湖岸边的周如乐心中一片迷茫,仿佛误入歧途,找不到前途出路。太宰公明知自己终将难逃一死,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所以他始终下不了这个狠心。说来这都是时运不济,自己为相尚不足一年,便逢上这几桩烂事,偏还凑在一起,当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一死以谢天下。
所以当皇上驾往丽景门的时候,周如乐趁着宫中忙乱,悄悄退避在后,待出了悟道堂,他却不知道该往那儿去?永寿宫被乱军暴民围成了铁桶,宫里的人自然插翅也难飞,现在就算托庇于太后老菩萨,太后老菩萨也未必救得了他——乱军暴民指明要他的项上人头。
周如乐想保住自己的首级,至少他应当死得体面,身为皇太孙的曾外公,当今皇上的亲舅舅,他不想因此丢了颜面。
周如乐枯坐在湖岸边冥思苦想,自缢?跳楼?伏剑自吻?都不是什么好死法!忠臣孝子所不为……既然要死,他自然要死得其所,死得堂皇庄严!周如乐这时候忽然想到了投湖,投湖自沉,以谢君王,往昔有屈子,今日有周公,如果有人能够将古人今人相提并论的话,则未免不是他留在史上的最后一段佳话。
周如乐这样一想,便觉得死也不甚可怕,他试着向湖里迈出一步,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衣衫的下摆——这儿水浅,周如乐不快的皱起眉头,想换个地方蹈水,又一想还是算了,于是便又往前走了两步,湖水这下子漫进了官靴,水很凉,几乎凉透了他的心,而两行浊泪,不知什么时候顺着面颊滚滚流淌,他抹了一把泪,继续朝前走,湖水这时已经齐到了他的胸口,老泪纵横的周如乐叹息了一声,在齐胸深的湖水里站住了脚,他忍不住回头望着岸上的宫阙,心里百味杂陈,似有无限的留恋,这一刹那,他几乎不想死了,他要转身上岸,然而不等他从湖泥里拨足出来,脚下忽然一个趔趄,身子歪了一歪,跟着仰面后跌……他惊得直想喊叫,却因此呛了满口的水——越发心急慌忙,手舞足蹈,可是上面既抓不住,下面也踩不实,整个人浮浮沉沉,越是挣扎就越是陷入虚空——一片虚空,四周皆变得飘渺迷茫,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在虚空里飞逝,也最终被无边无垠的虚空吞噬……
宫里没人知道周相爷的去处,皇帝叫人搜索,内侍宫监把能够藏人的角落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仍是不见其踪迹。
天将明时,有人将太宰逃匿的消息泄露出去,位于宣和坊的太宰府第于是遭乱军暴民抢劫,这也是京中首遭洗劫的权门贵家,因为皇上已经降罪于周家,乱军无所顾忌,府里若有人稍敢阻拦,立予格杀,周家三百余口,由是死伤大半。昌国公周如喜的府第同在宣和坊,当下亦被波及,乱兵冲入之时,家丁奴仆呼爹叫娘,各自逃命。
韩夫人听得外面大呼小叫,心中情知不妙,摸黑起床后,不知往何处藏避,最后才慌不择路的一头钻进了茅房。她猫着身子、忍着秽气在里面躲了半晌,这其间甚至还有一颗人头滚落到自己的脚边,一股血腥气随之弥漫而来,中人欲呕,韩夫人紧紧的扣住自己的喉咙,把眼睛闭得死紧,而头脑里回旋着的全都是当年胡人攻入渔阳,胡兵血洗全城的骇人景象。
总算侥幸未让贼人给搜到,竖起耳朵听得茅房外鼎沸的人声渐去渐远,她才确信乱兵暴民这时已经散去,仅着单衣、赤着双脚的韩夫人悄悄出了后门,夹在满街的游民散勇当中,仓皇奔走至濡沫坊,急叩宁安公主的府门。
府门打开,韩夫人一头栽倒,顿时人事不知。嬷嬷们连拖带拉,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她掖进房里。
宁安公主这一夜都没睡,惊悉此事后,更是愁眉难展,半晌无言,保义夫人忙着去弄了些姜汤,赵钱氏拿出几件衣裳替她披上。韩夫人喝了几口姜汤,眼睛发直,惊魂依旧未定,身子也簌簌的抖个不停。保义夫人好言好语的抚慰了半天,韩夫人才象回过神魂,哇的一声嚎啕开来,哭得屋子里人人面色惨淡。
宁安公主白着脸说:这里呆不得,收拾东西咱们赶紧进宫去……
赵钱氏去叫管家,管家回说:眼下可走不得,满街都是乱兵流民,个个凶神恶煞……老奴听说宫里王娘娘家也遭抢了,所幸没有死人,而户部吴侍郎的夫人原想避到尼庵去,结果半道上给人污了身子,还有兵部张尚书的小姐,昨天被人劫走,到今天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唉,这都是谁造的孽!
太子妃周鸾这一夜也没有睡,自从皇后来过景明楼,储妃的伤心便一阵接着一阵,怎么都止不住,然而夜深人静,她也不敢大声哀泣,只能任由眼泪在脸上横七竖八的流淌,虽然最后她哭得象个泪人,但至始至终却是半点声音都未发出。
天刚放亮,极度不安的储妃便去了太后老菩萨的体仁阁,跟这宫里的所有人一样,她也不知道太宰的踪影去向,虽然心里老是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她现在宁愿相信,祖父是躲藏在体仁阁周太后的身边。而不管怎么说,她身为周家的女孙,无论如何都要去见太宰一面,祖父要是有什么叮咛嘱托,她好牢牢的记在心底。
周太后见到太子妃的时候,眼睛不由分说的就红了,但是周太后没有说话,只是拉起周鸾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揉抚,这可怜的没人疼惜的孩子!
周太后已经听说太宰不见了,她想不通这会儿他会去哪儿?然而当天光大亮的时候,周家遭劫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宫中。
太子妃听此凶耗,身子震颤,泪如雨下,周太后却有些发怔,她二弟不见了,她娘家也遭了浩劫,几乎就给抄家灭门,老天!这都是怎么了?这些无法无天的乱臣贼子怎么也不怕遭天打雷劈!
周太后一边流泪,一边使劲的跺脚,不想这时候忽然觉得一阵眩晕,天地似乎都在眼前旋转,两腿也发硬发麻,软的迈不开步子,想开口唤人,却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太子妃被周太后突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她眼睁睁看着周太后的脸色,先是由红转白继而由白转青,然后看着她的嘴巴歪向了一边,眉毛眼睛也变得高低不平,而她的口水正从嘴角源源不断的流溢出来。
“太后娘娘!”太子妃有些不敢置信,她抱住周太后摇摇欲坠的身子,声嘶力竭的发出一声声尖叫:太后娘娘!太后娘娘!
“不好了!太后娘娘快不行了!储妃娘娘也晕过去了!快、快、快去禀报皇上、皇后……传、传叫太医!”慌慌张张的侍女们这时都争先恐后的惊叫起来。
洗劫周府的其实不是已经溃乱成匪的北营禁军,而是奉旨诛贼的南营禁军。南营的禁军将士一直觉得自己亏了,象劫商铺、抄大户,抢库银,这些百年难遇的好事南营将士都没有参与,因此心里早憋着一股气,既然皇上亲口表态说,太宰负君误国,当与严惩!众人都盼着奸佞伏诛,悬首于宫门,然而不久宫里就传出周如乐畏罪而逃,不知去向,众情激愤,极待渲泻,于是座落在宣和坊的周府就成了众矢之的,墙倒众推。
陆正己和唐觉之本来无心去为难周家的妇孺老幼,只是乱军逞凶激勇,既难安抚又难弹压。况且连他们自己都被禁军扣为人质,除了随遇而安,勉力自保,也没有什么安邦定国的法子。而眼下乱象纷呈,越闹腾便越难收拾,然而眼前的乱局总不能任其延续,陆唐二人想到这里,心中不觉生出许多隐忧。
“舅父大人,乱成这样,当如何是好?”唐觉之忍不住出声相询。
陆正己神色凝重:局面危甚,你我须见机行事……
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都知道要见机行事,可怎么见机,又怎么行事?身在乱军之中,行止都不能自主,遑论什么见机行事了。唐觉之皱着眉头,说:要么把张参军、马都尉他们叫来问问,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想的?
陆正己点头道:也是。不妨听听他们的打算,咱们再作计较。
唐觉之这便让看护他们的军校去请张参军、马都尉他们。须臾,诸人皆到,张成义含笑拱手道:郡王和太师如今都想通了么?
唐觉之眼睛一翻,哼道:你们做下的事,与造反无异,趁着皇上宽大赦免,尚有机会改过自新。否则成乱臣贼子,为国所弃,为人所耻!
马都尉道:郡王此言差矣,咱们诛国贼,除奸佞,胸怀社稷,心系百姓,这若不是太宰祸国,何来今日之乱?禁军起事,乃是拨乱反正之举,所利在国在民,又何罪之有?
储都尉说:少说这些之乎者也的废话,事已经做了,不若一发做到底。咱们人微言轻,不足以成大事,所以尚需借重郡王和太师的人望……
陆太师厉声斥道:你们、你们果然立意造反?
张成义道:太师言重了。造反乃乱臣贼子所为,非我禁军将士所欲。只是今日事既然已经做了,便如开弓之箭再难回头,皇上所在的永寿宫如今困若孤城,金吾卫亦不足仗持,京师之乱,眼下唯有禁军能够平复,而禁军若安得京师,操持国政,皇上亦将莫之奈何,在外的许骠骑等人投鼠忌器,必不敢肆行妄为,此所谓天赐良机,郡王和太师应该早下决心,则南北两支禁军自然服膺听命,愿效犬马之劳。而郡王威高权重之时,禁军将士亦能借此博取功勋,荣宗耀祖,不枉此生为人。
钱都尉说:这都是禁军将士们的意思。周家势败,正是郡王起而行事的大好机会。这良机稍纵即逝,郡王何得推阻。
唐觉之迟疑未决,张成义却笑道:自古忠臣出于孝子,来人,去请老夫人出来。
唐觉之一惊:怎么家母也在军中?正迟疑时,陆太君已然从后堂出来,但见老太太满脸喜色,见到唐觉之后,便忙忙的说:吾儿既不为自己所想,亦当念及你那苦命的妹子、念及庆王……今日之事,乃上天眷顾我唐家,千让百忍,咱家终于捱到出头之日了!
陆太君这话正中唐觉之的心结,刚刚心乱如麻,到是没去想这其中的关节,如今陆太君一语道出自己久藏的心思,顿时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明媚。
所谓天命所归,其在天也在人,天既灭周氏,自当匡扶唐氏。唐氏虽甘为忠臣,不敢附伪附逆,然唐氏子孙却未尝不可以登大宝,临天下,外甥既立,舅家辅之,理固宜然,无可厚非。
唐觉之念想及此,浑身暖洋洋如沐春风,当即对张参军及诸都尉说:若天命归庆王,诸位出将入相,列位公卿,赢得封妻荫子,荣宗耀祖,自当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