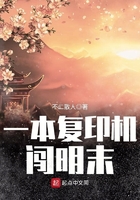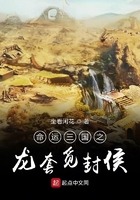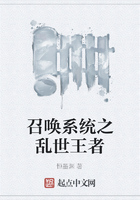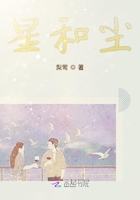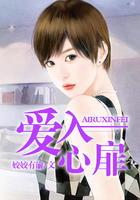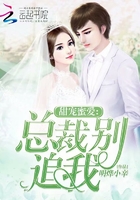上皇内禅,庆王登基,顺顺当当一气呵成,只是当这一切尘埃落地,唐太妃之母陆太君却总有一丝说不出来的微憾。外孙虽说做了皇帝,自己的女儿到底没有当成皇后,因而凡事只要往这上面一想,老太君心里就耿耿于怀的有些不大痛快。
在长庆宫的汪皇后病倒的时候,陆太君祷天祝地,眼巴巴的盼着她咽气,然而汪氏命硬,在床上躺了七八天,竟然就这么好了。而且陆太君还听说皇后汪氏生病的时候,太上皇亲自端汤侍药,恩爱之情可比得当年的贵人柳氏。为此,陆太君心里颇为生气,虽说子贵而母尊,但她女儿毕竟是孤零零的呆在永寿宫,相形之下,反到不比这失势的太上皇后过得快活。
陆太君一时奈何长庆宫的二圣不得,所以就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太上皇跟前的妃嫔身上,她希望能从她们身上得到几分补偿,她也要让她们知道,除了长庆宫的二圣,永寿宫的当今圣母娘娘同样是高高在上、忽略不得的。
近侍们出主意说,太妃娘娘从前即是仅次于皇后一等的皇贵妃,身份上早就高过她们,现在则是永寿宫唯我独尊的圣母娘娘,将来更要成为与长庆宫并驾齐驱的皇太后,所以后宫的妃嫔应该象以前到体仁阁朝见慈圣太后一样来朝见圣母娘娘,这样她们才能明白宫里的尊卑长上,才知道拿出恭敬之心来侍候娘娘……
陆太君采纳了这个主意,于是寿妃以下及至宁妃都要到永寿宫来朝贺圣母太妃,这其中还特别点出了宁妃王氏的大名,你王宁妃平素不是持恩仗宠,目空一切的么?这下看你还怎么骄横!
圣母隆熹太妃的这次宣召自然不是象从前那样一团和气的下贴子,而是径自派出身边的近侍内使去往长庆宫降下了口谕。
王宁妃跟永寿宫的唐太妃素来不投机,接了口谕便有些愁眉苦脸,明知此行去不得,却又不敢不去。左思右想,只得去找陈康妃讨主意。
陈康妃安慰她说:去是肯定要去,她要是给你气受,你可千万陪笑脸装小心的忍着,忍一忍就都过去了,难不成她还会吃了你?
王宁妃连声叹息:这老天偏是不长眼睛,越是小人就越是得志猖狂,真真气死我了!
陈康妃说:就算生气那也轮不到你,皇后和太子这一次才是倒足了大楣,还有出了家的周储妃呢,却也没你这般气性大!我听说这次连福妃都要去永寿宫朝见呢。
王宁妃不屑道:靠山倒了,这不是急着要再找一个,说不定,她这一去就不回来了,留在永寿宫里侍候新主子,贵妃娘娘不秃不癞,正好可以卖弄她的梳头手艺……
陈康妃吃吃一笑:她还在月子里呢,也不怕受了风寒?再说儿子都没了,再怎么讨好也是白搭,难不成太上皇愿意跟她再生一个?
王宁妃一撇嘴,说:受点风寒算什么?赶着去讨好献媚才是紧要!抱不住旁人的大腿,她心里总归不踏实!
王宁妃说得还真是准,那张福妃尚在月子里,本来已经免了她的朝见,但是张福妃死活都要来,劝也劝不住,因此也就和寿妃宁妃她们一起来了。
永寿宫的唐太妃原来是跟皇帝一起住在清凉殿,但为了显示自家的尊贵,特地搬到周太后住过的体仁阁召见她们。陆太君更是吩咐下去,待妃嫔们来至山下时,除了张福妃,其它人一律不许乘轿坐辇,得自行举步上山入阁朝参。
张福妃这一天似乎心情大好,她穿着后宫朝会时的礼服,插戴满头的珠翠,黛眉红唇,双颊还点染了些许胭脂。陆太君替她安排好的辇轿不坐,偏偏要和寿妃康妃她们一道登阶而上,一路上即使是面对王宁妃的冷嘲热讽,她也充耳不闻,安之若素。
后宫的妃嫔虽觉得张福妃今天的行为举止有些怪异,但谁也不承想,她今天竟是有备而来。她那行动生风的宽袍大袖里面居然藏了一把磨得锋利的剪刀,趁着诸妃低头向圣母娘娘请安拜贺,而唐太妃晗首赐张福妃独座的时候,这个张福妃忽然冲上去行剌。
当时的情形把吴寿妃陈康妃她们都给吓傻了,王宁妃虽说没被吓傻,却也目瞪口呆,“嗬嗬嗬”的挥手直叫。
太妃娘娘跟前的侍从尽管都围上来护驾,但是张福妃的气力大的惊人,她手中的剪刀在空中乱挥乱舞,口里发出的叫声尖利急促。“还我儿子的命来!你们还我儿子的命来!”
张福妃举止言行就跟疯了似的,挥舞着剪刀,见一个戳一个,内侍们畏首畏尾的近不得她的身。陆太君想挡在太妃娘娘的面前,结果也吃了她几剪,身上接连扎出四五个血洞,当即一声闷哼,摔倒地上。但看着张福妃将要逼近太妃座前,陆太君情急之下,双手死命抱住了张福妃的腿脚,扯着嗓子,杀猪似的急叫:快,快拦住这个贱人,杀、杀、杀了她!
张福妃听了这话,淬口唾沫在她脸上,恶狠狠的说道:“都是你们母子干下的好事!快快还我儿子的命来!”操起剪刀往她的手上猛地一戳,随后再大力拨起。陆太君吃痛不过,一声惨呼,晕厥过去,张福妃顺势踢了她几脚,犹不解恨,扬着剪刀怒叱:老不死的贼婆子,是你害死我儿子,今天我先弄死你这个害人精!
说时一剪刀便要往她的咽喉处落下,吴寿妃这时却从惊骇之中回过神来,当先一把揪住张福妃的发髻,将她的身子拖得后仰,口中急急叫道:我捉住她了,娘娘到是快跑啊!
唐太妃也省过神,双泪交流,跺着脚道:母亲,母亲……
殿中的内侍都仓惶奔过来,一边搀扶卫护圣母娘娘,一边去抢夺张福妃手中的凶器,而张福妃死命的想要挣脱吴寿妃,所以回身便是一剪刀,“卟”地便将吴寿妃手臂上的一块肉给绞了下来。吴寿妃“哎唷、哎唷”的松开了手。
张福妃披头散发,“格格格……呜呜呜……”的又是笑来又是哭,“去死吧!你们统统都去死吧!”她把手中的剪刀瞄准了唐太妃笔直的扔过去。
“去死吧!你们都去死吧!”脸色狰狞的张福妃歇斯底里的嘶声怪叫,然后象个猫似的一扭身往阁外飞跑,七八个内侍跟在后边,边跑边嚷:捉住她!捉住她!别给她跑了……
张福妃其实早就不想活了,周太后的体仁阁她是轻车熟路,所以一路跑到栏杆尽头,纵起身子轻轻一跃……
“嗳,你说,张福妃她真的疯颠了吗?”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天,王宁妃还是会把它拿出来说说。她还记得张福妃手持剪刀、满脸狰狞的模样,“唉,那个吴寿妃多什么事,由她那一剪刀下去,姓陆的老贼婆那还有性命……
陈康妃笑笑说:吴寿妃也很后悔呢,说什么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的话,她也是一时情急,结果吃了一剪,伤得可真不轻,当时殿上也就是你无动于衷罢了。
王宁妃说:我也差点吓死了,这几天一闭上眼睛就想起福妃来,还是那么哀哀怨怨的,唉,她儿子怎么就不见了呢?想想柳贵人逢难跳岩,被追册为皇后,张福妃也跳了岩,却说她行为狂悖,贬为庶人,连落葬也不允许,就一把火烧了了事,骨灰也给抛到茅厕里,好歹也曾位列后宫,还生过皇子,竟不如个普通的宫女。
陈康妃说:早跟你说过的,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张福妃连凤凰也算不上,又做出这种事,唐家能饶得了她?幸好自己跳了岩,要不然有她生受的。
王宁妃叹了口气,怅怅地说:咱们虽不是庶人,跟庶人有什么差别?好东西现在都送到永寿宫去,孝敬皇帝,孝敬圣母,却忘了长庆宫里的上皇和皇后了。咱们呢,也都不幸,衣食服御的都给减了等,哪里都不能去,关在这宫里捱命等死罢了。
陈康妃说:我母亲也是好些日子没进宫来了,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不过,福妃这回总算替咱们做了件好事……
王宁妃一怔:什么?
陈康妃笑道:长庆宫永寿宫从此各过各的日子,咱们也不必三日一朝,五日一参的去看别人的脸色。贵妃看到咱们只怕就会想起福妃,吃了这一吓,怕是一时难以缓过神来。
王宁妃也笑:那也是她活该!就算身份尊,位置高,那也要别人诚心诚意的敬重才成,那有象她这般抓肉往自己脸上贴的……姓陆的老贼婆这回就算不死,也活活掉了层皮,想起这事来我就要发笑,永寿宫里笑不得,我便在长庆宫里笑……上次说给上皇和皇后听,也是极难得的笑出声来,唉,姓唐的记得叫咱们去朝贺,怎么不让皇帝来长庆宫朝见上皇呢?她心里有愧,不但自己不敢见,也不让自己的儿子见,还口口声声说以孝治国,以德服人,所以普天同庆,四海欢忭呢。
陈康妃说:这都是朝廷说出来遮羞蒙人的话,你也信得?子逼父禅,权奸当国,仁义道德的说了满嘴,离篡弑却只差一步,也有脸说是承天应运、鼎新革故的真命天子?我呸!
王宁妃莞尔一笑:姐姐呸得好!我也跟你一起呸!呸!呸!
张福妃的行剌,加深了永寿宫和长庆宫之间的对立。陆太君被救醒过来,一口咬定姓张的贱人身藏利器,是想谋害太妃和皇帝,幸好那一日小皇帝不在圣母娘娘的身边,否则当面行剌圣驾,这后果可就难测了。
陆太君还觉得她女儿太不中用,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居然只独罪福妃张氏一人,而把宁妃康妃她们都给放还了,诸妃既然同来,则未必没有参与预谋,应该拘拿鞠讯,问个明白。
唐太妃不肯同意,只是说:既是长庆宫的人,理当网开一面,何况这还只是揣测,又没有真凭实据,真要拘拿鞠讯,让太上皇情何以堪?
陆太君怒道:当年因为柳贵人的事,太上皇要将你赐死,那可是没有半点的犹豫,你凡事总不肯听我的,将来终是要吃大亏!
唐太妃皱眉说:张氏已死,死无对证,难不成将宁妃她们也一并赐死?皇帝刚刚登基,便闹出这样的事,叫天下臣民如何看?我看处置张氏也就是了,不必牵连到旁人身上。
最终,福妃张氏被追贬为庶人,焚毁尸身,化骨扬灰,不许收葬;其至亲家人同坐大逆,一一问斩于城西校场口;张氏宗族凡有官诰皆予削夺,流配三千里外,遇赦不赦;长庆宫侍候张庶人的内侍宫婢全部当庭杖杀;永寿宫八喜堂曾经侍候过张庶人的内侍宫女人人重杖四十,发交慎刑司,罚做最下等的苦役。
这福妃张氏虽得罪了永寿宫,其于长庆宫却是有功,所以太上皇私下里为张福妃招魂超度,谥以“忠悯”,追册为皇贵妃,其神主牌位秘密奉藏于萱慕堂的后室受供奉祭享。
外朝方面,百官原先所议定的皇帝每五日即率群臣赴长庆宫朝见太上皇的大朝礼,因为张氏之事,被唐大相国以太上皇潜心静修,不欲为外事所烦扰而予以驳回。除此之外,本已首肯的许可燕国大长公主、宁安公主等宗亲贵戚进宫探视太上皇的特权亦都被取消。
被禁军放火烧毁的长庆宫门此时也加快了修建的速度。大相国唐觉之和执金吾张成义于百忙之中,都亲自吩咐下来,太上皇帝将要在此长住怡养,为防奸滑小人潜入宫中,图谋不轨,所以宫门要修得格外结实牢靠,连带宫禁周边的一圈围墙也要加高加固。
王守礼据此嘀咕说:臣不谒君,何得言忠?子不朝父,何以言孝?真是岂有此理!
太上皇似乎不以为意,反而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二龙相见,必有一伤,如此甚好,何必假戏真做,两不适意。
长庆宫的太上皇似乎看淡了世情,且将生死置于度外,因而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长庆宫虽然与世隔绝,却也因此自成一统,好歹太上皇汪皇后和诸妃儿孙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这寻常日子,散淡生涯,虽谈不上其乐融融,不过上上下下却因时艰而能和衷共济,而宫里的两位皇孙,年纪幼小,尚不识世间的忧患愁苦,整日承欢于堂前膝下,也足以慰人心怀。
宫外进呈的供奉虽时有或缺,大体上也足够敷用,王守礼深知眼下的各项用度都比不得过去,因此宽进紧出,除了太后、上皇和汪后那里不敢省减,其他人都各有裁抑。
宁安长公主不能进宫探望,心里自然抛舍不下,愤然上书皇帝及唐太妃陈情。长公主的上书自然到不了御前,最终搁置在唐相国的书房,而唐相国并不打算回复。
宁安公主无奈,径自入宫朝见太妃,唐太妃虽对唐相国言听计从,但公主所请系人之常情,况上皇那里,唐太妃自己也颇为牵挂,没有上皇,又何来皇帝?这人子之孝岂能弃而不论。
唐太妃因此让皇帝在朝会上问起此事,唐相国难以推托,只得许可宁安公主可以送物进宫。为防里外勾结,互通讯息,公主府致送的孝敬之物都要经过禁军的反复查验,确认无虞后,方才由又痴又哑的奴仆在宫门处转交宫内。
长庆宫里,汪皇后病体痊愈,跟随遇而安的太上皇不同,太上皇后心里始终怀有一丝期盼,从朝到暮,汪皇后常常举头遥望东南,口里念叨着南乡郡主。
“走了这么久,怎么着也该有个信儿了?”
尽管汪皇后望眼欲穿,但是期待中的勤王之师始终没有出现。京畿左近的州郡在错愕中得知京师生变,尚不及有所筹措,而皇上已经禅位,庆王随接登基,继而“吴王辅政、改元大赦”的诏书遍传天下,行事之速,有如疾风迅雷。大势所趋,州郡的守令于是一从旧俗,跟在朝廷的百官后面,上表称贺,俯首称臣,自是诚庆诚贺,顿首顿首,率土臣子,无不欢忭,皆戴德而称心……
洛上的方大用和齐鲁的唐会之此时也都在密切关注京师的情形,当然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京师有变,身为封疆之臣,坐拥重兵,扼守要区,言行举止当须慎重。
方大用不惟自己如此,还差亲信前往赣地军前,晓谕自己的儿子讨逆将军方镇川,要他也暂缓进兵,静观时局,若天不佑国,可据荆湘两湖以立足存身。
方唐二人按兵不动,静观京师之变,果不其然,大将军晋相国,进位吴王,独揽朝中大权,虽然如此,到底有所忌惮,不敢不替自己请封,于是方大用和唐会之皆诏授王爵,此乃唐觉之广布恩泽,使人安心之举,而封授之后,臣子照例要上表谢恩。
上表乃是表明姿态,方唐二人要做文章的话,自然也就做在这里。方大用所上的谢恩之表,破天荒的一式两份,一封呈献皇上,其中“诚庆诚贺,顿首顿首”之语,皆与众臣的忠心无二,然而另一份却专呈太上皇,请安问慰,致祝万寿无疆,亦显出方大用的臣子之孝来。
唐会之的上表同样也花了不少苦心,表中云:王爵之封,诚惶诚恐,固辞而不敢受,当竭诚竭力,尽忠尽孝,为国藩屏,永镇疆封。
唐会之并附家信一封,劝诫唐觉之:兄长身为相国且进位吴王,位居人臣之极,唐家因此而备极荣宠,弟初则以喜,继则以忧,但恐盛衰无常,过犹不及,而祸福相倚,吉凶难测,尚望兄长广纳忠贤,持盈保泰,功成不居。宜王妃,弟之女也,亦请兄长善待之。
唐觉之见信失笑:二弟胆小若此,又能成什么大事!
且说南乡郡主吃尽辛苦,狼狈于途,由京师出走之时,南乡郡主便不敢泄露自己的身份,所以由南都到南平,这一路走了将近有三十天。
而身在闽地剿匪前线的骠骑将军许成龙已经得知皇上内禅,庆王登极的消息。最初,当京中生乱,周氏一门惨遭不幸的消息传来之时,奉命监军的周如喜,望天号哭,不能自持。许成龙也是惊疑不定,苦于难通音讯,所以迟迟不能定计。
待到南乡郡主赶到南平,夫妻俩见面时各自惊喜,互诉衷肠。南乡郡主自然说起这京中之乱,并极力劝说许成龙带兵勤王。许成龙眉头深锁,率兵勤王,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由闽地至京师,路途遥远,所谓远水难解近渴,何况眼下皇上内禅,新帝已经登基,自己师出无名,将何以勤王?
周如喜却说:立储先当立嫡,继则立长,方称传承有序,而庆王非嫡非长,竟何以嗣位?皇上内禅必非出自圣意,将军但可声称奉太后遗诏与上皇密旨,领兵勤王,则大功必成。
周如喜这话自然也有道理,许成龙一时难作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