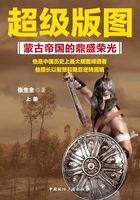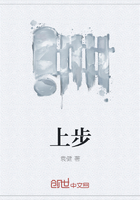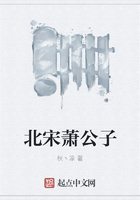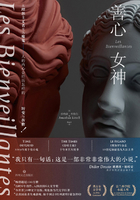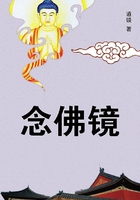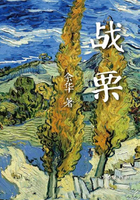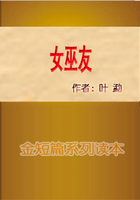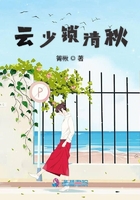方大用和唐会之的上表,让进爵为吴王的唐大相国放心不少,事实上,唐觉之倒不担心方大用能有什么大作为。洛上处四战之地,上有立国西秦的僭主伪帝嗣靖王,北有虎视眈眈的东胡大汗也里温,凭他一人承担这两边的压力,方大用一定不敢轻举妄为。
至于唐会之,与自己乃本家兄弟,其虽因废太子而略生嫌隙,不过既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唐字,自然荣损一体,相共进退,再说唐会之亦很识趣,上表只求“为国藩屏,永镇疆封”。
节镇一方,有如封藩,如果能够世袭据有,等于国中自立一国,会之的算盘到是打得不错,唐觉之也乐意送他这个顺水人情,再说以齐鲁的唐会之来钳制中原的方大用,本来也是一着很妙的布局。
现在领兵在外的将军节度当中,没有上表庆贺的唯有身在闽地剿匪的许成龙,而唐觉之想要对付的正是这位身为郡主仪宾的骠骑将军。为此朝廷给讨逆将军方镇川下了密令,要他设法解除许成龙的兵权,如有必要可在阵前斩杀,周氏余孽周如喜可一并处决,不必拿送京师,至于李得天和黄世英,只要愿意接受招安、归降朝廷,则既往不咎,量材任用。
安抚好镇守一方的节将,唐觉之回过头来安排朝官,武安侯张成义出谋献策,劳苦功高,虽说升迁为领军将军,但实际仅充任了执金吾一职,这自然是大材小用。
唐相国现在凡事皆要与张成义商量,因而常常要派人宣召,这么一来一去,颇耽误时辰,偏偏处理军政大事又少他不得,所以张成义仅担当了月余的执金吾,便以皇帝名义诏拜其为太保,协助相国处分政事,诏书中亦夺周如喜爵职,改以陈从圣为太傅。
鉴于执金吾掌领宫廷禁卫,职责重大,干系非小,任用别人吴王都不大放心,想来想去才将此职授予自家爱妾林氏的兄弟,也就是当年受父荫而承袭禁军指挥的林家老大林重阳。揖捕司的缺则给了振威将军马行原,至于放火焚烧长庆宫门的储定安储都尉则升作了统领禁军南北营的领军将军。
朝廷其它职差也各有分派,因政事堂已废,左相戴有忠迁御史中丞,忠义郡王宪源充宗人府的大宗正,驸马陆怀授了一个有职无权的抚军将军,等于闲废,京兆尹崇恩仍复其职。其余太尉门下的故吏旧交也都安置于六部九寺的大小衙门,以人尽其用,物尽其才。
因为皇帝尚小,所以一任政事军务皆委决于相国,并且皇帝受太妃指教,还当面提议要给自己的舅父加九锡,增封邑,结果吴郡十县皆入吴王囊中,唐相国自然笑而纳之,至于礼加九锡,吴王却上表说,加九锡非人臣礼,岂敢僭越,因而固辞不受。而吴王母陆太君,推恩荣封为吴国太夫人,礼遇同大长公主。
朝政和兵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似乎滴水不漏,唐相国把目光放远,想要恩被蛮夷。为相者既要安内,也要抚外。如果说周氏兄弟对国家尚有微功的话,那也就是会抚外夷、能通外交,唐相国旁的方面尽可不服,若论及与外夷蛮邦打交道,还是不得不佩服周如喜的高瞻远瞩,眼光独到。所谓花小钱办大事,但以区区岁赐,换来天下升平,四夷宾服,干戈不兴,波澜不起,端的是很不简单。
象上皇禅位,少帝登基,天下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西南的林东臣就是佯装不晓,朝廷一再催促,大理王林东臣这才不情不愿的上表,庆贺新天子登基践祚。林东臣是西南藩夷,上表称贺乃其职分,而他如果不上表,不修职贡,则说明边藩已生离心,不肯尊海内共主,归结而言则是因为天朝上国圣德有亏,王道不行,周边蛮夷皆以为不耻,所以拒不来朝。
因此林东臣的上表称贺,唐相国特别重视,给予林东臣重赏不谈,还赐以等同于吴王的冠服节仗。
除了林东臣的西南蛮,三秦是伪逆僭号之地,朝廷向来不屑一顾,环顾四海之内唯东胡方称得上是大邦,且又是友邦善邻,所以打探东胡君臣如何应对上皇内禅,新帝即位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唐相国心里早有一副安天下的妙计,那就是内肃朝纲,外和诸邦,为此相国暗地里密令唐会之,要他不计代价,努力说服东胡遣使来朝,庆贺少帝登基。
除了这些朝政与外事,唐相国现在还得面对一件让他尴尬与烦心的事,因为此事涉及宫闱,唐相国对此不但无计可施,尚还需百般遮掩。此话若说出来谁也不敢相信,皇帝之母,永寿宫的隆熹皇太妃居然暗生情愫,私通款曲。这要不是永寿宫的宫监前来密报,唐觉之决计不会往这上头去想,但是永寿宫的宫监说得言之凿凿,又由不得唐觉之不信。
说来这事与自己也大有干系,因为母亲吴国太夫人遇剌,当时虽说没有伤及要害,但是手上、身上被利剪捅穿的几个窟窿眼老是不见好,并且越来越红肿溃烂,触之剧痛,望之骇然,陆太夫人哼哼叽叽的忍耐不得,唐太妃也急得要征召各地良医。
唐相国于是想起一人,此人姓李名润,原本是军营中的散职郎中,治刀枪剑疮极为拿手,因累积军功授为朝奉郎,李朝奉的医术乃系家传,自有秘法,素称神奇,唐相国一想到此人,便化忧为喜,当即请他进宫替太夫人疗伤。
相国所请,李朝奉不敢不遵,自然使出浑身解数来为太夫人诊治疗伤,而刀剑疮伤最耗时日,尤其太夫人手上的创痕,由外到里皮翻肉烂,且伤及筋骨,最是棘手难治,因李润的家传之法,向来秘不示人,所以凡事亲历亲为从不肯假手他人,因而落得格外的忙碌辛苦。
吴国太夫人手上身上的创伤,也牵连着永寿宫圣母娘娘的一片孝心,唐太妃日夕不离其母,嘘寒问暖,恨不能以身相代,而李润亦是有家难回,只能留待宫中,以便随传随至。圣母娘娘便因李润做事认真辛苦,故常常赐食赐物,以为礼敬。一来二去,彼此间由陌生变为相熟,自然就消解不少这君臣之隔和男女之防。
永寿宫的圣母娘娘事实上是个寂寞的女人,有一腔说不出来的幽怨和伤心,儿子庆王的登基固然让她高兴了一阵,但是高兴过了,她依然寂寞和忧郁着。
象这个偌大的永寿宫如今只住着她一个人,虽说得到了身为帝母的尊贵威严,但是她曾经熟悉和依赖的,甚至是痛恨和诅咒的那些人都离她远去,只剩下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女人,不知道怎么打发这空闲下来的一大堆日子。虽说这一切都怨不得旁人,是她心甘情愿要把自己幽禁在这深宫里头。
回首以前的日子,虽然郁郁不得志,虽然心中常怀怨怼,但还算过得风平浪静、悠闲自在,身在宫里的女人几百几千年的都是这样过下来的,轮到她本来也可以这么不慌不忙、细水长流的过下去。然而半道中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子受禅登基了,自己变成圣母娘娘了,退位的上皇带着他的后宫头也不回的就远离了自己。
刚开始,唐太妃对身在长庆宫的上皇还有一丝牵念,但自从出了张福妃行剌的事后,长庆宫反倒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其所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唐娘娘对上皇的思念越来越淡泊,而对于自身的安危却越来越警惕,越来越放在心上,现在她甚至都怕听旁人提到长庆宫的二圣。唐太妃有时会去猜想,在太上皇的心里,也一定无时无刻都在痛恨唐家,他应该绝对不会原谅唐家的所作所为。
为了自己的儿子和娘家,唐太妃其实没有别的好法子可想,在上皇和儿子之间,她注定只能选择儿子和唐家。只是上天知道,死去的阿爹也知道,这一切原都不是唐太妃的本意,她想温良恭谨,有始有终,可是竟不能够。
想庆王成了皇帝,反倒不似他为王爷时能够常陪侍在自己身边,天未明即要早起上朝,晨午时分要读书听讲,身为帝王当要知晓帝王之道,因而一刻都不得闲,也闲不得。
皇帝偶尔对几个对子,吟两句诗赋,或者唱唱吴歌时调,那些保傅们便用“呜呼哀哉”来表达自己的痛心疾首,以为皇上寻章摘句,吟词唱曲,日益沉迷于此等雕虫小技之上,未免荒废了天地正业,辜负了万民百姓,妨害了江山社稷。
唐太妃心疼儿子,是因为她看得出自己的儿子整日里也过得不开心,但是听了保傅们的谏奏,她又不能不狠起心肠,把皇帝叫来跟前训斥,把那些引导皇帝不学好的小内侍都给赏了几十板子。
看着皇帝唯唯诺诺,低眉顺耳的样子,唐太妃又觉得老大不忍,皇帝虽然乖觉听话,可毕竟还是个孩子,想当年汪皇后对太子晟也没有她现在这般严厉。
唐太妃在请朝奉郎李润饮茶的时候,往往就会絮絮叨叨的说起这些闲事。她觉得这些话如果再找不着人说,她就会被闷死憋死。事实上她几乎已经憋得半死!永寿宫里她找何人说这些心底话?跟那些太监宫女说么?还是跟自己的母亲兄长说?
而且不管怎么说,永寿宫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永寿宫了,原先的那份热闹如今都烟消云散。但是想想从前,虽说有诸多的不美满、不如意,但这流水行云似的日子却还过得有滋有味。吵架伴嘴,争风吃醋,貌和神离,尔虞我诈,这一出出一折折的,都比戏台上演来的还要过瘾,陷身其中,直叫人乐此不疲,然而好好的一场戏忽地就散了,自己孤零零的失了群、落了单,既唱不成曲,也看不成戏。唐太妃忆及从前,想及今昔,往往一声叹息。
很多时候,李润都不知道怎么回复圣母皇太妃的话,他只能端座低头,目不旁视,幸好唐娘娘只是要个人在旁边听,等唐娘娘说完了话,自会让他回去。
可是唐太妃一但打开了话匣子,便有些收不住,一旦开个篇、起个头便如开闸放水似的滔滔不绝。有时候唐太妃人在永寿宫坐着,心思却转到长庆宫去了,话里话外全绕着上皇过去的那些风流韵事,从柳贵人到王宁妃乃至于张庶人生孩子……一件事勾出七八件事,七八件事又总能回到这第一件事上面来。
李润听得多了,忽然就生出几许疑心,太妃娘娘莫非天癸衰竭,气血不足,故而肝郁火旺,心神烦躁,意不能守,神不能安,忧思萦怀,言语噪刮,果若如此当以疏肝解郁、健脾和胃作为对症之策。
李润一念及此,自然奏对以进,唐太妃便恍然大悟的说道:果然是夜常盗汗,起坐不宁,有时又似神不守舍,无端端的总想生气发怒,难道真是邪气入侵、疫病缠身?若真是如此,恐怕又要劳烦先生。
李润至此又得摊上替唐太妃诊治内疾,调理玉体的重责大任。
唐太妃与朝奉郎李润品茗言谈,相与甚密,永寿宫的宫监们接二连三的报来消息,说得神乎其神,活灵活现,相国大人终于觉得难以隐忍,趁着进宫探视吴国太夫人的机会,唐觉之将内心的隐忧一一向其母道来。
陆太夫人斥其胡说,外人的诋毁你也信得?凡事当用点脑子想想才好!李郎中侍疾甚是小心谨慎,这必是有人眼红嫉妒,所以散布流言,恶语中伤。你妹子身有暗疾,自然也请李郎中为她诊治调理,这问诊问诊,不问又何以诊?李郎中开出的方剂,拿给太医院的太医们看,也都说拿捏得极有分寸,是个好方子!同行的太医们都这么说,那还有假么?再说你妹子,这一向都神情恍惚,动辄生气发怒,言行举止大反常态,果然象是妇道人家的病,我是过来人,尚能明白二三分,你却如何懂得?……这事由始至终我都知道,你休再胡说八道。若有外人瞎说乱言,直接给我打死了喂狗!
唐觉之不敢多言,起身怏怏而退。
然而事隔未久,相国大人终是逮得进言劝告的机会,因为唐太妃越来越对李润言听计从,宠信有加,故而特意向唐相国提出要任用他为太常卿。
太常是九卿之首,举凡史、乐、卜、医乃至庙寝陵园都归其掌管,李润以区区朝奉郎一跃而提升此职,不能不令唐觉之怀疑其中有私——只是这样的事如何跟太妃娘娘说得。
唐相国只能旁敲侧击的点出两句:太夫人的伤我看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李朝奉日夕留侍在宫中未免有些不妥,娘娘深处内闱,应防小人诋毁生事。娘娘适才说要提升重用,臣本来也是这个意思,欲将朝奉郎李润外放为湖州太守,湖州是个好地方,但做上一二任,子孙都不用受苦捱穷了,这也算是给他的酬庸,不知娘娘意下如何?
唐太妃却说:太常卿不与他做,那么就做太常寺的少卿吧。
唐相国一怔,道:外放为湖州太守已是高升,岂能任处身庙堂之上的太常卿?
唐太妃淡淡一笑道:既便太常做不得,光禄卿可做得?倘若也做不得,那么为少府令,把咱母子的衣食交给他去管吧,让别人承办这事我也不太放心。
唐相国说:太常、光禄、少府,事皆有人,并无出缺,李朝奉倘不能就任湖州太守,恐怕便连这个缺也要被别人补上。
唐太妃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这么说来,你是非要把他从我身边赶走?莫非早就有小人诋毁生事,却只瞒住我一人?哼哼,想不到这闲话竟然说到宫里来了!
唐相国说:宫中不能容留外人,朝奉日夕在此,必有闲话生出,想娘娘亦明白此中道理。
唐太妃不悦道:都是谁在胡说八道?宫里请个大夫叫个郎中,也是外臣能管的么?再说皇帝的那些师傅们讲官们不也都是外人?这进进出出的怎么就没人闲话?偏偏一个侍医问疾的李朝奉就派生出这么多话来。
唐相国无奈道:宫闱禁中,凡事总得避人闲言,娘娘也应该远离嫌疑。臣与娘娘乃骨肉至亲,所以不惮以直言相劝。
唐太妃竖起眉头,冷声道:好个骨肉至亲?你倒是信了闲言,疑心起我来了!哼,这也轮不到你来说,有上皇和皇帝呢!
唐相国苦笑道:娘娘,天下之圣母,受臣民礼敬孝养,当以身作则,为天下表率。闲言本无关紧要,只要人不在京中,自然言声止息。
唐太妃怒道:相国大人但管外事好了,宫里理当我来作主!
唐相国说:皇上年幼,尚须臣等尽心辅弼,遇事岂能不管不问。
唐太妃大怒:你休拿皇上做借口,皇帝是我生的,难道反不听我的?哼,这许多年总算捱出头了,哪个还敢给我气受!李朝奉不做太常便做少府,谁敢派他出宫,我就向谁要人!别的我也不多说,相国大人自己看着办吧。
唐太妃说完,拂袖而起,单把唐觉之给丢在殿堂中。
回到后寝,唐太妃越想越生气,她与朝奉郎李润不过就是闲暇时在一起喝上了几杯茶,说上了几句话而已,竟然蜚声四起,被人说得如此不堪,好在她现在至尊至贵,根本不用看谁的脸色,倒是旁人要学着看懂圣母娘娘的脸色。
唐太妃知道自己的脾气这一向急躁了许多,这不正是阴阳失调,腑脏失和的症结么?可是说来也怪,她只要和李朝奉喝上几盅茶,闲闲的聊上几句,这便心也平了,气也顺了,神也清了,待到李润起身告退时,心里反而有些惆惆怅怅的,于是就想着下回见面要跟他说起的话——都是闲话,越扯越乱、越乱越扯的那些话。当实在没话可说了,唐太妃会不耻下问的向他请益,所开的方子里配的都是那些药?各自都起什么效用?又是那里出产的最好?——这些淡得不能再淡的闲话,唐太妃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真是好玩极了,单单配齐一剂药,其中就有这么多的学问,李朝奉要是不说,她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唐太妃觉得这永寿宫一天都离不了李朝奉,要是李朝奉真被派去做个什么太守郡令,她这病一准儿就好不了。
唐太妃拿定主意了,别的事上她可以放手不管,单只李润升任太常卿或是少府令的这件事上,圣母隆熹皇太妃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当一次家,做一回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