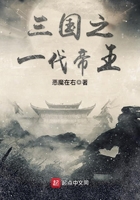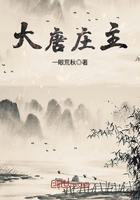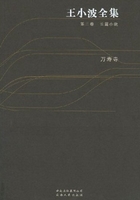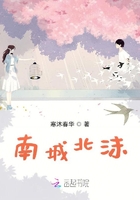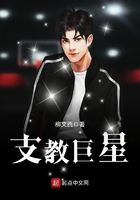勤政殿举行的大朝议因为没有结论,皇帝因此下令继续举行,直到宰辅大臣们达成共识。皇帝表示说:因为兹事体大,所以才要集思广议,卿等不妨畅所欲言。
但是皇帝并不知道,在今天的朝议还没有开始之前,宰执之间已经计划好了怎样收场。
想到今日殿堂又将有一阵噪聒,周太宰就双眉紧锁,于是悄悄拉住了尚书左丞陆正己说话:皇上以三天为限,要咱们拟旨上奏,象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吵到什么才有结论?唉,真是烦人!衙署还是少撤为好,把那些本事不大,却老是出言不逊的言官谏官们赶走,才是咱们该做的正事。
陆左丞迟疑着说:夺人家的乌纱,砸人家的饭碗,哪个心中不恨!这事难办,难办的很呐!那些言官谏官,前赴后继,凭你我怎么赶都是赶不走的!要是不小心惹急了他们,天天给皇上奏一本,可有你我受的!
周太宰便道:那些臭嘴乌鸦着实可恨,天天在皇上面前噪聒!就象茅厕里的屎耙子,搅啊搅,搅得臭气冲天了,还不肯息事宁人。
陆左丞悠然说:御史台眼下正被宋有道管着,他看相爷办事能顺眼么?
周太宰恍然大悟,连道:怪不得!怪不得!对了,朝议的事,大人是不是有什么高见?
陆左丞慢吞吞的说:高见倒是没什么高见,不过我想,衙门总得裁撤几个,员额也要减杀一些,不然皇上那儿实在不好交代,但是裁撤下来的人应该都要有去处。把他们安置好了,这才不会有人闹事,这样上上下下的人也才会满意。咱们在皇上面前也才算交了差事。
周太宰听了大喜,伸出拇指笑道:兄台妙计,妙,实在是妙不可言!
陆左丞说:这事可得瞒着那位柳相爷。那一位脾气倔,说话直,又没在京里混过,半点规矩都不懂。他要是知道,跑去跟皇上一说,那就坏事了!
周太宰笑道:那是个书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咱们不理他,由他自个儿跟自个儿别扭去。哼哼,等他那天把皇上闹烦了,他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
陆正己说:要不咱们先上道札子给皇上,若今日所议不成,明天也不用议了,直接草诏拟旨,待皇上朱笔批了,咱们照旨遵行。
周太宰眉开眼笑,拍拍陆正己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这个法子极好!”
这一天的朝议到晚上依然没有争出结果,皇帝也觉得听烦了,都是昨天说过的陈词滥调。看来这大朝议,大家七嘴八舌的也议不出什么好办法。
散朝时,皇帝独留三位宰执与唐太尉在殿中,皇帝说:开议了两天,众说纷纭,没个头绪,朝议这事应该就此作罢。
中书右丞柳子安对皇上说:议而不决,等于不议,皇上心中应自有主见。撤并衙门,裁汰冗职,已属刻不容缓,不宜久拖不决。
皇帝又问唐太尉,唐太尉也说:陛下乾纲独断,何需问臣。
皇帝于是谕示:朝廷设立官职原为办事,事去则官除,此为常理。撤并衙门,裁汰冗职,此事交政事堂详议,拟定裁撤的机构员额,然后会商呈奏。
周太宰领旨,回去和陆正己反复商议,拟出奏稿呈给皇上。
奏稿中建议:撤兵器监和军马司,督造军器,牧养军马一事皆归于兵部,不再另行择人设衙署掌管;屯粮司和广储司并为屯储司,纳入户部;度支使一职改由宰执兼领,省并其属官僚佐;将御史台侍御史员额由六人减为二人、监察御史由六十员减为三十员;撤谏议院,除谏议大夫另行任用,裁其下司谏、拾遗,员额凡二十人;罢弘文馆,将弘文馆的侍读、侍讲诸学士充任国子监国子博士,国子教授,翰林院清贵之地,冗员犹多,除保留草诏制诰的翰林学士和翰林承旨之外,其他皆可罢省;并太常寺于礼部,光禄寺则可省入内府,宗人府掌管皇族事务,大宗正宜存不宜废,可罢省宗人令……六部九卿此后亦当列出本部堂所要裁撤省并的佐官属吏,研议之后呈上都堂。
皇帝接到奏稿,觉得有些不太满意。轰轰烈烈准备推行下去的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结果只是不痛不痒的裁并了几个部门,除了减少了几员谏官,罢省了一群词臣,几乎啥都没做,这不等于是敷衍塞责吗?
皇帝于是又把三位宰执召来,当面听取他们的看法。皇帝开门见山的说:看了卿等的会奏,朕以为不妥。衙门并而未撤,冗官简而未除,只不过是挪动了一下,归并了一下,所谓减员,也只是减了言官谏官,翰林词臣,其余大体未动……你们且拿回去再议!
周太宰说:皇上励精图治之心臣等感佩。只是国朝迄今凡二百年,典章体制已成定规,今日若遂然撤并,恐朝野震动,不利于长治久安。臣领枢机,不得不为皇上妥为设法。
陆正己也附合说:凡事宜长图而不可燥进。所以先将衙门减省,而后再图撤罢。衙门撤了,官员属吏自然就无所任事,既无任事,那第一步减,第二步裁,合理合情,朝野不至于震荡,政事交接亦不会被延宕,即便被裁撤之官员吏属,只要得到妥善安置,便不会对新政阻挠抗拒,更不会对皇上心生怨望。
皇帝听罢默然,转头问柳子安。柳右丞也以为事情一次做绝,下次更难以推行,故而宜缓不宜急。皇上既然想力行新政,那倒不必在这件事上耗费时光。
皇帝于是准奏,令政事堂颁诏施行。
只是上苍似乎故意跟皇帝过不去,这道省并衙门,裁撤吏员的诏令发下去没多久,西南便爆发了战事。
西南诸夷自国朝平定天下,即上表请求归附,而朝廷以西南诸夷地处荒僻,朝廷鞭长莫及,于是赐给官服印绶,委以土司一职,代为镇抚一方,并允许子孙世袭其职。
其间有一位叫木成栋的杂姓土司,据金川江天险,伪言受天符命,而起兵称王,周边诸土司或逃往内地,或望风而降,或依附其下壮其声威。
木土司一时声势大盛,转而进攻周边府县,也是所向披靡,连克思州等十余城。原来骑墙观望的其他土酋,纷纷归附,木土司信心大增,于是自称滇王,欲与朝廷分庭抗礼。
西南各地告急表章如雪片般纷至沓来,皇帝深为忧虑。御史和司谏们纷纷上奏,力陈军务之紧急,亦显武备之重要,故而兵器,军马,屯粮等司监不可轻易裁撤,应予恢复加强。
皇帝不开始并不同意,诏书刚刚下颁,裁撤还未进行,就这么半途而废,实在难以甘心,然而兵部的大人于御前呈言:兵器监、军马司虽已奉旨裁撤,但兵部尚未能接管其事,请皇上暂缓裁并,俟战事完毕再作考虑。
皇帝颇为无奈,只得将上述诸司监一一恢复,所以不但旧制未能革除,反而因战事又增加了一些职官属吏,以专其事。
此后不久,因户部调节钱粮不灵,广储转运司也被复置,由尚书右丞柳子安兼任的度支使也摇身一变,成了人数宠杂的度支使司衙门。
柳子安长于学识,拙于谋事,于理财征赋更是一窍未通。初任其事,孤掌难鸣,不但起用了原屯粮、广储、转运司的旧人,还另行配置了一堆吏员属官以为辅佐。而理财征赋,事颇烦难,柳子安兼任伊始,便忙着到各地征税追饷,以助军需开支。是以百姓赋税非但未能减轻,倒因西南战事又增多了一笔。
那木土司夜郎自大,据有西南半幅之地,便欣然自得,致书于朝廷说:陛下抚有中原,如天中之日,而寡人经营西南,如日旁之月。日月经天,并行不悖,是故陛下有中原而为帝,而寡人据西南而称王。寡人愿与陛下约为兄弟之国。
一个蛮夷土酋,也敢跟朕称兄道弟,简直是荒唐可笑!皇帝不笑反怒,决意用兵西南,剿灭这个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木姓土司。
只是派谁为三军主将领兵征讨,又让皇帝大费踌躇。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右将军唐觉之是个恰当人选,与宰执会商时,皇帝说:大军易发,主将难求!朕拟用右将军唐觉之为帅,领兵西征,诸卿有什么意见?
周太宰摇头以为不可,军权操之唐氏,已历三代,何况皇上刚刚罢了唐氏的领兵之权,今复用之,恐生变故。
陆正己亦持此议。他对皇上说:虽不敢说唐氏一门心怀叵测,但陛下力推新政,唐氏因此失权失势,心中未必不怀恨。陛下重用右将军,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试问谁能制服?况西南夷乱,乃是芥癣小疾,将军不臣,才是心腹大患。皇上宜深思。
皇帝听罢,内心有些动摇,便道:西南虽是边患,却可动摇国体!况且卧榻之旁岂容他人憩息!木氏叛乱,大逆不道,不加惩处何以安定四境?领兵征战,朕不用唐觉之,又能委派何人?
陆正己建议道:不妨以车骑将军周如乐督师西征,惩罚凶逆。想那西南蛮夷,乌合之众,撮尔小贼,天兵一到,自当束手就擒,到时绑缚都下,献俘太庙,成就圣武神功。
皇帝还想派人问问柳子安的意见,只是柳右丞尚在外地筹措钱粮,这一来一往,徒废时日,只能作罢。
第二天皇帝颁诏,以车骑将军周如乐为征西大将军,领禁军骁骑卫精兵五万,并西南各处守卒,合计十万,讨伐木氏。
周如乐受命出征,一路姗姗,将近一月方到西南。及至西南,官军未及休整便贪功冒进,想一举拿下思州,不料在鹰愁涧中了埋伏,前驱的一万兵士几乎折损过半。
周如乐听了前方败报,仍是没把这个蛮夷土酋放在眼里,还是下令攻取思州,他想单凭官兵的人数,就足以推平思州,等到拿下思州就可以向朝廷上表告捷,请皇上劳军犒赏。
那木成栋给了官军一个下马威后,便按兵不动,思州山高谷深,水急林幽,处处可设伏兵,而官军初来乍到,陷于此地恰如无头的苍蝇,自是被动挨打。
连吃了几个败仗之后,周如乐终于变得谨慎小心,他让官军坚壁清野,就地安营,企图长期围困,然而木成栋识破官军之计,率士卒翻山越岭,先是劫了粮道,一把火又烧了营寨,混乱之中,官兵溃散,又遭木成栋大杀一通。
虽然一败再败,周如乐仍想隐瞒战况,只是皇帝派出的监军不依,一五一十奏告朝廷。
皇帝大是震惊,正要严旨切责,不料坏消息接踵而至。周如乐听说监军将败绩上告朝廷,生怕皇帝责备,便想扭转败局,于是亲自督率三军强攻思州,眼看着思州城就要攻破,结果木成栋领兵从背后杀来,而思州城中也冲出一支劲旅,前后夹击,官军大败,十丧六七,粮草辎重军马兵械丢弃无数,而周如乐仅带身边亲随突围而逃。
木成栋获此大胜,一鼓作气,乘胜推进,接连攻陷周边八州四十余县,洋洋得意之下,僭号滇帝,于是置百官,封将相,建宫室。
皇帝一闻再闻官军败绩,寝食难安,坐卧不宁,连夜召太尉唐明商讨西南军务。
唐太尉闲居在家,亦很关注西南战事,当下向皇帝多有建言。皇帝深以为然,便欲以太尉督军驰援。唐太尉以年老推托,皇帝再三催促,太尉始推荐其子右将军唐觉之领军征战。
皇帝应许,当即再发禁军三万,以右将军唐觉之为平夷大将军,总领西南军务,以中书右丞、度支大使柳子安为监军使,负责粮草后勤。诏令夺周如乐车骑将军印绶,罢征西大将军职,槛送至京师治罪。
唐觉之带兵西征,行至西南却按兵不动,整日里只是叫来些当地土人来问问当地的土风人情,或者叫士兵们出操演练,排列阵形。柳右丞见状心中狐疑,屡屡促请动兵,唐将军总说是时机不至,不可枉动。柳右丞无奈,欲自率一军与敌交战,又为唐觉之所阻。
柳子安更是恚怒,欲上书朝廷,细数唐觉之种种叵测行为,让皇上有所提防。谁知柳大人正要拟稿,唐觉之却亲到柳右丞的营帐中,与柳大人促膝详谈其谋军布局与克敌制胜的思路。
唐觉之以为,敌人连战皆捷,心高气盛,正是锋芒毕露之时,我军刚遭败绩,远来疲累,宜避敌锋锐;况且皇上和朝廷对西南诸夷仁泽恩厚,木氏虽骄横不可一世,诸夷却未必肯舍弃朝廷而臣事木氏。所以吾已派人对他们安抚慰问,只说皇上只是归罪于木氏一人,并且深知诸夷是为其所胁,所以不会问各位的罪,如果各位立有大功,更可得朝廷的重封厚赏。所以木氏虽能骄横一时,终必不会长久。而士兵随军征战,家中父母妻儿日日倚门盼望,岂可不顾惜他人性命,而逞自家一时之快。
一席话说得柳子安心服口服,于是对内加紧储备粮草,整顿士卒,对外却示弱于木氏。至于上呈皇帝的奏书,也由细数唐觉之的种种不是,变成了通篇的嘉许赞扬。
都堂上的周太宰为此有些纳闷,跟陆正己闲聊时不禁哂笑:这书呆子被唐觉之灌了什么迷魂汤?把个监军使变成了劳军使!这仗还没打就预先唱起了高调!
因为周如乐的大败,周太宰和陆左丞这几天心情都有些低落。周如乐是太宰大人的异母兄弟,本是同根,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周如乐被槛送京师治罪,先不说这面子挂得住挂不住,自己到底是救还是不救?要救则只有自贬,可惜这太宰位子却还没有坐热。
陆正己与太宰同病相怜,要不是他当初力荐,皇上决计不会让周如乐掌兵出征。所以这个“保举非人”的罪名是逃脱不掉。这也怪他考虑不周,原想借此结好周氏,结果这个草包搞砸了一切。因他的牵连,自己灰头土脸,畏畏缩缩,皇上面前话都不敢多说两句。
朝廷大军卷土重来,木氏依仗地形,严阵以待,不想除了一些佯攻骚扰,官军并无大动,这样对峙数月,蛮兵皆人困马疲。
木成栋以为,官军在此安营扎寨,一时半会恐怕不会撤离,自家也得修堡垒,筑皇城,以便坚守,再说手下兵马征战多日,也得犒赏修整一番。蛮人上阵为兵,下阵为民,并无军规军纪约束,得了犒赏,便喝酒耍钱,歌舞娱神,于是人心渐渐松驰,不复当初奋勇。
双方各自屯兵不战将近三月,唐觉之见对方锐气已失,这才下令诸路进兵,第一仗便收复思州宁远等二十余个郡县,官军的士气由是大振。
初战告捷,唐觉之不失时机,一路上剿抚并举,恩威同施,原先骑墙观望的土司豪强大都重新归顺了朝廷,唐觉之威逼利诱他们侵吞蚕食木氏的后方地盘。
土酋夷长既得朝廷封赏,又能多占土地人民,眼见得木氏一方势败,自然乐意为官军效力,木成栋闻知,暴跳如雷,丢下官军不顾,亲自引兵攻打那些背盟的同族。
而唐觉之柳子安趁着木成栋与土司们彼此相攻,无暇他顾之际,兵分两路,奇袭木氏盘踞的土司老城,一举俘获木成栋的母妻亲族一百余人,斩杀的蛮兵夷勇,堆成一堆,覆土成山,号为京观,以此震慑当地蛮人,使之永不敢叛。那木成栋闻知老巢被捣,家族覆灭,吓得连夜远遁,逃至境外。
捷报传到宫里,皇帝大喜过望,一边发内帑银三十万,绸缎十万匹劳军,一边派出使节往境外蛮夷国索取元凶大恶。
这场西南战事,由普庆元年二月爆发,到普庆元年十月上平定,历时不过八个多月。朝廷虽说取得了历年未有的大捷,不过府库多年的积储也几乎用得囊空袋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