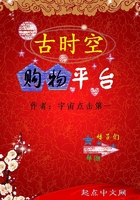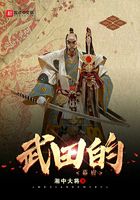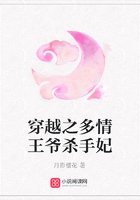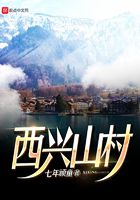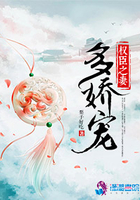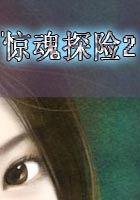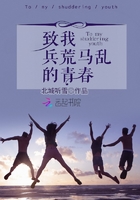自从太子晟醉酒殒命,上皇在皇后的劝说之下,就此打定了主意滴酒不沾,但是这天上皇难得高兴了一回,便又频频呼酒。等到酒宴将散时,上皇左一杯右一杯的已然喝得酩酊大醉,内侍们掖之不能起,扶之不能行,连肩舆都乘不得,最后还是王公公背负上皇而走。
虽然上皇醉了,但是汪皇后始终清醒得很,京师上空的日食应该是上天示现的一个兆头,其于长庆宫到底是好是坏呢?汪皇后一时还有些瞧不出来。
两位皇孙先前就被奶妈和嬷嬷们安顿着睡下了,康妃这会儿也率着宁妃和寿妃先行告退,光明殿里眼下只有陈太后、汪皇后和唐储妃这祖孙三代女人在。她们的目光灼灼,似乎都想要说些什么,只是没人抢先开这个口。
烛影摇红,照得地上的影子也晃晃悠悠,汪皇后忽然幽幽的叹了口气,她嚅动嘴唇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成。
陈太后努力了半天,这时终于挤出一丝笑容,她说:皇后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天狗食日,乃是上天示警,吾倒以为这是上天给永寿宫一个悔罪改过的机会。
汪皇后苦笑一声:悔罪改过?但愿如此罢。
元献太子妃唐媛一直有点心神不宁,这时候却插话说:回禀母后娘娘和太后娘娘,儿臣清明出宫往佑圣寺祈福上香,曾经见过元妙上师一面……
陈太后一时没想明白,怔道:那个元妙上师?
汪皇后的眉头却是一皱,急急地说:你见过她了?可有什么消息?
陈太后这下也回过神来,“是啊,宫禁森严,消息难递,你若是见过她,可曾设法通些消息?上次陈夫人来去匆忙,竟是不曾见上一面……唉,消息难递,叫人莫之奈何!”
唐媛道:儿臣亦没有料到会在佑圣寺里见到元妙上师,不过既然见到了,那也是天假其便,儿臣岂能放过,当即修书一封,请元妙上师设法转呈臣父,儿臣要臣父心念社稷,抱忠怀孝,妥为设法。元妙上师亦亲口答应儿臣,同仇敌忾,致成此事。
汪皇后先是一喜,继而又迟疑道:话虽如此,到底远水难救近火,时移势易,似乎难作倚靠……
唐媛道:虽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唐字,然而儿臣敢请太后娘娘与母后娘娘放心,臣父忧君忧国,自会尽忠尽孝,匡扶帝室,谨守臣节。
陈太后说:吴王是吴王,尔父是尔父,龙生九子尚有不同,何况尔父与吴王只是同族!吾看天现日食,其兆头应该甚好!世事千变万化,总有他们顾虑不及之处。与其死水沉沉,波澜不起,倒莫如生出些变化,让人觉得日子还有些盼头。
汪皇后定了定神,忽然说:这长庆宫四面高墙,密不透风,闷得象个葫芦,得想办法钻它几个眼子,也好透透光,通通气。
陈太后眼睛一亮,点头道:对,应该趁着这天象示警的好时机,密密麻麻地多钻些眼子!
日食异象发生之后,京师和江南如今都在传言,煞星凌日,而日主人君,此大凶之象,莫非预兆着长庆宫的太上皇凶多吉少,这回将要应劫而去?这大不敬的话如果往深处细说,太上皇的幸与不幸跟宰执的忠义与皇上的孝顺大有干系,而这正是天人感应的具体例证。
百姓和朝臣们对于吴王不忠和皇帝不孝的声讨和指责隐隐约约传进长庆宫帝后的耳朵里,这给上皇和汪皇后带来了些许希望。长庆宫的人觉得现在应该妥善利用外间的这股风评,虽然上皇和皇后暂时还看不出情势将往何方演变,但是不可否认,日食的发生对于长庆宫而言喻示着新的转机已经或者将要来临。
长庆宫的人都想赶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连日来,汪皇后一直呆在同庆堂跟上皇推究盘算此事,因为汪皇后的迫切,连带得上皇也跟着热衷。
只是不管怎么推测盘算,幽居禁宫的帝后贵人们,对于宫外的情形如同盲人摸象,所以这推究来、盘算去,都是纸上谈兵,难见效用。
汪皇后因此难以安心,她跟前的亲信何知书说:奴才以为,要想探知永寿宫和朝臣的态度不难,假如上皇忧心成疾,卧病在床,永寿宫岂能对此置之不理,这忠孝二字其实就是把衡量的尺子,为人子者,敢不虔敬?眼下天现异象,可不正因为忠孝不存,仁义俱失,诸礼皆废,所以才会人怨天怒。
汪皇后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只要上皇卧床装病,借此试探永寿宫吴王唐妃的回应,以及朝臣百官所持的态度。根据永寿宫和朝臣们的态度,长庆宫便可具体选取所要应对的策略。
皇后这就郑重其事的去同庆堂跟上皇商量。上皇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好端端的要他装病卧床,这似乎有点太不着调,但是汪皇后一再说,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皇上就得用一些非常的法子。皇上这病自然不是遭了天遣,而是给不忠的臣子和不孝的逆子给生生气出来的。永寿宫如果还有一点孝心,自然该来长庆宫朝觐太上,永寿宫要是肯来朝觐,日后朝臣和外戚来宫里问安请谒,应该再没有理由阻挠非难。眼下宫里的当务之急是要先跟外面通上消息,这消息不通,寸步也难行,永寿宫来不来朝觐其实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皇上能够跟朝臣和外戚们相见,只有见了,才能传递消息,才能有所安排,……皇上不妨权当是在演戏罢了……
汪皇后的话最终说动了上皇,于是乎上皇突然就病重不起了。
上皇这回发病甚急,慌得内廷令王守礼带上一群小宦不管不顾的想冲出宫门去传召太医,却被执金吾林重阳如临大敌般的拦阻在丽景门内。
王守礼几番交涉未果,于是领着一帮宦官在宫门里呼天抢地的大哭大叫,宦官们尖利的嗓子一时竟压倒了金吾卫将士们的喝叱,他们那拖着长音的数落哭叫,比京师里专事哭丧的妇人们还要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显然这些举动都是长庆宫预先编排好的,意在让上皇染疾的消息不胫而走,使得天下臣民尽知。这目的自然也如愿达成,不上两日,合城皆知上皇病重,却被弃置于冷宫而无人过问。茶馆酒肆若有人谈及此事,则每每摇头叹息不已。
上皇染疾的事自然也惊动了朝臣,太师陆正己和太傅陈从圣会同谏议大夫尚质和京兆尹崇恩等人联名上奏,请皇上率文武百官亲临长庆宫朝觐太上皇帝,以尽人子之孝、臣子之忠,安黎庶百姓之心。
上皇染疾是桩大事,永寿宫不能再无动于衷的置之不理,先前已被朝臣们的天人感应说搞得心神不定的圣母娘娘,现在越发食不香而睡不宁。
“朝政外事自有吴王做主,娘娘有什么好担心的!”陆太夫人劝她息心宁神。但是唐太妃却听不进耳,她想,要是皇帝亲往长庆宫朝觐就能够消灾弭难的话,自己似乎没有理由去干涉阻止。
唐太妃召来吴王征询他的看法,唐觉之先还不置可否,未了却说了一句:长庆宫之丧,实即为永寿宫之喜,娘娘何须为此挂虑?臣在此为圣上和娘娘贺。
吴王这话最终打消了唐太妃心中的顾虑,天现灾变,自然是要报应在下方凡人的身上,上皇若应验了此劫,自然就代受了天降的灾殃,诚如兄长所说,这对永寿宫而言,有利无弊,正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自己的确是多虑了。
唐太妃拿定了主意,只许太医进宫侍疾,自己却守着皇帝不让他前去朝觐。然而大长公主和长公主此时都来永寿宫见她,燕国大长公主惦记着小楼子的前程,倒还恭顺安分,宁安长公主却是人未语泪先流,她眼泪汪汪的哭求圣母娘娘开恩,允许其进宫探视父皇。
“父母有病,子女事亲奉孝,原属天经地义,儿臣若不能竭尽孝道,岂非连禽兽也不如?”
这话说得唐太妃脸色讪讪,面对宁安公主一再的恳求哀告,圣母娘娘有些招架不住。何况除了两位公主,她所信任的内廷令李润和保义夫人郑氏也在她耳边殷殷相劝。唐太妃架不住众人劝说,原先的想法几乎就快要动摇了——允许两位公主进宫侍奉尽孝,至少可以堵一堵朝臣们的非议责难。
陆太夫人知道了此事,轻描淡写的对自己的女儿说:心软成不得大事!再说凡事你兄长自会考量,娘娘且忍一时,切不可擅自主张,等到长庆宫的上皇崩了,公主便日夕长住在宫里,也是无妨……日食是上天谴责,总要有人应劫遭殃才成,娘娘难道要把祸水引入永寿宫,心中才惬意不成?
唐太妃立刻警醒过来,绝口不提许人朝觐之事,便是太医院的太医们也再不派去长庆宫问诊侍疾了。
保义夫人凭着梳头的好手艺,如今在宫里重新站稳了脚跟,宁安公主来的时候,她自然去谒见了公主。
当她见到宁安公主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的样子,便在私下提醒公主说:宫里的事现在都是吴王做主,圣母娘娘做不得大主,公主求她还不如去求吴王。而吴王又肯听太保大人的,太保大人所宠的倪夫人正是府上二夫人的姐姐,公主不妨通过二夫人去请倪夫人从中帮忙。
宁安公主对于这些骤然贵显起来的人家一直打心眼里瞧不上——都是些什么根基出身?竟也冠冕堂皇的做起了公侯、夫人!虽然内心里鄙夷不屑,宁安公主眼下却不得不低头求告于人,所以一回到府里,她便放下架子,央请姚璎珞往张府里去说情。
公主吩咐交待的事,姚璎珞不敢不尽心,当即去见了姚琉璃。
姚琉璃笑说:难得公主肯来求我,这可是天大的面子,我就试着跟我家大人说一声吧。
那姚琉璃果然有些手段,第三日上便从太保大人那里讨来了符节,并差人送到公主府上。
自己千求百讨而不得的符节,姚琉璃得来却全不费力夫,宁安公主因此感慨万千,贵不如贱,屈尊就卑,堂堂公主竟不如权臣家的一个侍妾,世道颠倒如此,上天现出灾异景象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大学士陈广陵想要尽忠,而太傅陈从圣偏偏要他先尽孝。这里面其实很有分教,因为陈家父子二人在尽忠尽孝的问题上存有歧见,所以话不投机,彼此争执。
“不忠不孝,其能为人乎?象你这样忤逆不孝的孽子,又何以称得上尽忠报效?可恶,陈家怎会生出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
陈从圣大声斥骂自己的儿子,就好象在骂一条不听话的狗。在这之前,他已经摔烂了三只茶盅,他觉得自己快被这个不孝的儿子给活活气死了!
可惜陈太傅的冲天怒气并不为儿子陈学士所接受,陈广陵当下辩白说:“父亲大人此言差矣,先圣曾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父亲大人要儿子谨守孝道,从父母之言,儿子原本不该不听?其为人子,当尽孝道,若为臣子,应竭尽忠心,但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以尽忠事君为先,父亲大人要儿子尽孝,便是陷儿子于不忠,则儿子绝不敢遵从听命。”
陈学士这话噎得陈太傅说不出话来,真是有其君,必有其臣!陈从圣跟陈广陵的分歧就在于各为其主,各尽其忠。陈太傅受恩于太上皇帝,所以一直以太上皇的孤忠耿介之臣自期自许,他对于太上皇的际遇始终是耿耿于怀,所恨者,在于自己不能帮扶辅弼,成功成仁,再造乾坤。
当他以自己对太上皇的忠诚来评价自己儿子的行止,那么他儿子陈广陵简直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女儿入宫为皇妃,自己身为国戚,却弃太上皇帝于不顾,助纣为虐,甘当贰臣,此即为不忠;而父母在堂,却不听教诲,擅作主张,又诚属不孝,此不忠不孝之徒尚还有脸面振振有辞,作语自辩,简直就是不知羞耻。
然而陈大学士对于其父的斥骂却始终不能服气,陈广陵自有陈广陵的想法,当今天子如今是他的门生,他只能竭尽所能辅弼这位天子门生。何况忠孝忠孝,忠须在孝前,自己身为皇上的臣子,且又是帝师,自当事君以忠,然后才能尽孝于亲,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惟有尽忠事君而已,所以陈广陵认为,自己对于当今皇上的忠心,乃是良臣所为,是尽善尽美的大孝。他若是听从其父的教诲,那便是对当今皇上不忠,既然为臣不忠,那自然就更谈不上为人的孝道了。
父子两人为着这忠孝的道理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忠字,一个孝字,都是几天几夜也辩不清,论不完的大道理,偏偏这父子二人都是学富五车的宿儒,引经据典,坐而论道自是寻常功夫,府里的女眷躲在帘帷后面偷听,此时都是面面相觑,叫苦不迭。
堂上陈太傅以杖触地,犹自怒道:忠臣出于孝子之家,为人子者若不能事亲尽孝,试问将何以尽忠于皇上?
陈学士却说:忠义虽出于孝道,然而大于孝道,否则当无大义灭亲之说。
陈太傅当即冷笑道:俗谓名师出高徒,此话果然不假。吾儿为帝师,但知忠而不知孝,其所教的门生天子,学问偏颇,礼仪疏失,既不知忠,亦不知孝,弃父母于冷宫,不朝不问,全无人子之礼,亦无人主之望,所以获罪于天,日食灾异,即为明证,吾儿对此还有什么好说的?
陈学士一时语塞,讷讷地道:圣上为权奸所蒙弊,儿子只有百般导之向善,以圣上之聪慧,当会翻然悔悟,礼敬二圣。
陈太傅摇头叹息:国贼不除,难有宁日,上皇内禅,且是本意哉,乃为权奸威逼,故太子废死,二圣幽闭荒宫,而少主幼冲,权奸借机专权窃国,种种不臣不法之事,罄竹难书。为父受皇上深恩,无日无时不筹思报效,然而孤掌难鸣,只能忍气吞声……唉,当日若非为父贸然进言,权奸国贼又何能领兵作乱?纵虎归山,反受其害,悔之莫及,此皆为父有负于皇上,思之心常愧疚,不免落泪无言……
陈太傅念及此处,两行浊泪不觉洒落胸前,竟呜咽不能言语。
陈学士劝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意高深莫测,世事瞬息万变,此皆非人力所能挽回,当顺时就势,恪尽本分而已,父亲大人又何必为此耿耿于怀。
陈太傅恨声道:你我虽是父子,却终究不能同心同德,为父的话你既然不听,也罢,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你我从此分道扬镳,今后各为其主,各尽其心便是。
陈学士垂手道:儿子但知尽忠,不免有失于孝道,忻望父亲大人万勿怪罪。
陈太傅道:我自当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明天你就给我择府另过……
陈学士肃然道:谨遵父教,自当从命!
帘帷后面的女眷这会儿都大惊失色,老太爷这话里的意思,竟是要赶老爷出门!这,这可如何是好!唉,这书读多了,人读痴了,为着这所谓的忠孝,父子之情、家人之义便都可以不问不顾的一断了之么?这事要是传扬出去,岂不让诸亲六眷们笑死!堂堂诗礼之家、书香之族,竟然也生出父子隔绝,不相往来的怪事。然而陈家这父子二人都是一言既出,九头牛也拉不回的倔脾气,女眷们因此都只敢哭,却不敢劝。
可是陈太傅又说:青天白日的嚎什么丧?当初圣上内禅,举国惨戚,到未见尔等女流妇道流泪伤心,君恩大于亲情,此等不孝之人,目无君上父母,自弃于天地,逐之出门,乃是合家庆幸之事,你们都给我回内宅去……
女眷们屏息静气,不敢言声,只有康妃娘娘之母陈金氏随口嘟囔了几句:虎毒尚不食子,老太爷怎么能够翻脸无情呢?儿子固然可以不认,难道连宫里的娘娘也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