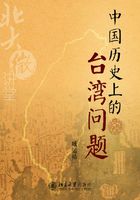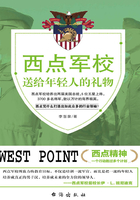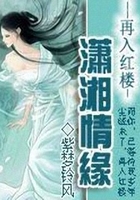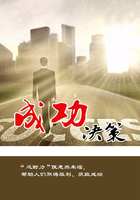长庆宫的种种不满,少府令李润都看在眼里,尤其当太皇太后一把浊泪地说起燕国大长公主的时候,李润也会感到恻然,父母子女,人之天伦,如今两宫睽隔,声息不通,终不是长久之态。所以在回去禀复的时候,李润字斟句酌的颇费了一番心思,这话要说得恰恰好,既宛转又明白才行。
唐太妃对于李润转述的长庆宫的态度并不感到吃惊,在默然良久之后,唐太妃淡淡说道:李大人这趟辛苦了,想是受了不少难堪与脸色吧。
李润说:替皇上、娘娘当差办事乃微臣之职责,岂敢言得辛苦!不过象太皇太后所言,皇上日理万机,不能亲临,倒也罢了,何以安国夫人能进宫探视,大长公主、长公主却不得入宫侍亲奉孝?这又是何家的礼仪规矩?臣自然无言可对,想太皇太后年已老迈,思女心切,出此怨言也是难免。
唐太妃沉吟着说:让长公主、大长公主进宫侍亲奉孝,想来到是无妨,不过此事尚需跟丞相商计一番,好有个安排。
不让皇帝赴长庆宫朝觐二圣正是唐太妃自己的主意,她在永寿宫里自成一统,安享富贵尊荣,对此越来越习已为常。长庆宫这三个字,现在只要稍稍一想都会让她皱起眉头,而皇帝年纪还小,留在永寿宫自己的身边尚放不得心,何况是置身于长庆宫这个自己鞭长莫及之处。若皇帝轻涉险地,遂然生出变故,到时候谁能够担当大责?
李润到底不是圣母娘娘肚里的蛔虫,一时没听出唐太妃是拿丞相来做托词,当下却说:宫里的事娘娘皆可做主,虽是丞相亦管不得。娘娘要是照准的话,丞相那边想也没什么说的。不过就是寻常家人见面,一月三旬,每旬许其一见,按理应没什么大碍……
唐太妃现在已将李润视为心腹,所以便与他直言道:长庆宫那边与咱们终究有些心结难解,太皇太后和上皇恐怕也不能就此消气释怒,这都是没法子的事。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皇帝跟上皇虽是父子,然尊贵并无二至,若有闪失,天下难承其重!所以当以不见为好。至于大长公主和长公主也没说不许她们进宫侍亲奉孝,不过总得等时局安稳,诸事谐和,方能成行。这事暂时就这么着吧,只别叫皇帝知道。长庆宫那边的供奉若有什么短缺,李大人不妨在这上面多多操心费力,别再叫人说什么子不孝亲,两宫睽隔的瞎话。
李润听出唐太妃的意思,当下不敢多言,垂首应是。
唐太妃却笑道:李大人何妨随意些,早前吃了你开的方子,晚上也还能囫囵睡上一觉,精神气力的都好了许多……只是夜梦仍多,成日似烦似闷的打不起精神来,虽然倦极思睡,一时半会的又合不上眼……
李润说:娘娘还需固本培源,养性修身,饮食上面亦要善加调摄,假以时日,当会痊愈。
唐太妃说:从前呆在宫里能有个人在跟前说说话,玩笑会子,开心不开心的这一天也就过去了,宫里的日子往往都是这么过的,可是现在却不成了,定下神来就会乱想,好事喜事想不起几桩,转的念头全是些不如意——按理也没什么不如意的,可就是心烦意乱,总象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这心也就悬在那儿,悬成细细的一根线儿似的……可是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天既塌不下来,地也陷不下去……可吾偏就没有一个踏实的时候。
唐太妃也说不出来她到底在担心什么,就是心里老觉得不踏实,这股不踏实,白天她还可以强压着,然而一到晚上它就出来作祟,疑神疑鬼,坐卧不安。
唐太妃皱着眉头跟他说起另一桩事来,前日去后山那边赏芍药,深红浅紫的倒也好看,可就是没来由的听见一阵小儿的啼哭,隐隐约约,似有若无,问起身边的小宦却都说没听着?后山那里,等闲时你要记得带人去仔细搜搜,别是有什么邪物古怪的东西藏在那儿。
听唐太妃这么一说,李润顿时想起后山处的那个僻院,当下吃了一惊,赶紧回说:禁宫大内,自有百灵呵护,妖邪古怪之物避之惟恐不及,岂敢冲犯慈驾!想必是宫里捉鼠的猫儿在山中嬉闹,叫声经风吹散,传到了娘娘耳中,令娘娘起疑生惑。
唐太妃道:我分明听见是小儿啼哭……只那么一两声,再听却又没声了……
李润还待再说,后殿这时一声咳嗽,陆太夫人缓步出来,李润连忙上前请谒,陆太夫人笑呵呵地说:老身幸亏李大人的悉心调理,原先筋骨疼的老毛病,今年开春竟也轻了许多,只是每天这晨起装扮,煞是费心,头发一掉便是一把,几乎梳不成型,想问李大人可有对症的好方子?
李润对此倒是无辙,正想着该如何回禀,唐太妃却想起什么似的说:保义夫人!是该把保义夫人叫进宫来,她可是梳头的好手,当年一直侍奉周娘娘的,眼下怕是呆在宁安公主府上,要不这就打发人去宣召。
陆太夫人便也微笑道:当年她可是是个大忙人,咱们等闲还请不动她,不过梳头功夫那是顶刮刮的好,周娘娘的头发当初稀疏得连个钗簪都绾不住,给她三弄四弄。不也梳成那个一尺来高的王母髻。娘娘这就下旨去召她入宫吧。
小宦去公主府上传旨宣召的时候,保义夫人没有讶异,没有不舍,也没有太多的犹豫,略微收拾了一下随身的物事,就出来拜辞公主驸马。登轿上路时,保义夫人心底有些酸涩,事实上这怕是极好的了却尘缘的法子,是快要溺亡之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相见真的不如不见,不见了至少不烦心。保义夫人烦恼的源头除了驸马爷再无别人,然而就算驸马爷是个无价宝,也禁不住天天看,何况她只有在一旁偷窥旁观的份,却不能有更多的想法与盼头。而保义夫人靠得越近,看得越多,这心中的盼头与想法自是与日俱增,已至于暗自憔悴,不能负荷。
驸马爷现在不得志,所以呆在家里的闲时辰多,他身边有公主和姚夫人陪伴着,有清客帮闲奉承着,宴饮游猎,听歌赏舞,过得到也并不寂寞。
然而对保义夫人而言,越是傍靠着驸马爷,就越能感受他那咻咻逼人的气息,这气息总是让人战栗眩晕。于是夜深人静,独卧在床,只要一想起他来,内心便腾起一股火苗,先是缭,后是烤,“烘”地一下熊熊热烈的燃烧,烧得她口干舌燥,周身无力。所以保义夫人现在尽量地躲着他,躲得远远的,她怕看驸马爷的皱眉或是微笑,怕听到他的轻言漫语,更怕那一直追她追到梦里的咻咻气息。
驸马爷其实还是原先那个驸马爷,只是保义夫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保义夫人了。她象是一只蠢笨的飞蛾,看着红晃明亮的火光就情不自禁,将要投身而入。
幸好保义夫人还有最后一丝的警觉,她觉得照这样下去,或迟或早都会有她出丑卖乖的时候,趁现在她还把得住自己,她得离开这冤家——他是她命里的冤家,她一直这么觉得,尤其是那日她趁着驸马爷醉酒,在书房里与他有了一些亲昵的举动之后。
保义夫人从登上车轿,就一直强忍着没有掀起帘子回望,她这回重返宫里,就象鸟儿给赶进了笼子,她情愿呆在笼子里头,呆到老、呆到死,她只想关死自己这颗心。
保义夫人回到永寿宫是在四月的月底,她从承运八年十月初九出宫替张福妃取药到光正元年四月底回宫,屈指算来在外面呆了有半年,这短短的半年中发生了多少事啊,在保义夫人尚没有来得及唏嘘感慨的时候,另有一件天地失色,阴阳反背的异象出现于南都的上空。
五月初一的巳交午时,有天狗食日,其时天地晦暗,阴阳两昧,都人恐慌,于是齐集街市,敲锣打鼓,点放鞭炮,以吓退天狗。
唐太妃当时正躺在榻上小歇,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渐渐就变得昏黄灰暗,仿佛是乌云盖顶的模样,还当作是天要落雨,内使和小宦们这时却慌张的跑进来说是日蚀。
唐太妃吃了一惊,赶紧起身,出殿眺望,这时候天色已不甚明朗,天狗食日将已过半,内使们呆呆愣愣的都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唐太妃只得冲他们大叫:快,快去佛堂上香!求佛祖菩萨保佑!
内侍们正要奔出去时,天竟然就在一瞬间全黑了,唐太妃的心也慌张得象是跳不动,她呆若木鸡的站在殿廊下,不敢动弹,更不敢抬头朝顶上看。
好在这异象前后只有一柱香的功夫,“出来了,出来了,日头又出来了!”,欢声之中,暗影慢慢移去,一丝艳阳当空复照,宫里宫外这时都是人声鼎沸,唐太妃也不知不觉的松了口气,但仍是眉心深锁:天狗食日,这总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是因为皇上没能赴阙朝觐,所以上天示警,告诫下方?
心慌意乱的唐太妃叫来李润,问及他的看法,李润说:皇上贵为天子,事天当以孝道,事亲亦当以孝道……
唐太妃听了这话,有些怔怔无语。
每天散朝后的巳时到午时,弘文馆大学士陈广陵照例要为皇上传道授业解惑。因为门生是当今天子,陈广陵自然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况且陈学士腹有诗书,凡事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比如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问题古往今来,论述者众,然而在陈学士看来,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如导之向善,则善;若趋之为恶,则恶,所以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才是为人师者所最需注重的根本。
自从上次皇帝没能听从陈学士的教导,不肯趋长庆宫朝觐上皇,陈广陵就一直耿耿于怀,百善孝为先,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行不彰,则大道难行,也因此陈广陵特意在今天向皇上开讲这篇孔子述作、唐玄宗御注的《孝经》。
……孝乃至德要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終……
陈广陵在此告诉皇上,作为天子之“孝”应该“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看到皇上貌似有所不解,陈广陵又说:身为君王,应该尽其礼敬亲爱之心以侍奉父母双亲,如果皇上能亲自去做,天下的百姓自然就会跟从效仿,因而就能够以自身的仁德泽被众生,教化也能够因此施行推广,四海之内即使是外邦蛮夷,也会心向往之……
少帝心不在蔫的点了点头,跟着便张嘴打起了哈欠,陈广陵道:陛下若是困倦,请容臣暂退,此经留待他日重新开讲。
少帝皱眉说:不必了,此章讲完即可,先生想来也困倦了。
陈广陵正色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圣人且不敢言倦,臣又何敢言倦!况孝经章之三者,专讲诸侯之孝,陛下犹须揣摩领会。
陈广陵对此阐释说:身为诸候者,其位高贵,因其高贵,往往不易久长,而终遭危殆,所以身在高位者,不能骄奢跋扈,要遵礼守法,恭谦下士,要节约吃穿用度,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保自家的富贵,才能为国家社稷出力效命,才能协和庶民百姓使之亲睦友善……然而皇上登基,大权旁落,高位者流于贱俗,凡庶者窃权弄国,皆因不明这忠孝之道,故而贵贱不分,纲常颠倒,使人心生隐忧……
皇帝这时揉揉眼睛,打起了第二个哈欠,陈广陵正正衣冠,正要有所规陈,日食此时遂现于上空,天苍地茫,阴阳莫辩,宫里杂声四起,少帝情急,长身而起,一把拉住陈学士的袖子,慌慌张张的问:是什么事?竟何以如此?
陈广陵虽说见多识广,当此时亦觉得愕然,他携住皇帝的手,厉言厉色的说道:此是天谴,陛下不可不察!
少帝战栗不能言声,煌煌丽阳一霎间全无光影,昏黄晦暗乃至一团漆黑,此种不同寻常的异象加上身边陈先生厉言厉色的语调,让皇帝感受到一股难以言说的惊恐慌乱。
日食临空,天地苍茫,皇帝受天之命,自当谨慎戒惧。
皇帝身边以陈学士为首的一帮保傅们,都借此机会向皇上进言:吴王不过是一介武夫,治军或者是其所长,治国却未必有此能耐,象谏议大夫尚质在四月的朝会上所呈奏的几件事,几乎件件都点在要害上,奈何吴王全不以为然,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遂有天变发生。
鉴古可以知今,所谓藩镇、所谓匪患、所谓武人任事,都是遗害当今,流弊将来的祸端,然而吴王并不把它们当成大事。吴王眼里的所谓大事,就是专擅朝政,重用私人,就是搞乱天下以至于不可收拾,所以上天发怒,降此异象以告诫皇上。
帝在幼冲,权臣掌政,内有藩镇,外有僭伪,此情此景,令人揪心!陈广陵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想,状如一幅“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骇人图画。
然而越是景象骇人,越是不敢大声疾呼,他怕这陡然的一惊一咋,这连人带马或许就失足掉进了深渊。
日有食蔫,乃是上天怪罪谴责,朝中和国中都对此议论纷纭。然而此种异象,钦天监事前居然全无禀报,当拿他们开刀以塞那帮腐儒之口。吴王与张成义商议之后,决定将钦天监主事的大小官员下狱论罪,以负其责。
钦天监的监正上书告冤,年前禁营军士火焚官署,钦天监亦遭其灾,台阁损毁,不能登临,事后虽数番奏请,修缮营建之费至今并无拨付,且署中观天之仪,测象之表,当时尽为军士洗劫,投之熔炉,化为铜铅。毁物易,造物难,台阁好砌,而仪表之属难觅精工良匠打造校准,如今天出异象,臣等既无台阁可供观星测日,亦无浑仪简表可以推演其变,工无利器,莫之奈何,因此获罪,臣等岂不冤哉!
而谏议大夫尚质亦按捺不住,上章谏奏,言称京师所现日食,乃上天以灾异之象谴告人君,因为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有失,而国家何以有失,以至于上天感应,降此显兆?乃是不忠、不孝,失礼与无义;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又受命于天子,天意人心互为感应,此即所谓天人感应,若人君为政有过失,上天即示以警象,使人君感知天意而心生凛惧,若再不自省,天将发威逞怒,恐更有不测之祸,败亡之灾……
尚大人的谏奏获得了朝官们的一致支持,太师陆正己和太傅陈从圣请皇上付以廷议,天象示警,自不待言,朝廷当检讨究系何事震动上苍,致获天谴。而皇上也应该反躬自省,心常惕惕,上以应天命,下以顺民情。
年少的皇帝对于五月初一所发生的日食异象,也感到惊骇震怖,所以陆太师、陈太傅以及尚大夫等一干朝臣所言称的天人感应,他便觉得言之在理,天威莫测,怎不让人凛然生惧。
因为遂然发生的日食异象,朝臣们由此结成了朋党。原先吴王手里有年少的皇上,手下有禁军的南北二营,对付赤手空拳的朝臣自然不在话下,而现在天现灾异,朝臣们便可以借助天象示警,以古圣先贤所阐述的“天人感应”之说,代上天立言,吴王可以欺人,亦可以欺心,终究难欺皇皇上天!
清凉殿中的廷议,朝臣们众口一词的把京师发生的日食归结为“天谴”,这是上天降下的警示,而上天又何以现出警示?在于为政有失。既然为政有失,相邦宰执这些当国秉政者便难辞其咎。
虽然吴王和张成义等人坚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然而终究压不过朝臣们引经据典、异口同声的喧嚣。这也正是张成义最感到担心的地方,朝臣最好是一盘散沙,互不统属,否则一旦成群结党,则党同伐异,群起而攻,既难于辖制,又难以威服。
廷议非但没有平复吴王和朝臣们的纷争,反而更加蔓延扩大,从年初时以庶族寒士取代世族高门登台入阁的诏令,到四月间关于朝觐上皇礼仪的争论,此际都被朝臣们翻出来作为上下悖乱,贵贱颠倒的范例,因为有这些疏漏错失,所以上天才因此而震怒,日食也才会现于京师的上空……吴王身为相邦宰衡,对此岂能无动于衷,应深体天心,负其职责。
廷议之后,吴王宣布大赦天下,并且由于天现日食,将请皇帝下诏罪己,放宫中奴婢百人,另差遣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代为郊祀皇天后土,祈禳平安。
天象示警,罪在宰辅,这对于正春风得意的吴王不啻如当头棒喝,请教于张成义,得一妙计,心里方才稍安。
五月初三,吴王为表敬畏天威之意,将自家所食吴郡十县的封邑,舍去其三,作为自惩自罚之举。其余朝臣,上至三公,下至佐使,一律停俸三月,以应灾变。
京师的日食也引来方少师和唐节度的关注,两人都飞骑驰文,上达于朝廷,对于天象示警,谴此灾变,深深表达了边臣的担心忧惧之意。
“倒行逆施,必遭天谴!”
五月初一日食发生的时候,长庆宫最初也跟永寿宫一样陷入了莫名的惊恐当中,但是当到了晚上,上皇和汪皇后都估摸着回过神来,便觉得这天谴应该是冲着永寿宫来的,自然是因为弃父逼母,不忠不孝;犯上作乱,无礼无义的缘故,象这样的乱臣贼子,天不降谴示警,这老天当真是有眼无珠。
所以上皇在这天破例的置酒设宴,太皇太后、皇后诸妃以及储妃皇孙都会集于光明殿,酒行数巡,众人都努力的抑愁去悲,然而想到席散人去,悲愁复生时,这享宴终难成为欢宴,只为了不扫上皇之兴,皇后诸妃们都强作笑颜,聊为尽兴添欢。
“倒行逆施,必遭天谴!”这一天的酒宴上,被人说得最多的,自然也就是这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