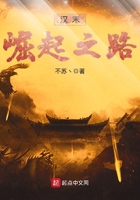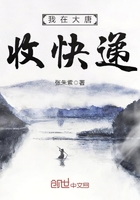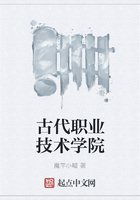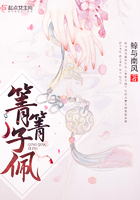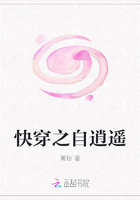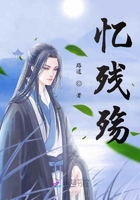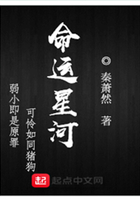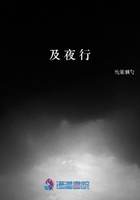皇帝是江山社稷的表征、是家国宗庙的根本、是臣民百姓的主宰,是维系外朝内廷、四海天下的灵魂所在,倘若灵魂暗昧不彰,则不免形衰体朽,里外皆难作长久撑持,以至于感染国家臣民,都将无精打采、浑浑噩噩,如同行尸走肉般了无生气。
虽然永寿宫的圣母唐太妃不爱听“皇上恐将一病不起”这样的丧气话,但不论是在后宫内闱还是各官署衙门甚至市井里坊,眼下谈论最多的总还是立嗣立储这个话题。
皇帝倘若一病不起,立储之事便刻不容缓,只是立谁为储,事关宗庙社稷,需要当今圣上之母唐太妃的点头首肯才能成事。只是唐太妃连自己的母亲吴国太夫人都能拉下脸给骂出去,宫里自然再无人敢在她面前提及立嗣建储的一字半句。
唐太妃这几天的心情既伤心又绝望,眼睁睁看着儿子在病榻上苦挣苦熬,自己却爱莫能助,太医们对此又几乎束手无策。面对此情此景,唐太妃简直就要发颠发狂,最终她把一腔怨怒都发作在身边的小宦跟宫婢们身上,只要一个不顺眼,就得拖下去挨板子,而要是犯了点小过错,则更是把人往死里打,打得那些轮值当差,近身侍候的内侍宫婢们每天都要焚香祷告,既然逃不掉一顿打,拜求老天开眼,千万别给打瘸了、打残了。因为前几日已经有十来个倒霉晦气的被打得皮开肉烂、骨断筋缩,奄奄一息的不知生死。
宫里除了这些小宦和宫婢们整日惴惴不安之外,就连那些有头有脸的执事公公也视皇上卧病的清凉殿为畏途,他们在少府令李润面前叹气诉苦,但就算少府令李润此际也劝解不得。圣母娘娘的心中此时除了儿子,便再无旁人的位置,假如能够换寿替死的话,想那圣母娘娘肯定也是毫不迟疑的。
因为皇帝的病,原本安排好的三位边帅遣使朝觐上皇的事先是被耽搁,继而就给取消了。使臣们虽然无奈也只能望着长庆宫的宫阙遥遥磕拜,然后各自离京复命。
但是替天子守边的镇帅在京师都有其行馆,天子脚下若有什么风吹草动,行馆里的属吏便会将种种消息传闻快马送出。而皇上患病可是件天大的事情,各节度的门人手下都不敢怠慢,一有消息传出便赶紧派人禀报各自的主公。
三位镇帅中得知消息最详最确的应该是齐鲁节度大使唐会之,别人的手下尚在路上打马狂奔之际,他的手头已经一连接到了好几份邸抄快报,消息的便利、来源的可靠则都要归功于他那位坐镇于京师的贤内助——安国夫人陈氏。
安国夫人陈氏最初听到皇上患病的消息,立刻便想到宫里去探明究竟,但是宫里为了封锁消息,并不许朝官命妇们任意出入,别人对此或许就作罢而回,但是陈夫人却是百折不饶地要探求一个准信。她虽然不能进宫,但却可以过府。所以每隔一两天,她就要去看望唐相国的偏房、赐封为凤阳郡夫人的林氏,又或者请林夫人往来相叙。
妯娌间的交情一向谐好,所以陈夫人想套林夫人的话并不太难,而林氏随在吴国太夫人身后进过两次宫廷,亲眼探看过皇上的病情,且又得知一些隐情内幕,一俟陈夫人动问,便滔滔不绝的说起自己的观感来。“唉,皇上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林夫人见自己一句话便把陈夫人给惊住了,不觉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都是勉强不得的事……”
见得陈夫人呆在一旁并不作声,林夫人又道:若皇上不幸而弃天下,安国夫人以为,子侄之中何人能够承嗣大位?
陈夫人收敛心神,正容道:这话可说不得。皇上是天生洪福之人,自有上天神佛庇佑。
林夫人微微一笑:安国夫人是自家人,所以说些内情到也无妨。我曾听太夫人和我家大人商计过此事。皇上年少无嗣,因而只能从子侄辈中挑选皇嗣,如此则又非青华宫的两位郡王爷莫属。至于所择何人,我想安国夫人必定是心满意足的。
林夫人的一番话,陈夫人当然心领神会,当下却说:既然都是自家人,只要有我十分,那么自然少不掉你那五分……
林夫人说:安国夫人言重了。到时候咱们家还不是要多多仰仗于夫人一家。
陈夫人说:岂敢,岂敢,此事全仗相国大人和夫人之力,恩高情重,实在难以报答万一,妾和外子亦当时时感戴在心,岂能有负于人,自蹈不义。
闻此喜信,陈夫人的心满意足自不消多说,所以前脚刚送走了林夫人,后脚就差遣可靠的家人去给老爷通风报讯。
一切果然都不出她的预料,都说是风水轮流转,不经意间就转到自家门上来了!陈夫人如今别无他事,只一心一意地盼着宫里早些传出皇帝大行的噩耗。也因此陈夫人在家书里频频告诫老爷:外孙胜儿有望立为储贰,承嗣大位,此时此际老爷决不能再伙着他人胡闹折腾,应该偃旗息鼓,静候佳音才是。
使臣朝觐的事最终化为一场泡影,长庆宫的二圣对此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怅然。因为在这之前,上皇对自己在召见使臣时该作的应对问答,已经推敲酝酿了好久。那都是些极富深意,值得这些节镇边帅们去研议领悟的言语,也是上皇牺牲了若干个不眠之夜才换来的深思熟虑后的想法。
可惜,上皇和皇后的一切努力全然是枉费心机,当二圣还在倚门盼望的时候,边帅们的使臣都已经踏上了出京的官道。
二圣虽然猜出这其中肯定是因为某种缘故,但是上皇和汪皇后都没有想到,使臣不来朝觐上皇,竟然是因为永寿宫的少帝罹患了重病。因为始终猜测不透情形,二圣心里都是纳闷得很,这情形直到大长公主进宫探视太皇太后,闷在葫芦里的秘密才终于被揭开。
燕国长公主在带来了少帝患病消息的同时,也一并带来许多坊间的传言。长公主自己其实也没有见到病中的少帝,但尽管永寿宫现在千方百计地想封锁皇帝卧病不起的消息,可是宫里的任何事又怎么瞒得了她那身为散骑常侍的义子。何况,朝廷都已经宣布大赦狱中的刑徒,这自然是因为皇帝的病情益发加重了,所以需要借推行仁义,来为皇帝延寿续命……
听燕国长公主这么一说,二圣便都恍然,跟长公主的想法一样,长庆宫的诸贵人也都认为新天子别无他选,肯定是元献太子妃唐媛的儿子皇孙胜奉天命承大运为至尊。
燕国长公主说起皇孙胜将要奉天承运时,语气颇有点不忿。所谓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皇孙胜若即了大位,她这个大长公主跟吾皇至尊的关系便又疏远了一层。
“唉,其实朝臣们的心思不说也知,都在吁请上皇复位听政哩!再说皇孙胜,一个抱在手里的娃娃,便即了大位,又能有什么作为?还不是任凭他人操弄摆布!”
“朕居深宫,形同幽禁,如何能作此奢想?”上皇现在极有自知之明,在听了长公主的话后,只是摇头苦笑。
汪皇后在一旁,这时却也插了句话:连皮带骨统统吃下去的东西,可曾见过有人会心甘情愿的吐出来?
燕国长公主说:那也未见得!这人要是吃得太撑,保不定就要往外吐!
上皇微微皱着眉头,心情似乎有些沉重,沉吟了一会,方才自言自语地说道:想那唐会之和唐觉之毕竟只是同族共祖的远房弟兄,而皇孙胜却是他的嫡亲外孙,这里面的亲疏远近,他自然可以惦量得清楚明白。再说太子妃也是一路历经磨难,对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自会多加分辨,如今她能借此熬出头来,诚属天意怜悯。依朕之见,胜儿如果承嗣大统,于我长庆宫未必没有几分益处。不过,一山难容二虎,昊儿若丧,胜儿嗣位,当是明争暗斗之始,但不知当国之人容不容得朕等袖手居闲。
上皇最后这番话说得有些凄楚,燕国长公主听后,马上为之开解:情形再坏,怕也坏不过今时今朝,上皇又何虑之有?二虎若能相争,岂不是有大把的笑话可看,我倒乐于冷眼瞧那么一瞧……
汪皇后叹说:人在局中,岂袖得了手,抽得出身?唐觉之也是无可奈何罢了,但凡有他人可立,又哪里轮得到胜儿。都说退处宽闲,悠游岁月,吾也怕到时候心虽想而力不能。
大赦天下的诏令,皇帝在登基时已经颁布过一次,时隔不到一年,朝廷又再次宣布大赦,因而这一次能够沐浴浩荡皇恩的刑徒,举国才不过寥寥千数人而已。但依照历代旧例,举凡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的死囚并不在赦免之列。
遵奉朝廷的大赦令,慎刑司也放出一批囚系于狱中的宫婢内侍们,但是张庶人之子和他的奶妈以及保义夫人郑氏在不在赦免之列,慎刑司的内使公公不敢做主,只得行文呈告于少府令李大人。
李润也觉得事涉宫闱隐秘,不便擅专自主,于是请命于吴国太夫人。
吴国太夫人这几日,一来忧虑皇帝的病情,二来关注于立储的大事,心焦神悴,一时倒忘记了这档子事,听了李润的禀报,先是一怔,继而便道:敢问李大人于此有何高见?
李润拱手说:事涉宫闱隐秘,卑职岂敢置喙。
吴国太夫人道:你说来听听也无妨。
李润这便小心翼翼地说:回太夫人,卑职奉上命推问细故,如今仅就张庶人之子而言,其人身在襁褓,尚未学语,自然无法审得;其奶妈乃宫外所雇民妇,不通文墨,更不识道理,一问而三不知,且有出首之功,圣母娘娘亦曾予以宽贷;至于保义夫人,所行所为简直是糊涂透顶,起初未有参与,知悉后隐瞒不报,所谓失足成恨,全系咎由自取。强究细推,卑职以为,此事皆寿南山一手操弄,为此卑职曾仔细讯问过八喜堂的旧人,皆云寿南山原即与张庶人相善,所以趁着那日宫中兵乱,竟不惜以身试法,为之藏匿掩瞒,犯下此滔天大罪,然而天网恢恢,终究疏而不漏,于是事泄败露,寿南山自知死罪难逃,故而畏罪自缢,以此逃避惩戒。至于寿南山的手下,都已经奉旨杖杀,现朝廷大赦,恩泽天下,罪人犯妇如何区处,下官敢请太夫人示下。
吴国太夫人点头说:的确可恶!那奶妈既然自首,又蒙恩宽贷,姑且算她命大,打二十板子,就此赶出宫去。保义夫人知情不报,原本应该坐罪论死,念其曾有微劳,且遇朝廷恩赦,夺其品阶,发入浣衣局充作役使。张庶人之子,暂先收置在慎刑司的监房,这贱种虽说留不得,不过皇帝尚在病中,杀之恐怕不祥,可听其自生自灭。
李润俯首称是,回头便照此发落众人。沈家娘子受杖二十,撵之出宫;保义夫人按规矩原本也要受杖,但李润以为,保义夫人曾为命妇,其品阶足可抵得杖刑,所以饶了她这顿打,只是发往浣衣局充作了洗衣妇。至于重新收入慎刑司监房中的皇三子,既然上头吩咐任其自生自灭,而不是立刻弄死,可见还是给了活路。李润因此格外关照慎刑司的手下,要他们弄点米汤糜粥之物,仔细喂养,不可闪失。
慎刑司的诸内使皆道:此事何需大人操心,皇三子虽称贱种,亦是贵胄,再说大牢里也未必不出天子,小的们都知道如何安排。
内使们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李润,汉季宣帝之旧事岂用人说。当下李润把脸一沉,斥道:贱种贵胄,非我等能够妄论,都不怕掉脑袋了么?
内使们见得少府大人发怒,亦都变了脸色,诺诺然拜辞而退。
再过得几日便进了腊月,皇帝依然是不死不活的高卧床榻,如此看来,不论唐太妃喜与不喜,这立嗣建储的事怕是再不能拖延不决。吴国太夫人于是叫来唐相国和张太保商量此事。
“依我看,这就打发人去长庆宫把那孩子抱来,不管皇帝有无变故,这孩子先养在宫里总归没错。”
唐觉之说:话虽如此,青华宫的太子妃却如何安置才好?也一并接来宫中?要是让她们母子睽隔,却又大违人情常理,且会之系嗣君外祖,以其外戚之贵,又岂肯久居人下?再说论起辈份,圣母娘娘与唐媛之子乃是祖孙,查考历朝诸代,又哪有庶祖母尊处慈闱而听政颁令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此子若立,朝臣们定然要借此生事,节镇边帅也会呼应唱和,前朝后廷自然难有片刻息时。
吴国太夫人斜看了儿子一眼,悠然说道:太子妃好好的侍奉二圣,倒是接她来做什么?难道当祖宗给供起来不成?皇帝既然可以崩,自然也可以立,至于立谁不立谁,当要看权在何人之手!现在后廷所奉唯圣母娘娘懿旨,外朝又全凭吴王谕令,建储立嗣的事,自是由不得旁人插嘴。唐媛的儿子如果能够承位,这就已经圆了她的大愿,岂能再因此生出其它非分之想,再说这原本也是为她好!至于唐会之,身为节镇,实同外藩,其意愿早已满足,此时若再有无厌贪心,却不怕生出祸患来么?祸福无门,惟人自招,保不定就是在自取其辱。再说,放着属于自家人的皇孙胜不立,难道却去立周家的那个孽种皇孙捷?
唐觉之道:皇孙胜和皇孙捷都无承嗣之望,儿子以为宫里另有个现成的人儿,可以议立。
吴国太夫人奇道:宫里另有人可以议立?立谁?我怎么不知?
唐觉之说:母亲大人莫非忘了永寿宫里尚有张庶人之子,可堪承位。
吴国太夫人失声道:你说让那个贱种承位?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天底下就算无人可继,也轮不到他来承位。
唐觉之道:本来这都是张太保的意思,太保大人前些日子跟儿子一说,儿子才如梦初醒。试想,若以唐媛之子继立,内则尊其母,外则崇其外祖,这两唐相竟,犹如二虎相争,其中必有死伤。而要想身家保全,除非辞位归闲,寄身于方外,或能免此争斗。
吴国太夫人脸色一沉,久久未语。
唐觉之见状又说:张庶人之子身在襁褓,家族星散,自身无依无靠,若立之为帝,亦不过是人前儡傀,幕后皮影。更何况圣母娘娘如能将张庶人之子收养为己子,则子凭母贵,母以子荣,圣母既为嗣君之母,自然可以跟从前一样尊居慈闱而听政颁令,朝臣对此亦无话说,即便长庆宫也难以借此出头。
吴国太夫人一叹道:话是不错,可是不立皇孙胜,那唐会之怕是立刻就要翻脸……
唐觉之笑道:太子妃、皇孙胜都在吾手中,他投鼠忌器,未必敢于翻脸。
吴国太夫人有些被说服了,当下却苦笑一声,道:想不到这贱种天生的好福气,竟白白捡得一个大便宜。哼,我这身上的伤才刚好,倒是又被张庶人遗下的贱种再插上一剪子!
唐觉之宽慰道:虽云便宜了别人,好处到底落在自家,再说张庶人行刺谋逆之事,天下皆知,圣母娘娘以德报怨,宽厚待人,哺育诸子,深具母仪天下的风范,足称大贤大德,天下又敢有不敬不服者。
吴国太夫人心有所动,当下点了点头:那这这么办吧。娘娘那里改日我再和她说说。
建储立嗣之议,太保张成义由始至终一直参预其间,虽然他身在殿中未置一词,不过既然唐相国都照他的意思说了,自然便不须张成义再多费口舌。
建储立嗣本来无关他事,但是张成义私心作怪,且又受了他人撺掇,所以就插手管起这宫闱之事来。
张成义本来也想过,假如立皇孙胜为储君,那唐会之或迟或早,得代为天子辅政,而自己乃是相国的心腹亲信,所以应该不会为唐会之所信任重用。再说,太子妃唐媛既为天子生母,将来终有膺尊号,称太后的那天,到时候若再推究起当年上皇内禅及元献太子之死,旧事重提,定案推翻,则自己绝对难逃干系。
不立皇孙胜,议立皇孙捷,道理一样,周家恐怕又要借此卷土重来,何况帝系仍旧归在元献太子一脉,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是以,当张太保的军中熟人、少府令李润在宫中与他偶遇,两人彼此寒喧之际,少府令李大人虽然只略略提及了皇三子的事状,张成义便立刻醒过神来。这可真是上天赐予的良机,若不能牢牢抓住,将来必定后悔无疑。
省时度势,眼下的确惟有张庶人之子可以议立,此子无依无靠,若能得而为帝,亦只能以圣母和唐相国为身后靠山,即便长大后亲政,追怀其本家亲族,查究凌虐其母的元凶,论起这大逆之罪,也只罪在唐氏一门。至于太保自己,既有首倡之功,又有议立之劳,更兼辅佐之勋,自然立于不败之地。
张成义一番思虑,主意拿定,当即说与唐相国,相国大人想通了这一层,也夸其足智多谋,两人精心谋划,晓以利弊,终于说通了吴国太夫人,而太夫人那里一旦说通,事情自然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