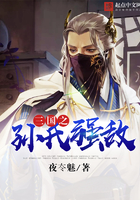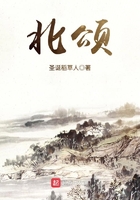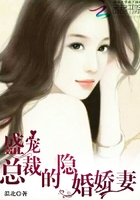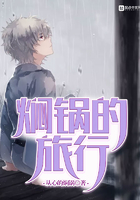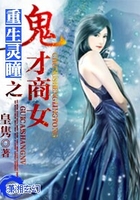正月正,家家户户闹花灯。本来元宵赏灯例为三天,但今年因皇帝大病初愈,危而复安,举国都要共此欢庆,所以又额外多加了两天。
跟民间一样,长庆宫各处殿堂和亭廊也毫不例外的挂满了花灯,长庆宫的这些精巧别致的花灯都是永寿宫的唐太妃和少帝特别孝敬献呈的,因为皇帝既要与百姓万民同欢,更要与家人亲长同乐。
然而少帝的孝心并不仅仅体现在这区区几盏供奉献呈的花灯上面。少帝现在想缓和一下自己和上皇之间生疏冷淡的关系,这也是他母亲唐太妃的意思。皇帝能够大难不死,长庆宫派来问诊侍疾的徐神医功不可没,然而细加推究,上皇老牛舔犊的眷顾爱护之情亦不可抹杀。
而少帝自从病愈之后,更加坚信自己为上天神祗所庇佑,是真命不二之主,因此对于退位闲居于长庆宫的上皇便没有先前的那等忌惮。既然无须忌惮上皇,少帝隐藏不露的孝顺之心便油然生发出来,所以在元宵节群臣入宫朝觐贺节的嘉礼上,少帝亲口对朝臣们说,朕要将这额外增添的二天节庆来与长庆宫的二圣同欢共度,以恪尽身为人子的恭敬孝顺之道。
皇帝主动显示的诚意孝心自然赢得了朝堂上臣子们的一片交口赞誉。国朝向以仁义孝道为标榜,因而只要皇上能够以身作则,恭行这些仁义孝顺之道,则海清河宴,天下升平,尧舜之世应当可以复期。
皇帝虽然年少,但也知道臣下的这些赞誉与恭维,不过是一种寄望和期许,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会把它当真。唐尧虞舜这些上古之事,本来就荒不可考,或许便如皇上爱看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一样,皆出于后人的猜想与臆造。否则单就尧舜之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清平盛世,这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先贤大儒们何以竟无一人能够说得分清明白?即使遍翻典册史籍,往往只是粗疏几行、寥寥数语而已,至于后世大儒所作的详述与追叙,也不过都是些人云亦云的姑妄言之和且疑且惑的姑妄信之。
少帝还记得自己曾在内府所藏的古本《竹书纪年》中看到过与正典史册中大异的记载。象竹书中说: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书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少帝因为是受禅而得位,所以对尧舜以来的禅代之事颇感兴趣,就此请益于陈学士。陈学士却对竹书所记嗤之以鼻:尧舜之事,见于三坟五典,传载有据,且有先圣大儒为之追述补记,岂可不信?而汲冢所出的几片残简谵言妄语,不知所云,非议古圣先贤,肆行诬蔑之语!此等坏人心术、谤讪倡乱之书,朝廷决当毁弃,不可使之存留于世!
陈学士说这话时,面红耳赤,义愤填膺,少帝也就不准备往下深究这个问题。虽然少帝在私心里以为,舜囚尧,自是因为尧之德衰,所以舜帝囚系唐尧亦属未尝不可之举。但无论如何,尧舜这两位上古的圣王,其以身作则恭行仁孝的事迹,应该不会有假。即使其中有假,隔了这千年万载之后,其假也足以乱真!再者如果确信汲冢竹书中所记是真,那么这上古三代的仁义慈孝之说难道竟是幌子不成?如此再推而论之,国朝所称的以孝治天下,以仁抚万民,自然也该是一句欺天骗人的假话空话了!
少帝决定效法尧舜,率行仁孝。于是在正月十九的这天大早,少帝率领群臣来到长庆宫朝觐他幽居在此的上皇父亲,其间奉觞祝寿,歌舞娱亲,足以显示其为人子的依慕与孝顺。
吴王唐觉之虽然没有参与上皇父子之间的欢会,却也没有干涉皇帝的这次朝觐,皇帝的病能够痊愈,这对唐家而言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喜事,再说幽居在深宫禁苑里的上皇想来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何况等过完了这两天节庆,一切还不都是原样照旧。
长庆宫的太皇太后和太上二圣对于少帝显现出的恭敬孝顺自然欣喜之极。临安殿上,宴乐由旦至暮,其间歌舞蹁跹,百戏杂呈,父子之间、君臣之间都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当皇帝起身,奉觞为太皇太后和太上二圣敬酒祝寿之际,上皇笑呵呵地建议座中的臣僚们应当咏诗作文以记述今日之盛。群臣无不响应,上皇和皇帝这一天各自作了一首御制诗以叙其盛会,而臣子们亦不肯后人,当下搜肠索肚,觅词揽句。臣子们的所作经上皇的评点玩味,以大学士陈广陵诗文俱佳,足称魁首,得上皇赐以文房四宝并御酒金帛若干。
元霄节固然热闹,但是民间也好,宫里也罢,多不过就是额外又闹腾了两天。等到节庆一过,一切便如吴王所料,复又原样照旧。
父子家人欢聚一堂,把酒论诗,共庆元宵佳节,长庆宫的上下人等欣逢盛会,个个与有荣焉。内廷令王守礼不想破坏这难得一见的喜庆气氛,因此刻意隐瞒了留香馆寿妃那边的事,所以直到正月二十日,客去人散,宫里开始陆续摘下花灯之时,太皇太后和上皇、皇后等人方才得知寿妃已经亡故。
虽然寿妃的亡故显得有些突然,只是宫里这些年历经了周太后、太子晟和张福妃诸人之丧,所以大家在言语间,都把寿妃的薨逝看得十分淡然。
象陈太后就说,寿妃的病根应该归结为自怨自艾,因而自弃于人世,不然旁人都活得好好的,她怎地就一直恹恹的凡事总想不开?
汪皇后则是触景生情,她想起了自己英年早逝的晟儿,因而便恨恨说道:若非乱臣贼子祸乱国家,宫里岂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这些丧乱之事?冤有头,债有主,上天明鉴,一切当有索还之时。
上皇这时候想得最多的却是吴寿妃所擅长的那些洛上旧风味,寿妃既逝,上皇不禁感慨,昔时佳味,此后大概是再难尝到。
上皇对于洛上风味的留恋提醒了陈康妃和王宁妃,趁着寿妃亡故,留香馆的人将要云离星散之际,抢先下手留住那些厨艺精良,身手不凡的食官膳夫们。于是寿妃生前所用的掌灶大厨,一半归了王宁妃,另一半则跟了陈康妃,至于其他人,除了留下几个负责洒扫上供,大多数都拨入其它殿堂以充役使。
寿妃无寿固然是件令人惋惜的憾事,但是别宫别殿的娘娘总还要把日子一天天的捱下去。而在这冷清寂寞的长庆宫里又有什么事能比吃吃喝喝更加重要?所以能够把吴寿妃身边的厨子留下来使唤听用,也算是王宁妃和陈康妃在这元宵佳节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收获。
两宫谐好,父慈子孝,这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场景,既合天心又顺民意,几乎就是众望所归。但是世上的事往往总是相悖互逆,有人满心欢喜的同时必有人在背后切齿痛恨。比如安国夫人陈氏,比如元献太子妃唐媛,比如出镇在外的齐鲁节度大使唐会之。除此之外尚还有高居朝堂、节镇边关,遇事常常袖手,惯作冷眼旁观之态的一帮臣子。
安国夫人陈氏的这个年节过得意冷心疲,大不如意,但尽管如此,大年初二那日,她还是打起精神前往吴王府向吴国太夫人拜年请安。
吴国太夫人是唐氏一族的活祖宗,她身为侄媳,且又是唐会之的贤内助,这人情往来,交结世故便不能不讲究个面面俱到、无可挑剔。
因为议立皇嗣的事,吴国太夫人在见到陈夫人时倒是含蓄的表示了一点歉意,但是陈夫人浑似不着意。
陈夫人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唐字,既是自家人,太夫人和王爷又岂会不关照。
吴国太夫人赞许道:吾家的媳妇就属你最明事理!呵呵,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别过了太夫人,陈夫人又往林氏那边转了一转,妯娌们之间说话自然无须顾忌,林氏说:都是我嘴快,谎报了军情,却不道尚有个庄王昃。还以为姐姐会嗔怒责怪,正念着要到府上去拜望请罪,不想今天姐姐倒先来了。
陈夫人笑道:当初我是怎么说的?皇上乃天生洪福之人,自会有上天神佛庇佑!这话你总还记得吧?可见我是全没把它放在心上。
除了到吴王的府上拜年,京中别人家的邀宴陈夫人也是一场不落的亲临,反而她女儿的太子东宫春华宫,节庆间她始终未曾去得。太子妃唐媛怜其母独在京师,这年节过起来无滋无味,早早就邀她进宫作伴,可都被陈夫人一口推托。
陈夫人自觉没脸面去见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唉,人越是有大指望就越是经不起挫折,然而挫折倒也罢了,可恶之处在于欺瞒与哄骗——明明已经有了一个皇孙胜,为何又弄出个庄王昃来?
象唐觉之的小老婆曾经暗示自己的那些话,现在看来都是在扯大谎,编瞎话,其目的不外乎是先稳住这一头,再算计那一头。自己偏偏就着了她的道!火急慌忙的写信给老爷,要他偃旗息鼓、静候佳音。这不是糊涂透顶又是什么?陈夫人只要一想起这些来,牙根子就会咬得“格吱格吱”地作响。
立嗣建储的事是引动陈夫人妇人之怒的主因,她连接写了几封信给唐节镇,将自己受骗上当的经过细细道来,信中自然怨天尤人,大倒苦水。她自身所受的委屈到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事,可是自家的大伯、堂堂的吴王岂能这样弄奸使诈,言而无信?不说是自家的弟媳,就算是对待外人,也不该如此下作无赖……他这分明就是瞧咱们不上!自然,咱们跟他家又不是什么嫡亲正经的兄弟,所共的不过是八百年前的祖宗,但凡有好事,又哪里轮得到咱们……
知夫莫若妻,陈夫人知道哪些话能够把人说笑,哪些话却能把人说跳。她觉得自家的老爷是该跳上一跳了,不然这老实头似的,到哪里都被人欺压!
元宵节后,依然春寒料峭。驻节于边镇的节度们加快了“合纵连横”的步子。这一次齐鲁节度大使唐会之取代了洛都留守方大用成了“合纵连横”的首倡发起之人。
跟安国夫人陈氏一样,唐会之也为自己所受的愚弄而怒不可遏,所谓天子一怒,伏尸千里,诸侯一怒,奋发其威。唐会之虽非天子,亦算不得诸侯,冲冠一怒之后当要如何如何,自然得冷静的加以思忖一番。
便拿唐会之自己来说,虽然也是晋阳唐家的子孙,可惜跟老太师唐明一系是疏枝远宗,当年便想亲近热络也始终是热络不上,至于唐觉之更是从没把自己这个前来投靠的远房族弟放在眼里——如今他凡事皆小瞧自己,自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想当年自己人在洛都,为谋取一官半职,好养瞻家口,成日奔走求告于太师府上,饱受了人前冷眼、人后恶语不说,还要被族兄唐觉之呼来喝去,其状直如卖身给唐府为奴作婢的书童小厮一般,虽说遍历了这种种苦辛,到头来却不过是给荐到闲曹,充任了一个闲职。
闲曹闲职既无权势亦无任事,到手的官俸自然微薄,且又无各处的孝敬上门,因而实不足以养济家小,更遑论光大门楣了。京中米珠薪桂,居大不易,闲官散职们要想升官发财,只有各寻门路,谋求外任。这外任若是放在繁庶州郡,除朝廷薪俸之外,立时即有大把的外快可捞,只须在任上混个三年五载,贫儿便能乍富,寒门或变巨室。唐会之当时便动了这个心思,一心一意求放外任,可老太师偏偏不肯加以引荐提携。
幸亏自家娘子贤德,为求得外任,不惜将嫁妆箱笼之物一齐变卖,又写下契书许以高利借得若干银两,凑足了所需之数,购下西域罕异的大珠一对,求托于当时的太宰周如喜门下,唐会之这才得已授任荆湘安抚使一职。
任职地方,便是一方的父母,既为一方父母,则辖下的子女奴婢又敢不奉献孝敬?便日常公事亦时有银钱税赋经手,所谓雁过者拨毛,经手者不穷,此诚是哉!只是荆湘富庶,眼红心热者众,唐会之并不敢贪心,原也只想做上一二任,然后置田买宅,安心适意的当个富家翁、长乐佬。却不想自己命中原有吉星高照,这赴任荆湘竟成了日后步步高升的跳板。
当上皇因为靖逆起事而巡狩到此,自己从龙护驾立有大功,于是直上青云,得已封爵拜相,且更与皇上结了儿女亲家。如今自己好歹也是荣封郡王的显贵重臣,唐觉之岂能再以当年的冷眼无视自己的存在?
想想自己凡事往往都尊他一声大哥兄长,可是这大哥兄长可有半分顾及自家子弟?——这也正是唐会之心中所恶极恨极之处。就算没有陈夫人的来信,唐会之也猜测得出京中的这些遂生的变故。立皇孙胜为嗣,口惠而已,皇帝若是真弃了天下,唐觉之自会更立新帝,再摄国政,立别人的外孙,让权于旁人,那是想也休想。夫人到底是妇人,见识有限,自然没能想到他玩的这些花样经。
唐会之目前并没有扶立自己的外孙登基为帝的念头,京中的上皇和皇上皆在,自己纵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也是在遥遥不可预期的将来。只是将来的事虽说要留待将来,但是眼下倒也不妨伸上一脚,使人有所留意。
盘算当下,自己虽然身为节镇,然而势单力孤,若是仅靠自己的实力,则胆气始终不壮,强欲与人翻脸,非但难以济事,更恐怕是招祸上身。
试想族兄唐觉之所以能够威逼天下,叱令诸侯,在于手中挟有天子,这亦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反观自己当前所能仗持的又有何人?既无所仗持,诸事便难以马到功成。
这样的念头在唐会之心里始终转来转去,世事翻覆多变,最是无情,自己小心谨慎一点总不会有错。只是再要叫他腆脸厚颜的臣事于唐觉之,则心底的这股气也非憋炸了不可。受气只能一时一地,又岂能一生一世?
唐会之因此油然想到,唐觉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假如自己能够巧借东胡之力来为我所用,则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朝廷或是吴王都不能不予以重视。
这思路一旦打通,唐会之身心顿时感到一阵过去从未有过的轻松惬意。仔细想来,自己未必没有凭借,象北边的东胡,西边的方大用,都可以借助其力。甚至南边的许成龙,虽然地处偏僻,遇事不能指望其倾力相顾,但是摇旗呐喊,助威助势总是能行。节镇三帅之间原来便有相共进退的盟约,这回也只要重新立誓结盟即可。
朝廷一向不敢于得罪东胡,且自己又独掌与东胡交结联系的孔道,此来彼往,交情还算深厚,所以今后若想事事如意,东胡背后的支持必然不可缺少。
再说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事,身为边帅,驻节一方,要想立命安身,长保盈泰,便不能不和周边交结。假使机缘巧合,能够化敌为友,相互帮衬,则不啻为皆大欢喜的上善之举。
而且据他打听得来的消息,身为洛都留守的方大用如今便跟长安的靖逆眉来眼去,勾勾搭搭。长安的靖逆原是方大用昔日的故主,但自从方大用叛主投南以来,双方理当视如寇仇,然而世事反反复复并无常态,唐会之若不是手头有长安送来的确切密报,当真打死都不敢相信方大用与靖逆勾搭是确有其事,半点不假。
唐会之思谋略定,一则使人前去东胡,献礼问好,一面派人往洛上传话:吴王做事,过于擅专,自己与他虽是同族,然道不同不相与谋,且忧灾畏祸,故而常思宗族保全之策。弟受上皇恩重,无时不思报答,只恨势薄力孤,不能安定天下社稷,退求其次,但求能存性命,避灾祸于当世,明公如有安身立命之计,不妨直言以告,弟当洗耳恭听。
方大用便带话给他说:你我皆受上皇深恩,理当为上皇讨个公道……吴王擅专,必不能久,如能令其自乱自溃,则社稷自可安固。贤弟背靠东胡,想来自有借力之处,愚兄正面应对靖逆兵锋,却不敢稍存懈怠之心。
方大用一点也不傻,唐会之想出这借力使力之计,方大用其实也早有谋划,只是跟唐会之的想法略有不同,方大用并不关心谁人会当南都的皇帝,他只想用心经略自己脚下的这一方地盘,然而中原自古便是四战之地,要想在此存身立足,自然殊非易事。所以当前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局势,当是南都忽然溃乱生变,四方诸侯趁势而起,共分其利,各取所需。
唐会之的传话,隐然正合方大用之意,成王成霸,存乎一心,万事俱备,只待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