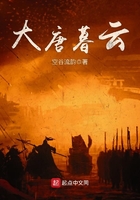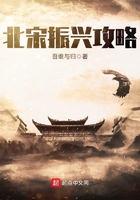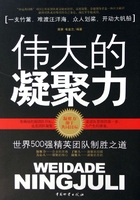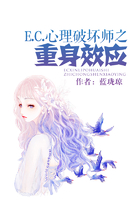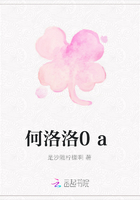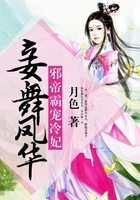六月的天气刚刚才有些燥热,唐太妃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却又犯了。唐太妃的这个毛病犯得有些蹊跷,内侍宫婢私底下都以为娘娘怕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只是按理说,深宫大内本是个瑞气钟祥、贵极富极的地方,自有满天的神佛时时予以照看护持,邪祟妖物什么的避之都唯恐不及,哪里还敢近得宫里贵人的身傍?
然而就在大前天的夜里,圣母娘娘为梦所魇,醒来后所表现的征兆就跟中了邪是一模一样。当时她“啊呀”一声,大汗淋漓的从床上一跃而起,呼吸急促,脸色苍白,直愣愣的眼光张惶地朝四下里乱看,身子也哆哆嗦嗦地象是受了莫大的惊吓。
内寝里值宿的宫婢都赶紧上来问安侍候,惊魂甫定的圣母娘娘这时候却抚着胸膛,颤声说道:“你们都看见了没有?有人压着我的身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怎么挣都挣不脱……哎呀,当真吓煞人了!”
宫婢们赶忙说:娘娘只怕是睡迷住了。
唐太妃怔了一怔,点着头说:嗯,我大概是睡迷住了。
唐太妃说这话时,惊容未散,语气也显得有点勉强,宫婢们看在眼里,只忙着好言好语的安慰。虽然惊梦而醒有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唐太妃所做的这个梦实在是诡异莫名,当真说出来的话只怕要吓坏身边的一干子人。
她在梦里果然看到了邪物,最初是一个,然后是二个三个,象云彩一般轻忽无声的飘来,飘呀飘的就飘到了她的床头,当先的那个老邪物伸着脖子看着她,而她好似正在熟睡,又好似睁眼醒来,她觉得那老邪物冲着她阴恻恻地笑,唐太妃尚未及惊叫奔逃,那邪物忽尔就翻上来压住了她的身子……
刹那间,唐太妃象被绳捆索绑,想喊喊不出,想动也动不了,浑身汗出如浆,头脑里却异常清醒分明——她看得见那老邪物阴沉铁青的面孔,并不青面獠牙,狰狞可怖;她也听得见这邪物磨牙似地说话:“跟我走吧……这里岂是你能呆得的地方……”,叽叽嚓嚓的声音,听上去干涩吃力,就象把小锉子在唐太妃的心尖尖上面翻来覆去地锉着……
唐太妃惊惶骇惧,几欲催心裂胆,她甚至情愿晕死过去,这样她就无需再去面对这越逼越近的面孔……她在梦境里痛苦不堪地挣扎,直到灯花“卟”地一声爆了,她“啊呀”着从床上坐起。
梦里看到的景象,在梦醒后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当着宫婢内侍的面,唐太妃什么也不敢多说。宫婢们说娘娘大概是睡迷糊了,唐太妃自己也胡乱地应着,虽然她知道她决不是睡迷糊了,因为这个睡梦中压住她的身子,又口口声声要带她走的邪物,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慈圣庄肃周太后!况且当唐太妃从梦魇里惊醒,尚还能够回想起那闯进自己梦境里来的,似乎还不只是周太后一人,那些故去的亡魂,象福妃张氏,象废太子晟,象太宰周如乐,都追随在周太后的身边,在她幽深的梦里影影绰绰地出没。
恶梦惊魂,唐太妃这一夜再没敢合上眼睛,在她的催促之下,寝宫内外到处都点上了灯烛,然而在明晃晃的灯烛之外,唐太妃觉得那些亡魂和邪物并不甘心就此离去,它们仍然在深宫里徘徊,在阴森幽暗处窥视,随时准备着伺机而动,摄取人的心智魂魄,而这决不是闹着玩的,在梦里,唐太妃已经亲身体验过它们的愤怨和不甘。
圣母娘娘从此不敢再呆在体仁阁了,她在第二天就火急火燎地传下懿旨,说要搬到清凉殿去住。
少府令李大人这天在殿上陪伴圣母娘娘,宫婢们因被驱赶到外面,所以不大听得清娘娘和少府大人到底商量了些什么,只是圣母娘娘的声音时高时低,有耳尖的甚至还听到了圣母娘娘的几声啜泣。
宫里的事向来不能多问多说,只能拿眼睛看,看着看着,是妖是怪,是邪是祟,最终都会恍然现形。内侍宫婢因此格外留着心眼,而接下来事情就渐渐地明朗起来。
少府令李大人如今正忙着预备一场超度的法事,据说手下的属吏已经远赴贵溪的龙虎山去搬请救兵,而太妃之母吴国太夫人也被接到宫里,太夫人这次从宫外请得许多镇邪驱魔的符录,于是好端端的一座体仁阁,其上下里外便都贴满了这些花花绿绿的符纸。
吴国太夫人还开解圣母娘娘说:死都已经死了,娘娘还有什么好怕的!你也别老是自己吓自己,自己放自己不安生,既然能做得皇帝、娘娘,那都是靠天命!自有天上的神仙菩萨护佑,岂是那些死鬼能奈何得了的?
内侍宫婢们可都不是傻子,听言观形,一点就透,虽然有些话,这人前绝不能说,但在人后却往往聚在一起各自猜度。
圣母娘娘不单单是中了邪,恐怕、恐怕她还见到了鬼!
只是当真是什么鬼怪邪祟的倒还好办,一驱、二赶、三镇、四收,倒不信不能够降服,然而怕就怕这鬼乃是家鬼,且又不是一般的家鬼,乃是供奉在庙堂里受享配祭的祖宗显灵。对于祖宗显灵,你是能打得还是能骂得?祖宗生气发怒,所以显身现形,总是因为后人有过错,这就是召来高僧高道超度禳解,也未必能够安抚得了,先人们要是怒气难消,赖在宫里不肯去就庙食享祭,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俗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永寿宫闹鬼的消息被大长公主带到了长庆宫。大长公主也是忙里偷闲地往长庆宫跑了一趟,永寿宫出了这么大的一摊子事,可怜母后、上皇他们还都蒙在鼓里,大长公主又怎么憋得住不去说它,也就权当讲个不相干的笑话。
大长公主的口才甚是了得,在她活灵活现地描述体仁阁和永寿宫情形的时候,就好象她一直呆在太妃唐氏的身边,所有见闻逼真得如同亲眼目睹。
陈太后年事已高,所以有点受不了这个,她想到唐太妃跟周娘娘的亡灵面对面的场景,浑身就觉得不舒服,可越是受不了,越是不舒服,她就越是要听。听过了,还觉得意犹未竟:我就奇怪,周娘娘和张福妃生前都不是什么好相与的人,张福妃也罢了,死后被废,孤魂野鬼似地得不到血食,想闹也闹不出名堂,倒是周娘娘,生前那里肯低头服输过?这死后怎么也不出来闹腾闹腾?原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大长公主“格格格”地笑,直笑到喘不过气来。
“母后,永寿宫那边正准备大做法事要驱鬼逐邪呢?她也不想想,周娘娘本是她的婆母,更是神主牌位供奉在太庙里的祖宗先人,她倒是驱那门子的鬼呢?这要是触怒了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只怕从此更不肯放她安生!”
永寿宫闹鬼的传闻,对于长庆宫的贵人们而言,的确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上皇和汪后从陈太后的转述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也是内心称快。
陈太后说:冤有头,债有主,周娘娘当年可是走得不甘不愿,所以人虽已逝,却迟迟总不肯瞑目闭眼,唉,想起来真是可怜可叹!
上皇和汪后一时念起了故去的母后,从陈太后的长安宫出来,便特意前往萱慕堂上香献祭。祭拜之余,上皇顾汪皇后言道:上天有眼,祖宗有灵,自作当还自受!
汪皇后这会儿心中正想着晟儿,所以脸上的泪一挂一挂地,始终都没有断过。
“闹又能怎么样呢?总是人鬼殊途,至尊大位从未听说是让闹鬼给闹没的!”这话汪皇后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只是那么随兴地一想,便觉得世事当真是既无奈又无趣。
永寿宫超度禳解的法事足足做了有大半个月,京师里的寺庙宫观也都奉诏为国祈福,一度暂缓营建的帝后山陵寿宫这时也重新开始起造。
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唐太妃每天的觉却还是睡不踏实,她身边就算守上再多的人,点上再多的灯,唐太妃也只敢囫囵地打个盹,她老觉得周太后的鬼影子一直在她的身旁缭绕。
吴国太夫人眼见不是办法,只得说:她这么不肯走,必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娘娘不妨再仔细想想。
一经提醒,唐太妃马上就记起一事来,莫非因为当初获罪而遭官府追捕揖拿的周氏族人尚未得到赦免,所以周太后的亡灵才不肯安分守己地驾返莲池?
经唐太妃的一再关照,朝廷特为此而颁下赦令,凡是逃散流离在各地的周氏族人尽皆免罪,家产田宅遭籍没者,将由朝廷官府酌情拨还。赦令中还特别提到了慈圣皇太后之弟、曾任过太宰的周如喜,称他为国效力,素有勋劳,应予推恩,故起复为琼州太守,加岭南节度副使衔。
朝廷颁布的赦令一下,躲藏在宁安公主府上的韩夫人这回终于得见天日。可是她无处可去——家产早被查抄,府第也为人侵占,虽能在宁安府上暂住,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韩夫人那远在岭南被谪为琼州司马的相公,现在也蒙恩迁升做了太守,所以韩夫人便一心一意地想去岭南投靠相公。但是朝廷却命她安住京师,原先宣和坊的旧邸当然不可能就此发还,但朝廷也体念到韩夫人当下的困境,赏给了一处前后三进,面阔五间的宅院,另有京郊的腴田百顷作为其安身养命的禄田,曾经逃散的旧仆佣妇听说了此事,这时也都陆续地寻上门来,主仆相见,且悲且喜,相互皆道万幸!
韩夫人目下虽说失去了一品“昌国夫人”的衔称,但是借朝廷如今善待慈圣庄肃皇太后亲族的机遇,韩氏改获五品“恭人”的诰封,除了不能随外命妇入宫朝觐之外,四时五节仍能得到宫里下赐的一份钱物禄米的供养。
韩夫人改获“恭人”之封,安国夫人陈氏可是居中帮了大忙,周家虽说是遭受了大劫,可是这皇亲国戚的身份任谁也剥夺不了,安国夫人也只是瞅准了时机,跟圣母娘娘说了一声,便因此落了个现成的人情。
发生在宫里的这些诡异莫名的事情,好象是个不祥的预兆,在六月的月底,随着长安靖逆的进兵犯境,朝廷竭尽全力方能勉强维持的这个“天下安和、歌舞升平”的局面似乎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靖逆的贸然进犯对于江南而言,可说是既突然又不突然。因为在这之前,洛都留守方大用已经郑重地警告过朝廷。他说,靖逆蠢蠢欲动,似有出关犯我之意,朝廷不能不预先加以防范,以免事到临头而难以措手……
但是朝廷并没有认真对待方大用发出的警告。朝廷一来是不相信方大用的言行,二来朝廷也看出了方大用的居心。他之所以危言耸听,不外乎是想挟敌自重,好借此调回移驻于大梁的方蜀山旧部。
朝廷自然不能如其所愿,想想当初为了减其兵众,分其地盘,不知耗费了多少心神,如今但凭一句“靖逆蠢动,情势危急”就让他把人再要回去,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都当作了儿戏?所以吴王和张太保彼此一斟酌,就决定将计就计,让方大用里里外外皆讨不得好去。
朝廷行事用人的策略,一向都是褒贬裁抑、有打有拉,以区别对待。既然方大用老以“人手不足,防守吃力”这样的说辞来威胁朝廷,那么朝廷便考虑安排讨逆将军储定安率领禁军北营的二万键锐驰援洛上,明里这是协助方大用守护中原,暗里这叫做掺沙子,即以禁军来节制边军,以储定安来监督方大用,外防内控,确保万无一失。
至于驻防于大梁的方蜀山,虽说他是方大用的亲侄,但只要肯为朝廷所用,那也不妨多给他一点好处与甜头,以收这分化瓦解之效。
想那方蜀山原先不过是方大用麾下的一员牙将,名既不彰,官亦不显,若没有通天的捷径,单是论资排辈,循序渐进地在仕途走个来回,这大半生的时光便已消磨殆尽,想要出人投地,光宗耀祖,更不知会在猴年马月?张太保亦是从行伍里起家,对此早有深切体会,所以便建请吴王不拘一格提拨方蜀山,其人在感恩戴德之余,自然愿意俯首听命。
吴王依计从之,当下亲自去信,以示荣宠,而朝廷亦给方蜀山加了节度副使的赠衔。
节度副使虽然只是赠衔,但是有没有这个赠衔,品秩排场就大不一样,再说节度副使属于圣上钦命,上可专折言事,下可自辟僚属,若上司有差遣调动,亦需事先知会朝廷。而方蜀山得此赠衔,虽说还谈不上能和方大用、唐会之、许成龙等人平起平座,但也算从此跻身于封疆大吏的行列,可以节制一方。这自然都是圣上和吴王给予的殊恩,方蜀山心里当会惦量分寸。
朝廷的这番布局尽管称得上高妙,可惜世事并不由人作主,总会有失算与落空的时候。
朝廷没料到方大用这一次居然没有挟敌自重、谎报军情,而拟派往洛都掺沙子的征虏将军储定安,心里视率军洛上之行为无功有过的畏途,磨磨蹭蹭地不肯从京师动身。这样一天拖上一天,一直拖到地接巴蜀的巫州太守上表向朝廷告急求援。据太守在表中所奏,长安伪主自将精兵十万,另有楼船百艘,顺江而下,欲取我湖湘之地。
狼烟突起,战事将开,朝廷骤闻此讯,一时有点小小的错愕。自从承运六年靖逆兵败西迁,江南的守备便侧重于防范东胡。尽管这几年与东胡结盟修好,南来北往的彼此打得十分火热,但是朝廷上下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考量,总是不敢掉以轻心。却不道原本“非我族类”的东胡偏偏能够相安无事,反而同宗共祖的靖王余孽倒时时不肯消停罢手。
大学士陈广陵这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扬他那套“结好东胡,永为善邻”的主张。在他看来,胡人虽然嗜利贪财,但胃口总是有限,因此朝廷可以跟东胡讨价还价地做成一单子买卖,退一万步说,东胡充其量不过是个恶形恶状的乞丐,江南尽可用些残羹冷炙将之打发,这原也费不了几许银两;但是靖逆父子却是国朝叛逆,亡我之心一直未死,其为祸患自然远甚于东胡,且犯上作乱之徒,朝廷岂能容忍姑息,不讨不征?此即所谓“其不犯我,我亦犯他,其来犯我,我更何待?”,靖逆即敢兴兵犯境,朝廷应该毫不犹豫地发兵征讨,尽诛凶顽。
陈大学士坚定的态度深深感染了他的天子门生,少帝摩拳擦掌地一心想要御驾亲征。
少帝在小瀛洲曾经玩过这排兵布阵的游戏,虽只是假模假式的对垒互攻,但是两边旗飞鼓震,内侍小宦们进退冲杀,场面煞是壮观热闹,如今皇帝听说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人动兵动仗,自是心痒难耐,当下连连跟小楼子表示要“御驾亲征,讨逆平叛,一统山河”。
只可惜皇上身边的小楼子胆子比针眼还小,他心里始终牢记着圣母娘娘和陈大学士的叮咛嘱咐:人君肩承社稷,抚育兆民,所以万万不可轻涉险地!散骑常侍常在君侧,应时时予以规谏劝告……
职责所系,小楼子不敢轻忽,赶紧把皇上的想法密告圣母娘娘。唐太妃一听,顿时大急,立刻便把皇帝召到自己身边,亲自看管训育,一边怒责朝中文武不能为国效劳,替君分忧。
满朝公卿包括吴王和张太保在内,眼下都没把靖逆的兴兵犯境看作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虽然巫州很快就失了守,但这也在意料之中。现在朝廷已经下了《征讨令》,李得天和黄世英奉命率部狙击,这也是吴王和张太保商量出的又一个一石二鸟之计。朝廷对这伙匪寇出身的游兵散勇一直心存猜忌,所以这回驱使他们冲锋陷阵,即使损兵折将,也不为可惜。
至于骁骑将军方镇川,兵部八百里加急,将他从黔中伐蛮的前线召回,一但李得天、黄世英抵挡不住,方镇川所领的一部当趋前阻遏,朝廷并不求胜,而只寄望于他能够拖住敌人的兵锋,这样洛都的方大用就可以从侧翼包抄,两军合围,靖逆必不能全身而退;除此之外,方大用尚还可以引军攻袭潼关,以此来威逼关中,官军一但攻破潼关,则长安城便遥遥在望,靖逆两面受敌,顾此失彼,当不敢以孤军深入。敌退则我进,官军收复巫州轻而易举,溯流直上,则巴蜀亦可手到擒来……
吴王唐觉之和太保张成义就象下棋打谱一样,把满盘的棋子逐一打量,靖逆以一支弱旅来攻强师,却又走不出奇招异术,此战才刚刚开局,便已经输了一半。江南非但无忧,更且要喜上添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