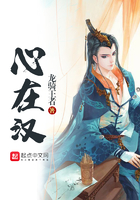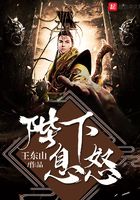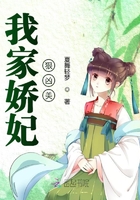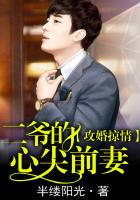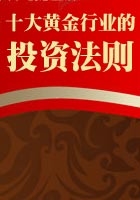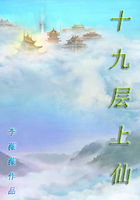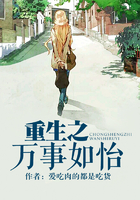光正二年的五月初十,方大用在自家的私邸里险遭不测。
当时云淡星灿,月挂树梢,方大用依照往常惯例,于饭后安步当车以消解积食,所走的也仍是老路,从书房明德斋出来,顺着观花廊道一路悠然往务本堂踱步闲走。
因为是在私邸且是内堂,方大用身边只跟着两个当差听用的小厮长随,然而就在长廊拐弯之处,有剌客突然自假山后面现身,手中亮晃晃的三尺之剑直奔方大用的面门而来,人剑合一,快如疾风闪电,当时的场面极是惊险骇人。但是侥天之幸,黑影方自假山后面蹿出之际,方大用便因吃惊过甚,口中“咦”地一声,脚下忽然一软,身子堪堪朝前一跌,那奔向面门的剑锋因此却剌了个空。
剌客蓄势待发的一剑走空,也是未能料到,当下稍一愣神,便反手一撩,连劈带削,直往方大用身上招呼。方大用惊急交迫,在地上连爬带滚,口中狂呼大叫,跟在身后的两个小厮见势不妙,都不顾性命赶上前卫护主人,一个人当先踢出一脚,然后双手死死攥住剑刃不放,另一个趁机上前把剌客团身抱住,方大用这时也一骨碌起身,抱头鼠窜,急如脱兔。
私邸里当值的侍卫闻声都陆续赶来,方大用被众人所护,心中的惊慌这才稍减,当下率众再到长廊,剌客已经脱身而走,长廊里惟见鲜血一滩和五六个掉落的手指,那两个长随一死一伤,已然僵毙在地。
惊魂甫定,方大用正要跺脚怒骂,谁知脚刚沾地便火辣辣直感痛不可当,却是方才惊走疾逃之际,不慎扭伤了脚踝,当时只顾保命,一时倒不觉得。如今这一脚跺下去,正是触到了痛处,顿时吖吖哑哑的呼起痛来,这不出声还罢,一出声,才又发现,自己的嗓子眼里象是塞了团棉花,嘶嘶地说不出一句整话。
有人潜入私邸谋剌官长,这实在是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不消方大用亲自下令,自有僚佐属吏遣兵派将地一路追查。
是夜,侦骑在洛都城中大搜大索,行商客旅、街坊士民尽皆骚动不安,虽然洛上九门紧闭,然而搜索至天明仍无半分线索。
如此折腾了三日,那剌客冥无影踪,城门却不能因此而久闭不开,没奈何只得照例开城,只在道隘关卡处增添人手,细加盘查来往商客。
这一场未遂的谋剌让方大用受惊不小,想起书上所说红线女、聂隐娘等前朝旧事,心头不禁泛起后怕,然而躺在床上养歇,头脑里又忍不住潜思细想,到底是何人想取自家的性命?东胡汗王和长安伪主应该都不会遣剌客,行暗算,而除此之外,似乎只剩下吴王和朝廷最为可疑?……看来,吴王和朝廷图谋自己已非一日,所以计出连环,皆为夺利取命而来。
好在自己福禄未尽,这剌客未能逞其所愿,方大用想到恨处,不禁咬牙切齿,夺人兵卒地盘不算,还想着赶尽杀绝,取人性命,这事岂可轻易罢休。
心中虽然有此大恨,方大用却明白眼下暂时发作不得,当下寄书朝廷,备述自己遭逢剌客之事,并推断此系长安伪逆所为,因天下欲取臣性命者,惟长安伪逆而已,然天命在陛下而不在逆伪,蒙天所赦,遇难呈祥,以此敢告陛下,莫为臣忧。
剌客自洛上铩羽而归,这让吴王和张成义颇为失望,揖捕司千挑万选的剌客,一出手竟是如此的不济事,幸好全身逃归金陵,若是再遭生擒,被方大用逼得口供,然后诘问朝廷,朝廷当何辞以对?再说朝廷遣派剌客暗算臣下,于法无据,于理难通,传扬出去,岂不天下大哗,众口啧啧?
眼下朝廷既然知悉方大用遭逢剌客,险遇不测,便不能不有所表示。而方大用奏称剌客为长安伪逆所遣,亦是吴王张成义所乐于见到,当即朝廷下诏予以安抚慰问,称其为国之元戎,岂容有失?若玉山倾倒,梁柱催折,此诚国家之大不幸也,所赖上天辩识忠奸,护佑元良,实乃可喜可贺,祈望郡王为国珍重,善加调摄护养,谨此问慰云云!
暗杀的事没能得手,朝廷却还要假做好人,在下诏抚慰之余,一并遣医赠药,且许其自置虎贲卫士二百人,随扈身边,以策安全。
事情办得如此不堪,张成义和吴王都是极为痛恨,因此吴王裁示,前时所遣之人无功而返,既辱使命,又有何颜苟活于世?马行原用人不察,至失先机,当以玩忽论,且罢其振威将军一职,仍居都尉之任。
而方大用吃此一吓,从此深居简出,每欲出行,必先清道驱人,身前身后更是布置了三重甲士,团团围护,以防万一。
在朝廷遣使遣医前来问慰之后,燕京和长安闻知方大用遇剌,也都派得人来,赠医送药,各自献上殷勤。
燕京和长安都判断出方大用的遇剌十有八九是江南的朝廷或者吴王所为。身为封疆大吏,占地千里,拥兵十万,顾盼自雄,叱咤生威,其一举一动,吴王乃至江南的朝廷岂能不侧目猜度?自是要百般设法,力纠其偏,然而无故罢废,终究难以服人,因而便想出此种暗算的下策。只是朝廷与节镇之间一但结下仇怨,便会越结越深,非到你死我活,不能罢休,因此趁其上下生隙,边镇离心之际,不妨施以援手,使之成为己方之助。
东胡方面据此努力说服方大用接受汗王的册封,然而任凭胡使磨破嘴皮,方大用到底狠不下心来接受胡人的封册。事情远没到当年石敬塘的那个份上,贸然背族弃国,落下一个难听的名声,估估算算,实在有些划不来。但方大用也不肯就此得罪了东胡,所以笑面迎人,百般敷衍。
长安方面跟东胡打交道比方大用要早,且东胡的大丞相宋有道既是靖王的姻亲又是旧臣,虽另投明主,到底不忘旧邦,因而长安方面在东胡燕京可称得上是人脉深厚,耳目遍布,所以方大用勾结东胡的事一早便为长安所知,并一直加以关注。
虽云关注,长安方面却是心有余而力不及。自从中原失陷,迁都关中,跟着先帝宾天,新主继立,诸事繁杂,其中又尤以提振人心,巩固家邦为第一要务,所以朝野君臣的眼光暂时都只能倾向于内,而不能旁及于外。
至于洛上留守方大用,长安君臣起初以叛臣视之,并不与之接触,而方大用也不敢私通敌伪,为皇上朝廷所猜忌。然而金陵忽就生出变乱,上皇逊位,大权旁落到外姓唐氏之手,长安方面审时度势,以为可作进取之图。然既欲进取江南,便绕不开坐镇中原,襟江控湖的方大用。方大用虽系叛臣,然叛而复降,降而复叛的事,古来多有,无非晓之以理、动之以利,不求其为吾效力,但求互通友好,两不侵害。
于是遣人至洛上与方氏商洽,长安虽地处偏远,亦有能言善辩之士,一来二去竟与方大用谈成了“保境安民,两不相扰”的约定。
约定既成,双方便常有来往,东胡欲册方大用为豫王,长安方面自是乐见其成,不过方大用若接受东胡册封,形如弃南投北,设藩立王,不啻自为一国,所损者江南也,既然江南有损,长安君臣便想趁机劝说方大用改动原先的约定,让长安也能分沾一些江南的余润。
长安的君臣对于收复中原故地固然已经不存奢望,但是从西蜀顺江而下据有湖湘之一部,从而在江南的腹心处打进一根楔子,却一直是念兹在兹的心怀期待,长安的始兴皇帝因此催促他的臣子们速速拟好定策,不要错过这等混水摸鱼的好事。
围绕方大用的遇剌,东胡和长安都加紧了各自的行动,反观江南的朝廷却是投鼠忌器,一时拿不出妥当周全的办法。
“此贼命不该绝,江南恐难有安宁之日!”陈太傅父子闲时只要提及此事,心中便油然生出许多忧虑,然而这到底是无可奈何之事,眼下除了静观其变,此外别无他法。
五月的月中,御史中丞家的三小姐戴嫣跟随她的母亲前往长庆宫觐见太皇太后和大长公主,戴嫣并不知道此次朝觐关系着她未来的命运,所以跟在母亲戴夫人身后的她,脚步轻盈欢快,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
戴夫人看她象个快活的雀子似的那么东瞅瞅西瞧瞧,表现有些不太稳重,便想吱个声提醒一下,但最终还是任由她去。出丑卖乖就出丑卖乖吧,她不就盼着大长公主眼高相不中,好黄了这门亲事。
戴嫣眼下还不知道大长公主府上要跟戴家结亲的事,戴夫人虽然有好几次想开口跟女儿说,可是话到嘴边又总是咽了回去。做母亲的没能给自己的孩子配上一门好亲,说起来这心里总有几分愧疚与不安。
象今儿一早进宫朝觐,戴夫人便吩咐女儿跟前的养娘,别把小姐装扮得太出挑,最好是荆钗布裙,素面朝天。但就是这么往丑里装扮,三小姐还是一枝花,往人群中一站,周围的那些侍婢丫头们顿时就给比了下去。
“唉,女大不中留!迟早都是人家的人!这可心不可心的,人说了不算,天说了才算!”戴夫人的心情因此越发滞重,这进宫后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太轻松,然而长庆宫远没有永寿宫那么宏伟阔大,紧走慢走也便到了太皇太后所居的长安宫。
燕国大长公主已经在殿上等着戴夫人母女,待受了她们母女的行礼叩见之后,大长公主这便把戴嫣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来。早就听说戴家的三小姐生得秀气,可惜养在深闺外人从未见得,眼下亲眼看过之后,倒也深以为然。虽然戴家的小姐身形姣弱,脸上稚气未脱,但是那骨肉停匀,明眸皓齿的样子,仍是让大长公主一见便生出许多欢喜。
果然不差!虽说看上去年纪略小,身量未足,但就如刚刚打蕾的花骨朵,别有一番韵致,何妨也只消得几许时日,这花骨朵便能长大绽放,从此浓浓艳艳,人见人爱,那时候谁人不夸自己的眼光准,相中这么一位招人怜、惹人爱的少夫人。
大长公主因此便叫她到自己的跟前来,拉起她的手,微笑道:“真真是个美人胚子,咱们家的傻小子福气可真不浅!这也真是他的命中造化!”说时便把自己头上戴着的一根垂珠镶宝的金凤钗亲自绾在了戴嫣的发间。
听大长公主话中的意思,显然是认可了戴嫣做自己家的儿媳,戴夫人见状,略微皱了皱眉头,心中虽然叫苦不迭,口里却道:大长公主的厚赐,小孩子家怎么当得起?三儿,还不快快拜谢大长公主。
戴嫣闻言,盈盈倒地下拜,大长公主一把将她扶起,含笑道:这孩子倒跟我拘起礼来!起来吧。宫里怕是从没有来过,来人,领戴家的小姐到各处走走,今后宫里少不得是要常来常往的。
看着戴嫣走出大殿,大长公主这又回头与戴夫人商量起两家的正事:我瞧这俩孩子模样般配,莫非是天生地造的一对?这事应该就这么定下来才是。咱家的孩子虽说眼下不济,将来可是要承袭玉田侯家爵位的,这样说来与贵府上也是门当户对,并不辱没你家的闺女,再说这闺女跟我挺合缘,等将来过了门,自然没人敢于委屈她!
戴夫人陪着笑脸,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幸而大长公主并不等她回话,径自起身去后寝搬请太皇太后的慈驾。
陈太后万事皆顺着女儿,大长公主既然中意,太皇太后自然也就中意,何况这丫头也着实不丑,跟公主府的小楼子堪称良缘佳配,当下太皇太后就在殿上宣了慈谕,亲自指定了两家的亲事。
事已至此,别无可想,戴夫人只得伏地叩谢,大长公主笑吟吟搀她起身,说:结了亲、换了心,今儿起咱们两家便成一家人了!
携女归家,戴夫人把太皇太后的慈谕和大长公主的意思俱跟戴中丞说了,戴有忠早料到会是如此,当下叹了口气,讷讷道:既然太后娘娘指配下亲事,我看也只有奉旨遵行了。
戴夫人在宫里时一味恭谨,并不敢多言半句,现在回到自己家里,这冲天怒气便朝着戴中丞迸发出来:气死我了!当初你要是肯听我一句,哪会有今天这种事?一家女还没等到百家求,就给人家强索强娶了!这还是官家的小姐呢?老爷也还是朝廷的司宪官呢?怎么事情一涉及皇亲国戚,御史谏议们就不敢仗义执言了?我真真是替你们羞死了!
戴中丞听得戴夫人数落,也不吭声,心里只想着如何能借个由头,去门去躲她两天,省得一天到晚地听这满耳的噪聒。
因为议婚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慈谕,因此三书六礼的需要格外准备周全。大长公主的手里头因有这桩大事要做,整日里便都忙得不可开交。
这六礼的首礼便是纳采,大长公主原是想请身份尊贵的当朝大老前去女家提亲说合,但是公主府的长史说,昔时元献太子册妃纳娣,曾以太师与太傅前往亲迎,公主如也议请太师太傅前往,于制怕有违碍,未必妥当。
大长公主想想也是,便请来了太保张成义和京兆尹崇恩作为男家的媒妁之人,前往女家,表达欲与女家互结秦晋之好的美意。
戴家自然允诺了这门亲事,媒妁替两家通过声气,便再往女家行采择之礼。这采择之礼,京师俗谓之采礼,本来可简可繁,但由两家商定采行,然而大长公主偏偏就繁不就简,将那些金玉珠饰,珍奇玩好之物,一一纳入采礼之列,并不问其价值几何。
采礼送过去后,接下来便是问名。因前时送来的采礼过于隆重,戴家这下也不敢过于怠慢,当下以上等红绫画笺写下了戴嫣的姓氏年庚,封在檀香锦盒之内,送来公主的府中。
大长公主请来善卜之士,先把未来少夫人的庚贴仔细看过,卜士云其八字纯良、清而不杂,正官夫星显著、而子息运禄两旺,是个旺夫相子,后福绵绵,既贵且富的诰封之命。
大长公主闻言,喜上眉梢,当下又请卜士将两人的生辰八字对照验看,卜士开口当然全是好话,既然小楼子属猴,少夫人属狗,这俗话说得好:猴配狗,终身守!良缘吉兆,自然莫过于此!
合过两人的生辰八字,且卜得是良缘吉兆,大长公主于是忙忙地行起纳吉之礼,这回自然还是先使人送礼,仍旧央请太保和京兆尹两位大人出面往告于戴家。
戴家此前也请人占卜过吉凶,却不象大长公主所声言的那么美满如意。虽然有“猴配狗,终身守”之说,但是术士却一口点出两人的八字不合,时日相互刑冲克害,所以即使属相相配,终究也是枉然……戴夫人听得这话,心头自是时常犯怵。
但是这门亲既是太皇太后亲自指定,且又收下了大长公主送来的采礼,婚姻之事再无推拒不从之理,不过虽然订下了戴嫣和于凤楼的婚事,但因女儿未及成年,戴夫人心存怜惜,所以便想着把婚事尽量往后拖延。
纳吉是六礼中的第三礼,之后还有纳征之礼,纳征即是下聘定,聘礼一至,婚姻落定,这接下来该是请期与亲迎了。所谓请期就是选日子,男家一旦选中了良辰吉日,便会来女家告知成亲迎娶的好日子,女家自无不允之理,然后就是新郎大官人披红带花亲自登门喜迎新人,然后女去而婚成。
戴夫人因此一再坚持,这纳征之礼无论如何也要留待于明年春上再行。
这话托两位大人给带了过去,大长公主开始并不肯依,按她原先的想法,戴家的三小姐最好年内就迎娶进门,至于年纪小又算得什么,可以不先圆房,待到十五六岁上再让这对佳儿佳妇行夫妻之实也未必不可。
好在大长公主人逢喜事精神爽,万事肯于听人劝,且戴夫人又百般求告,大长公主终于同意将纳征之礼缓到明年春上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