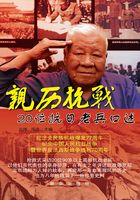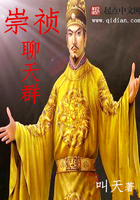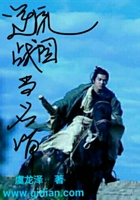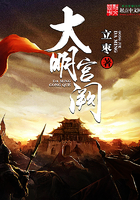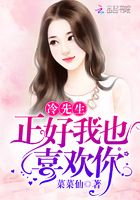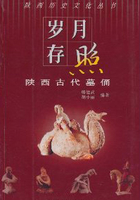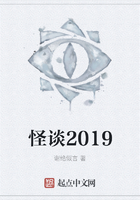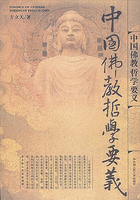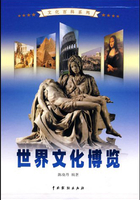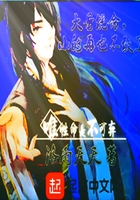所谓天意不遂人心,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张太保虽然算到了长安克破,群臣将齐趋长庆宫向上皇朝贺祝捷的事,但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圣母娘娘把群臣入宫朝贺上皇的时间往后给挪动了一下。
圣母娘娘有她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吴王不在京中的这段时间,唐太妃总觉得身边缺少倚仗,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偏偏城中又时不时冒出什么谶诗、流言之类,搅得人人惊疑、个个慌张,疑心之下易生暗鬼,这不枉死了礼部侍郎张敬白不说,还逼死了陈太傅、陈学士两父子才算消停。
朝廷日理万机,事烦且乱,即使有吴国太夫人坐镇宫中,帮着出谋划策、鼎力扶持,圣母娘娘仍有些应付不过来,幸好朝中陆太师勤于职守,尚能一用,但陆太师到底上了年纪,精力干劲都比不得往昔。
象这日宫里朝会,召对亲贵大臣,说起长安克破、关中收复的事,民间已经风闻大捷,欢欣鼓舞,喜气洋洋,自不在话下。但朝廷尚未正式布告天下,这样的盛典,百年难逢,总要祭天告祖,朝觐表贺,今日朝会便是专议此事。
太保、武安侯张成义首先提议道:此等大事,功德巍巍,昭如日月,朝廷不但要诏示天下,且宜遣群臣朝贺上皇并大赦天下,更要祭告于宗庙陵寝,使上下同庆,内外安和,四海咸知,臣等躬逢盛世,沐浴皇恩,亦不胜欢欣之至……
忠义郡王宪原和御史中丞戴永忠都附和说:太保此言极是。国朝有这等扬眉吐气的喜庆盛事,应告于宗庙、朝于上皇、大赦天下,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圣上、娘娘化育万民,德被苍生,如今宇内澄清、黔首大安,朝廷理当与万民百姓同欢共庆……
圣母娘娘和皇帝听了这些恭维话,面上都露出喜色来。
讨逆将军马行原、京兆尹崇恩以及少府令李润等人接着也都呈奏:伪朝倾覆,关中平定,战功煌煌,可喜可贺。上皇倚门望阙,久候佳音,娘娘和圣上应遣群臣前往朝贺,以惬圣意,以慰上怀。
听到亲贵重臣屡屡提到朝贺上皇,圣母娘娘慢慢收起笑容,低着头沉吟未语,年少的皇帝没有察觉,依然兴高采烈。
皇帝年逾十四,御宇也有了三载,虽成天努力象大人一样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到底还有几分孩童心性,当下兴致勃勃地说道:朕听散骑常侍小楼子说,街市上这几日张灯结彩,热闹得很,人人言笑宴宴,个个争说大捷,都敬祝国运昌隆,盛世太平。这样的喜事盛事,理当呈奏长庆宫,二圣闻知捷报,定然同感欢欣鼓舞。
振威将军、执金吾储定安当即奏称:娘娘贤德,故而皇上圣明。皇上孝心至诚,足以感动天地,此皆娘娘教导有方。臣以为,父子亲睦,两宫同心,上下内外,自然皆大欢喜。若准奏成行,一切均照吴王昔日旧例。臣督率有司,沿途警戒,翊卫宫廷,屏蔽内外,确保万无一失,皇上、娘娘当可放心。
圣母娘娘仍未言语,这会却微微皱起了眉头,抬眼想要征询太师陆正己的意见,却发现太师居然歪头打起了瞌睡,连殿上这么多人的言谈议论都没能惊动他老人家。
圣母娘娘转念一想:眼下事多言杂,且是人乏马困,若再议行什么告宗庙、朝上皇、赦天下的种种礼仪,前朝后廷、诸司衙门又要忙乎得人仰马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趁着吴王没有回朝,大家还是养精蓄锐,暂先歇口气儿再说。
当下也不需动问陆太师,圣母娘娘就此颁下懿旨:“班师回朝,献俘太庙,朝贺上皇、大赦天下,这都是朝廷的头等大事,自要妥善安排,不可马虎潦草,此事礼部、户部以及兵部、太常诸司不妨预先筹措准备着,一切等吴王凯旋回京时再议而行之。长庆宫二圣那里,可先遣少府令李润具礼禀奏,告以大捷,表呈四海欢腾,万民共庆之状,以此惬圣意而慰上怀。”
圣母娘娘一锤定音,把张太保还要再讲再劝的话都憋回到肚子里。
尽管永寿宫对太保张成义不大待见,罢了他所领的各项职事,免了他的朔望朝参,但是不入虎穴,蔫得虎子,张太保仍是当仁不让地出现在今日的朝会上。
作为居家待罪、听候议处的闲废之人,本来今天这样的朝会他可来可不来,来了也应该少说多听,以免沾染是非。然而为了说服永寿宫同意群臣朝贺上皇,这事关复辟反正成败与否的大计,张太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虽被削夺问政理事的职权,但头上太保的乌纱帽仍在,朝廷三公之位未除,所以仍能以奉朝请的名义参与这亲贵大臣商讨国是的朝会。
太师陆正己有好一向没有见到张成义,今天一早在朝房里候见时,冷不防看到久未谋面的张太保出现在自己面前,心上不免有些惊讶。不过太师的神情一向掩饰得极好,当下笑咪咪地迎了上去。
而张太保见到陆太师,则好象孺子见到了父母,连忙躬身下拜,寒喧之后,言词也变得凄清恳切:长安克破,关中收复,四海欢腾,万民鼎沸,国家有此盛事,理当大庆祝捷!在下虽待罪之身,闲废之人,亦不敢不来入贺。
陆太师见张太保执礼甚恭,只得安慰他说:太保大人精明能干,素为吴王所倚重,虽有些小过,终难获大咎。伪朝倾覆、长安克破,朝廷必有大赦之诏,太保大人只须忍耐上几日,自当会有弹冠之喜。到时老夫当去太保府上叨扰美酒。
张成义赶紧拱手称谢:太师国之大佬,言重如山,宫中府中太师若能仗义执言,施以援手,则老大人济人之恩,扶持之德,在下感激不尽。弹冠之庆,不复敢望,但能免祸消灾,已足称心。若以老大人所言,国朝盛典,当以大赦天下为最,在下多谢老大人指给一条明路。陛见之时,当奏请圣上、娘娘,修睦两宫,朝于上皇,大赦天下,使浩大皇恩能够泽及众人。
陆太师虽不以为意,却开颜笑道:“正是,正是。只要朝廷有推恩及人的旨意,太保大人也就有份沾恩被泽了。”
细节决定成败。太保张成义的谋划原都是围绕群臣朝贺上皇这一细节而展开。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获得永寿宫皇上、娘娘的首肯,早点安排下群臣前往长庆宫朝贺上皇的诸般事宜。
按照他与长庆宫二圣此前的约定,群臣朝觐上皇之际,就是讨逆诛贼,复辟反正之时。趁着群臣齐聚于长庆宫的机会,威逼鼓动群臣,一起拥戴上皇反正复辟,重归大位,再掌大权,诏令天下义士,保驾勤王、讨伐叛逆。
谋划既然天衣无缝,眼下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可恨唐太妃似乎洞察先机,竟然把朝贺上皇的时间给挪到了吴王回京以后。
就好比当头一棒,打得人失魂落魄,无力抵挡。这可万万使不得!吴王一旦回京,操持国柄,手握重兵,生杀予夺,威势凌人,那时再想竖旗举事,恰如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胜算可言。饶是张太保号称“足智多谋”,这下也没了主意,一时心焦气促,五内如焚,谋划生变,希望落空,这、这到底如何是好?
永寿宫的殿阁庙堂,吴国太夫人一向视同于自家府上的楼台厅室,随心所欲地出入于其间,不为别的,为的是替圣母娘娘和外孙皇帝看门守户、把关压阵。然而今天吴国太夫人竟意外地没有在朝堂上现身,只因她的儿媳、凤阳郡夫人林氏一大早就进了宫,此刻就陪侍在她的身旁。
林氏并不象太夫人那样常驻宫廷,她掌理着吴王府邸里的一大摊事。以前吴国太夫人当家作主的时候,林氏服服帖帖,乖巧安顺,不敢生半点抢班夺权之心。现在既然太夫人的日常起居都搬到宫里,那么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吴王府里自然就轮到林氏指手划脚、作威作福。
闲来无事,林氏视进宫为畏途,宫里礼数大、规矩多,哪有自己家舒坦自在。今儿要不是受了弟弟林重阳的请托,宫里当是能少去则少去。这其实都怪林重阳自己,受命侦办谶诗案却连累到陈太傅父子身死,不但官位谪迁,永寿宫的圣母娘娘和小皇上直到现在都心有余怒,不肯原谅,即使重新起复任用,也不许他在御前走动。
林重阳没有法子入宫,自有法子进府,他把张太保深夜闭门与储定安、马行原密会的事告诉了姐姐林氏。
但尽管他言之凿凿,绘声绘色,说得好似亲眼目睹的一样,林氏一开始也不大肯信,直恼得林重阳恨声连连:陆太师信不过,阿姊自家人,如何也信不过?
林氏说:不是我信不过你,旁人都不信的事,我信了也没用。你也说了,连陆太师都不准备往下深究,这回跑去说给老太太听又有何用?
林重阳分辨说:陆太师这几日忙昏了头,别的事一时也顾不上。只能说给太夫人听,老太太心思缜密,定能理清这当中的头绪。阿姊,你想想,三更半夜的闭门密会,能有什么好事,肯定有奸谋,趁着姐夫吴王不在京中,正是大搞阴谋诡计的好时机。
林氏想了想,道:太保这个人也不是全没有用处。有些事你不知道,为吴王议上九锡,就是太保出面首倡,为此出了很大的力。唉,好好的一桩事,居然就给搅黄了。
提到这件事,林氏犹觉遗憾不已,吴王若加了九锡,作为吴王夫人,她不也跟着水涨船高。
林重阳怔了一怔,才说:张成义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今儿讨好你,明儿奉承他,明明算计了你,还把他当好人看。他既然首倡加礼九锡,怎么看到风头不对,立马就缩回去了!可见面上做的全都是幌子,底下只想着谋他自己的私利。
林氏叹了口气,道:你既这么说,好吧,明儿一早我进宫去,替你把话带到。老太太怎么想怎么着,由着她去琢磨合计。她对张太保,也就跟你一样,早有些看不顺眼,宫里的娘娘对他也不甚喜欢,前些日子把太保家夫人进出宫殿的腰牌都给收缴了。太保呆在家里,不好好反思悔过,还敢跟人密谈,合该他自己找死,如何怨得了旁人!
朝会散后,陆太师去见吴国太夫人。太师虽说现在统辖百司,总领政务,是朝廷第一要紧之人,但朝政大事及官员升谪还需跟太夫人碰面会商后才能颁布施行。
太夫人此时还在跟媳妇林氏谈论张太保的事,见陆太师来了也没有打住,只是顺口问了陆太师几句。
陆太师说:太保张成义这个人,城府深、心机重,不可预测,难以琢磨。如能为我所用,而用尽其材,那自然最好;怕就怕心怀异志,别有他图。他本无名小卒,以军功起家,与军中渊源颇深,显贵之后,又频繁接近朝中亲贵。想想当初议加九锡的是他,刚刚促请朝贺上皇的还是他,其内心到底是何打算,别人当真是猜想不来。
太夫人点着头,说:你和我看法一样,这样的人实在让人不大放心。要不是念在当年推戴吾儿,积有微劳的份上,也容不得他到现在。本来让他待罪居家,就是有意放他一马,他若知趣,就该谨小慎微,可如今看来,他还是不肯安分守己。侍御史林重阳举告他深夜与他人密谋,这事你既然知道,也不来知会宫里一声。哼,深夜密会,必有奸谋,若真有其事,太保这条命他自己是不想要了!
陆太师听太夫人的口气里隐含有责备自己的意思,当下忙辩白道:侍御史林重阳的确说过张太保与人深夜密会的事。不过他所指称的,并无人证、旁证,这口说无凭,叫人如何确信?早先林御史办谶诗案,一路穷追猛打,结果办出了大漏子,弄得人心惶惶,至今未安。蒙恩起复之后,将功补过之心甚切,可是没有真凭实据,总不好指鹿为马、陷人以罪。所以我让他明查暗访,一但坐实其事,便可收捕下狱。那时就算往死里治罪,也没人觉得是冤枉的。
吴国太夫人放缓了语气说:老四,我倒不是怪你,只是这么重要的线索,原本可以顺藤摸瓜,就这么给放掉了实在可惜。
陆太师沉声道:只要有心想治他于罪,总是会找到办法。太保现在也越来越按捺不住了。或许把柄不用我们去寻,他自己就会送上门来。
吴国太夫人淡淡说道:要依了我,寻个不是把他做了,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吾儿觉之对他尚有三分信任,所以心慈手软,迟迟下不了决心。想想吕后是怎么除掉韩信的?说到底韩信有什么错?韩信错就错在太有本事,让人不安!
林氏在一旁听得一惊,听老太太的意思,不管有错没错,太保张大人大概算是活到头了!偏偏太师陆大人非但不帮衬着说点好话,反而一个劲地往火上浇油。林氏心中虽然替张太保暗道惋惜,却紧抿嘴唇,什么话都不敢说。
谈完张太保的事,吴国太夫人转了话题,问起朝会上的情形。
陆太师回复说:捷报频传,军民上下都是喜不胜喜,亲贵大臣们各有说法。圣母娘娘却另有高见,叫朝廷先行筹措一应礼仪,一切等吴王回京后再说。
吴国太夫人笑道:圣母娘娘总算有了些见识。朝廷凡事预先筹备,临事才能不忙不乱,否则等吴王班师回朝再筹措,未免手忙脚乱……朝中的事你替我多看着点,诸司百衙那一帮官僚,干事的少,混世的多,白拿着银钱俸禄,反正朝廷也不是他家的!
知道张成义今天要去参加朝会,姚琉璃一早起来就忙着侍候大人穿上朝服,然后守候着等大人归来。外头一声传报“大人回府了”,姚琉璃便亲身来至后堂,一边替张成义换下公服,一边低声询问:大人的脸色这么难看,莫非事不顺意?另有变故?
张成义怕她担心,吱吱唔唔地不肯讲明。可太保大人越是这样,姚琉璃越是忧心忡忡,于是沉下脸,正色道:大人不肯说出实情,难道能当作什么事都没有了么?是福是祸,总要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才好担当。
张成义无奈,便把今日朝会中的情形大略说了一通,说完长叹一声:事情既然有变,恐怕要另想对策。原以为太夫人那只老狐狸今天不在朝堂,还庆幸正是个好时机,不曾想圣母唐娘娘难得睿智起来,不但把群臣朝贺上皇的事一口给否了,而且要待吴王回朝再作议行。
姚琉璃呆了一呆,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可当真料想不到。她手按着椅背,努力撑住身子,而张成义垂头丧气,一头歪靠在太师椅上,也是半晌无言语。
待定了定神,姚琉璃勉强打起精神,道:此路行不通,难道别的出路也没有?大人总要另想个法子才行。
张成义低头想了一阵,狠狠地说:这事既然做了,再没有退步可言,说不得拼他个鱼死网破!夫人,你且出去,容我仔细考虑考虑。
姚琉璃站着未动,只是说:要么我再往宁安公主府走一趟,告诉她事情有变,提醒二圣那儿也好有些准备。
张成义摇了摇头,说:公主府你不用去了。人心只能聚、不能散,人心一散,劲儿一泄,胆战心虚,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除了朝贺上皇的事没有任何进展,今天其实还有另一桩事让张太保感到莫名地愀心。候见皇上之前,借着如厕的功夫,张成义跟马行原匆匆见了一面,却听他说:那林重阳昨儿跑去吴王府跟其姐林氏密谈,而今天一早林氏便也来到宫里去见了老太太。事情恐怕不太妙,太保须要早作筹谋。
几桩事勾连在一起,张太保已然觉察出逼近的危机,只是他尚没有想出应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