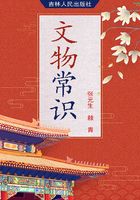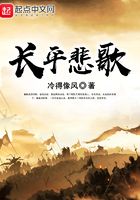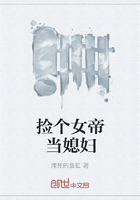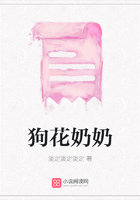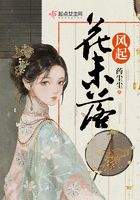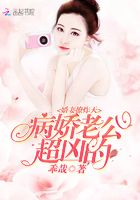自打见过寿春郡夫人姚琉璃,上皇便有些神不守舍,以至于整夜都不能安枕入眠。上皇的症状有些象被吉士所诱的怀春少女——从他把那方“同庆堂主人”的小印交付于姚琉璃的那一刻起,上皇仿佛把自己的心一并交托了出去,并且寄望于收下他信物的人千万不要辜负了他的殷切期盼。
长庆宫里三年幽居禁闭的生涯,打熬着筋骨,也打磨了心性,迫使上皇象蛰居的虫子一样潜藏暗伏,但是姚琉璃的出现,象是冷不丁划过苍天的一道闪电,上皇现在隐隐听到外面的惊雷,大地震动,万物复苏,上皇确信他终于等来了春风送暖、柳暗花明的时节,上皇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破茧而出,展翅高飞。
太上皇后汪氏最先注意到了上皇的那些细微的变化,她知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在上皇取出那方小印准备赐人的时候,汪皇后其实明白了上皇所欲表达的决心。皇后因此而开心释怀,这是上皇主动采取的行为,上皇终于开始承担上苍所赋予他的使命。
赐印这个举动,除了上皇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出来,在皇后的印象里,上皇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天纵英明过,以至于汪皇后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小视上皇了。也许跟自己一样,上皇并没有浑浑噩噩地虚度着日子,他也一直在等待时机,藏伏不露,然后一触即发。
汪皇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指,浅浅的破口已平复得快瞧不见,皇后这便想起姚琉璃和她的约定。“群臣朝贺上皇之际,便是复辟反正之时。重振旗鼓,讨贼诛逆,在此一举!”
三年来,这样的场面,曾无数次地出现在梦里面,也无数次地让汪皇后心动神摇,然而梦醒环顾,周遭依旧凄凉冷清,然后热泪盈眶,无语凝噎。
在这希望与失望的交替起伏中,汪皇后时而伤心、愤怒,时面难过、沮丧,但由始至终都不曾崩溃绝望。日子越是艰辛难捱,就越是不甘心撒手放弃,她始终在苦等苦盼。
天无绝人之路,这下应该是等来了、盼到了——姚琉璃的进宫,给所有的人勾勒出一个绝大的指望,光明灿烂,触手可及。所以接下来的这些日子,每一天都象是度日如年,每一天又都充满了期盼与渴望。与以往午夜梦回后的黯然神伤不同,这一次的期待和渴望,既不会是空中楼阁,更加不是异想天开,它是实实在在的——有誓书为凭,有印玺为证,有咬破手指按下的血印,有长庆宫里敲定的诸多细节,正因为有了这一切,它才格外地激动人心。
生死悬于一线,富贵或将成空,太保张成义对此蔫能不急。朝堂上,无计可施的张成义,心胆俱裂,五内如焚;归府后,面对姚琉璃探究的眼神,张成义只能闪烁其词,禁不住姚琉璃苦苦追问,最终仍只得以实情相告。
姚琉璃的失望溢于言表,张成义无言可以开解,他自己的焦虑不在别人之下,可是眼下又什么都做不得,当下只能挥手让姚琉璃出去,容他自己一个人呆在后堂里冥思苦想。群臣朝贺上皇的事既然行不通,那就只有改弦更张、另辟蹊径,或许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姚琉璃不敢打扰,悄悄退出后,竟不知道该往何处、该做何事才好。心里的恐慌越来越抑制不住,坐立不安的她几次都忍不住走到后堂门口附耳探听,躲在里面的太保大人就象闭关入定的老僧一样,半丝动静也听不到,姚琉璃虽然心惊肉跳、六神无主,却也只能干等着。
其实当太保大人一回来,姚琉璃就从他的脸上看出了情形不妙。大人不但脸上的慌乱掩盖不住,连话也吱吱唔唔地说不周全。
听说大人的计谋没能派上用场,姚琉璃知道这下可是坏了大事!作为亲赴长庆宫,亲眼见到过二圣,聆听过御音敕旨,取回过信物印玺,且在誓书上画押按印的局中人,她比谁都清楚太保的计谋。而在这一连串的谋划里,推动群臣赴长庆宫朝贺上皇是即将开场的重头大戏,是太保大人整个反正复辟大计里最不能缺失的一环,这也是姚琉璃和二圣在长庆宫见面时反复盘算推演过的结论。
这一环如果缺失了,整条链子就都断了,就好象预先编排好的一出戏,正要照本宣科地一折一折、一幕一幕地朝下演,然而还没等到鸣锣开场,戏本子忽然就给更换了,原来的那出戏还怎么接着往下唱?
眼看一切都将化为梦幻泡影,被内心的焦虑煎熬折磨着的姚琉璃却不敢去催促张成义。这会子催促根本于大事无补,她只能祈望大人快快想出可以替代的法子,而不管是什么法子,总要努力去试一试,无论结局如何,也愿赌服输,至少总好过束手就擒,低头就戳。
她在外面拈香默祷,这已是她点上的第三炉香了,看着眼前袅袅升腾的烟气,姚琉璃别无他法,只能收敛心神,一字一字地轻声念诵佛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佛号刚念完一声,一双手忽然按上她的肩头,姚琉璃心头一颤,身子一抖,“哎唷”一声惊呼起来,急回头时,看见太保张成义严肃冷峻的脸,竟不知何时他已从后堂出来了。
“你可吓死我了!”姚琉璃虽然抚着胸口,低声嗔怪,眼睛里却有喜色一掠而过,无论如何,大人总算是出来了。他恐怕是想出点名堂来了!
张成义的手依然搭在她的肩上,口气却显得有些紧迫:事情紧急,出乎意料,叫人来不及深思细想,当务之急只有把上皇赶紧从长庆宫弄出去。
弄出去?姚琉璃一时无法理清张太保话里的头绪,忙问道:弄什么?怎么弄?
吴国太夫人拿吕后杀韩信的事来打比方,执政的陆太师当然心领神会。既然要诛除奸佞,那就要赶在朝廷大赦之前,所以趁热打铁,事不宜迟,太师陆正己当即草拟了一道收捕太保张成义的诏令。
罪名也是顺手拈来,大笔一挥就定下“心怀怨望,谤讪吴王,离间君臣,图谋不轨”这几个字。这罪名跟那个“莫须有”异曲同工,按在谁身上都很合适,反正凡事有吴国太夫人作靠山后盾,吴王对太保即使有哀怜回护之意也怪罪不到自己头上。
太保是朝廷三公,且有勋功爵封,身份地位不比旁人。论理按律的话,欲治三公于罪,须朝廷集议,九卿会审,查明罪状,方可明正典刑。但自上皇逊位,吴王秉政以来,纲纪废驰,权大于法,朝廷大臣只要收捕下狱,自是触犯天条,难逃一死,至于以什么罪名处死,反而倒在其次。
俗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溯本追源,这又何尝不是张成义自作的孽!若非承运兵变,朝堂之上哪里轮到张成义之流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现在既然有机会将他整倒搞垮,陆太师就决不会手下留情,除恶务尽,总不能遗下后患,看他东山再起。
陆太师亲自拟好诏令,要使之奏效,接下来还需请得皇帝的恩准,盖上玺印,发至有司,而后就能奉旨拿人。皇帝尚没有亲政,所以只要圣母娘娘同意在诏令上用宝,事情便成了。这自然更加好办,陆太师只需将拟好的诏令送到吴国太夫人处,那么一切均是太夫人和圣母娘娘作的主,太师自己反倒置身于事外了。
做这种取人性命、要人脑袋的勾当,陆太师本不肯假手他人,一定会亲力亲为,偏偏这时有小宦找来,急急地说,政事堂刚到了前线来的公文,急等着太师老大人前去拆阅处理。
陆太师无奈只得将拟好的诏令用拜匣封上,即命这个小宦代他呈送给吴国太夫人,并请圣母娘娘钤印用宝。小宦捧着拜匣诺诺而去,陆太师暗想:前线来的公文,除了要粮?要饷?要人?还能有什么事。朝廷都快穷得见底了!明年的税赋只怕又要加征!
再想想张太保就是因为银饷粮草的事给搞下了台,若再往前推,周如喜、周如乐两任太宰也莫不因此而遘祸遇难。陆太师叹了口气,加征就加征吧,小民那里挤一挤,富户那里摊一摊,花捐杂税什么的再多征一点,先顶得一时是一时!
前线来的公文,其内容陆太师只猜对了一半,除了要朝廷筹备粮饷、增添兵马这些老生常谈的例行公事,出乎意外的,呈文者竟是齐鲁节度使唐会之。
齐鲁与东胡各自相安,一向风平浪静,莫非这下也出了事,陆太师赶紧拿起呈文细看。公文中说,几天前,也就是公文签发之时,唐会之的手下和东胡在德州干了一仗,双方互有死伤,为怕东胡挥师南下,唐会之请求朝廷增调粮饷人马,以备万一。
陆太师看罢,拍案直呼:这什么东西!真是荒唐透顶!
听到太师大呼小叫,太师手下的僚佐属吏都聚拢过来。陆太师指着公文,不悦道:公文没有加急,说明情况并不严重。他只说干了一仗,这仗怎么干的?杀敌多少?自损多少?是谁领兵出征?对手又是谁?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统统语蔫不详。这简直是在糊弄朝廷!唐会之这会子写这劳什子做什么?他还嫌朝廷的事不够多、不够乱么?驳回去,叫他自筹自备!
有属吏小心翼翼地说:大人,就这么驳回去恐颜面不太好看。卑职以为,还是暂不回应较为适宜,请大人示下。
陆太师摆摆手,唐会之呈上公文总会有他的用意,否则也不会没事找事。陆太师静下心来一想,果然就想到了唐会之的用意。他这是眼红妒忌方大用立下的功劳,所以也想在边境上搞点动静出来,这样才好引起朝廷的重视,趁机要些粮饷兵马,即使没能从朝廷讨得便宜,至少也让朝廷知道他那里面临大敌,自然不好再从他那里要人要粮了。唐会之仗着平素与自己私交不错,也不怕拆穿后讨个没趣。
陆太师把摆动的手往下一放,吩咐道:长安刚刚收复,关中平定尚需时日,敌若不来犯我,我不必先启战端,总以相安无事为好。粮饷兵马的事,暂无增添之必要,惟各地解缴朝廷的税赋,不得拖宕延迟,须按实缴足,解送京师,眼下就连一粒米、一文钱,朝廷都已指派了用场,决不可挪作他用。就照这样的意思回复他,让他自己看着办。
正说话时,先前派去代送拜匣的小宦前来复命,只说:回太师老大人,少府令李大人适才遇见小人,问清情由后,将拜匣一并携了去见圣上、娘娘和太夫人。故此小人特来回话。
少府令李润在圣母娘娘和太夫人那里都能说得上话,陆太师倒也不以为意。
陆太师拟好的诏令,少府令李润为之转呈,送到了圣母娘娘和吴国太夫人面前。圣母娘娘初闻还有些诧异:今儿一早,太保张成义还奉朝请入宫议政,怎么一转眼就要收捕下狱?李大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李润尚未回话,吴国太夫人已抢在他回话之前,轻描淡写地说:诏书上不是都写得明明白白——“心怀怨望,谤讪吴王,离间君臣,图谋不轨”,凭这几条,死几回都够了,如今只是将他下狱而已,是与不是,待三推六问之后,岂不真相大白。我看这事娘娘该准了。
圣母娘娘说:陆太师何在?收捕拿人,总要有所凭据,得先请他来问个明白才是。
吴国太夫人道:原不关太师的事,是我让陆太师拟诏进呈,这事娘娘不妨先准了。若有疑问,回头娘娘可以宣召侍御史林重阳来问清原由。收捕拿人,总是为了社稷江山,朝廷稳固!即使错了,谁也说不得不是!娘娘有什么可迟疑的!
圣母娘娘道:话虽如此,总该省慎一些。陈学士的事犹在眼前……
吴国太夫人不耐道:陈学士是陈学士,张太保是张太保!当初贻误军机,本就该治罪!
圣母娘娘只得说:既然如此,那就先下到狱里,慢慢置问。
吴国太夫人这便对李润说:李大人,娘娘既有懿旨,那就请宝用玺吧,发下去照旨遵行。
李润领旨,自去掌玺司请宝钤盖,且依惯例将诏令批转政事堂,政事堂的中书舍人接到诏令,先另录一份存入内档,然后再按诏令的内容,将原件下发至相关衙署。因为是奉旨收捕拿人的诏令,当值的中书舍人于是将诏令例行发往揖捕司遵照执行。
自散了朝会,掌理揖捕司的征威将军马行原便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事前左盘算、右琢磨,自以为的万全之计,不承想被圣母娘娘一口就给否决了,还说凡事皆须等吴王班师回朝后再议而行之。
圣母娘娘的懿旨有如晴天霹雳般地当头打下,自己和张太保、储定安会商密谋的计划就此都落了空,当时心中的震恐自不消说。马行原初还指望张太保能够据理力争,说服圣母娘娘改变主意,可张成义象个锯了嘴的葫芦,不但不说话,连屁都没有蹦出一个来。
朝议散后,马行原本想跟张成义找个地方说话,会商出一个善后的法子,既然事情不济,总得另想他法才成。偏偏张成义跑得比兔子还快,才一眨眼,他已经跨上马背,一声吆喝,径自扬长而去,连随从的家丁手下都追之不上。
张成义只怕是乱了方寸,马行原一想到此,心里就充满忧惧。这下如何是好呢?坐等着砍头灭门不成?要是连张成义张大人都觉得无计可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回头去找讨逆将军储定安,储定安莽汉一个,比起自己来更是没有主张,两人愁眉苦脸地枯坐了半晌,啥计谋都想不出,一开口言及的都是灾难祸患,白白地叫人泄气。
临别各道珍重,储定安忽地恶声恶气地自语:待我找到那姓林的,一刀把他做了,临死咱也拉个垫背的!
马行原吓了一跳,连忙拉住他:老弟万万不可莽撞!宫里未必就知晓咱们的计谋,姓林的又没有真凭实据,你想想,要是宫里得知了咱们深夜密会的事,还容得咱们在此闲话?恐怕在朝堂上就先下手为强了。
储定安想了想便道:老哥说的也是。不过群臣朝贺上皇的事既然不成,眼下总要想出别的法子才行。要不然我连一天安稳觉都睡不成,想起来就担惊受怕,说不定哪天就大祸临头,给抄家灭门了!
马行原说:事情都到这份上了,怕有个屁用。等太保张大人心情略平复些了,咱们赶紧去合计合计。南营那里我跟几位有过命交情的老兄弟试探着提了几句,虽说有些犹豫,到底这天大的事,谁也不敢拍胸脯、打包票应承。不过也不是一点门儿没有。
储定安喜道:好,能有门儿就好!承运八年,咱们一开始不也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哪个又敢拍胸脯打包票。不过等做下事情以后,胆横心壮,便一条道儿走到直。那日要不是我见机行事,叫手下纵火焚烧宫门,吓破了宫里贵人们的心胆,上皇哪里就肯退位内禅……
马行原瞪了他一眼,骂道:你又胡说八道的讨人嫌!当年的事怎么能跟现在的事相提并论!当年咱们是为人所逼,受人驱使,然而良知未泯,忠心犹在,所以为国除奸,将功赎罪。
储定安笑道:是,是,老哥说的极是。咱们良知未泯,忠心犹在,所以要为国除奸,将功赎罪。老哥哪里想出的这等好辞,怎么听怎么舒服!
回到衙署,刚刚坐定的马行原还没有喘匀一口气,就听有内使前来宣诏,顿时脸色一片煞白,冷汗涔涔而下,他以为东窗事发,密谋败露,那一刻心中忧惧欲死,直想拿刀一抹脖子,自行做个了断。
幸而他没做这鲁莽之事,接过诏令,送别内使,马行原抹了一把渗出的冷汗,心中暗道一声:侥幸!不过宫里突如其来的下诏收捕太保张成义,依然显得大事不妙,牵涉其中的人迟早都得大祸临头。
马行原皱眉思忖:莫非那日太保府上的密谋已尽为宫里知悉?想想不大可能。刚刚才跟储定安说过,宫里若是知悉其事,岂有不把自己和储定安一并收捕拿下的道理。更何况这收捕拿人的诏令竟还发到自己手上。
也幸亏诏令落在自己手上,收捕太保的事暂时尚能缓上一缓。马行原不敢迟疑,当下抢过一匹快马,疾疾往宣和坊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