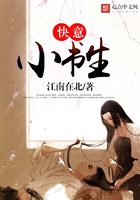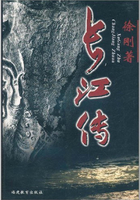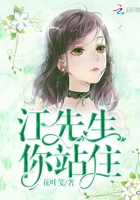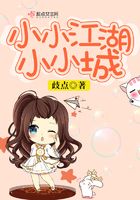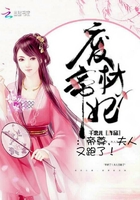风过雨停,天色微熹。扬州府署的奴婢下人们正为宁安公主回京而四下忙碌。因怕路上遭逢溃兵流贼,驸马陆怀特地点了五百兵士随从护卫,自己也一直陪送到西门外的十里长亭。
因为整夜都没合眼,公主面色苍白,妆容也无心整饰,心事重重的她,斜倚在宽大的车厢里,听着耳边单调乏味的马蹄声和车轱辘的转动声,觉得胸闷意躁,心里好象被什么东西拉扯着,沉甸甸地牵动五脏六腑一起往下坠落,坠落到一个无边无垠的深渊……离京师越近,宁安公主就越是不安,只是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双手合什,口中默祷,直到心神略微平复。
神思困倦,疲乏无力的宁安公主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张软和净洁的床,她躺在上面,放下所有恼人的心事,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等到睁眼醒来,发现一切不过是场荒唐离奇的噩梦,她只要轻轻一拂手,就象掸落灰尘那样,把梦里的困扰、忧虑、愁绪都掸入虚空。
这就好象承运二年,她从东胡归来,也是睡了长长的一觉,过往的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
宁安公主眯缝着眼睛尝试着让自己睡去,只是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她心底忽然一惊,象是什么声音悠悠传来,在呼唤、在提醒、在喃喃诉求。这之后睡意全无,怔怔忡忡有些失神丧魄,她听得出那是庆王昊的声音,她奇怪为什么隔了这么远她竟还听见了他的声音。
一方牙牌从衣袖里滑出来,掉在自己的脚边,莫名的悲伤油然而生,公主的眼泪滴在那面牙牌之上,先是一滴,然后两滴、三滴、无数滴。
千不该万不该,庆王不该出现在瓜洲。昨天,当她一眼看到这方正面镌有“散骑常侍”四字,边上朱书“勋字第一百四十七”的牙牌时,她就隐隐觉得不妙。
牙牌这样的东西,只在出入宫禁大内时所佩带使用,一旦出京即不许用,外任到地方为官则要追缴收回。至于牙牌上所镌的“散骑常侍”乃是随侍在帝侧的清要显贵之官,扈从伴驾,如影随形,这是特地授给燕国长公主养子于凤楼的贵职。而这个于凤楼,虽说现在是长公主的养子,身在朝中,位居显要,但追根溯源却是当年自家府上买来的戏子歌童,只因长公主见爱而转赠于她,现在他的牙牌竟落到瓜洲巡检的手上,公主与驸马自然感到万分震惊。
所以公主才要藏身到那座屏风后面,亲耳聆听瓜洲渡口的巡检向陆怀禀报得到这块牙牌的由来。只是这一听之下,公主自然也就绕进这桩事里,难以脱开身子。
昨夜酒宴未罢,公主即藏身在屏风后面,听陆怀询问瓜洲巡检。而那巡检伶牙利齿自把得到牙牌的来龙去脉叙述得甚是详细:
“午后风狂雨骤,水流湍急,江上并无行船,小的们都缩在衙署,躲风避雨,无事可做,直到日落酉时,才忽见有死人无数,漂浮在江面之上,被风浪波涛推送到岸边,方知江上不远处有大船翻沉。小人即领着手下查验尸身,其中既有身着官服的老爷,也有穿甲胄的将尉,更有净过身的内使公公,还有好些女子都穿着宫装……小人心中大骇,忙着指挥手下打捞,看看有没有溺水未死的?果不其然,有人因抓住了漂在水上的桅杆而侥幸未死,只是被水呛得昏厥,这牙牌便是其中一人所佩。与这人一同抓住桅杆的,尚有一人,约莫十三四岁的模样,披发无冠,身上亦无腰牌,只是身着的明黄衣袍,前后皆绣有团龙,小人虽然愚鲁,一望也知是宫里的贵人,所以不敢稍待,斗胆赶来上报……”
屏风里外,陆怀和宁安公主都听得心寒胆战,瓜洲巡检所描述的场景不用说是亲身经历,单是去想就觉得惊心动魄。
那巡检意犹未竟,继续说道:除了这块牙牌之外,小人那儿还检搜了许多腰牌,不过都是银铜木头的,有中书舍人,有羽林都尉,有翰林供奉,有宫门值守,还有什么尚宫、尚仪,都比不上这块牙牌贵重……
公主这时已隐约猜出大概,正想着要不要从屏风后面发话,陆怀已赶在自己前面吩咐下去:你所说的,干系重大,如今你且回去,好生看护生者,本官带了人马随后便到,此事暂不得生张外泄,否则唯你是问!
待那巡检唯唯而退,宁安公主忙从屏风后出来,夫妻二人面面相觑,都知道这事棘手。其实无需说破,公主驸马心中均已明白,巡检口中那个十三四岁,身穿绣龙黄袍,跟散骑常侍于风楼一同获救的,除了庆王庆庶人之外,再无别人。
想来庆王必是仓促乘船离京,中途不幸遇上风浪,翻船落水,虽然侥幸未死,可是既然流落到扬州府的地界,自己又怎能视若无睹,或者藏匿不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既然逃出生天,总是有上苍庇佑!”公主当下与驸马商计,虽无善计良方可力保无虞。只是觉得庆王虽然僭号称尊,狂妄悖逆,但当年登位到底也是出自于上皇内禅,何况他本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当初既未鼓动指使,又非同谋协从,登基后亦只是傀儡,并未亲政掌权,若将所有罪责都加诸于庆王头上,自不能公允服众?即或议其有罪,也当罪不至死。宁安公主与庆王同出一父,谊属至亲,于情于理,当不能置身事外,见死不救。
于是让陆怀先点上几百人,备下车轿,前去瓜洲相迎。
等到陆怀带人回来,夜已至深,宁安公主前去探视,庆王和于凤楼尚晕厥未醒,公主吩咐灌以姜汤,并以燕窝人参之物助其恢复元气,若是醒来,当速来报。
公主和庆王既非同母,且因年龄悬殊,平常并不特别亲近,然而她与庆王毕竟源自同一血脉,拥有共同的父皇,所以公主对于庆王的命运自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慨伤怀。可怜的庆王就好象当年流落在东胡的自己,四顾茫然,走投无路!自己万幸当年还能遇到出使东胡的周如喜,而庆王此生又能遇到谁呢?
这一夜自是无从睡得,跟驸马连夜商议明日回京后该如何禀报,因为事涉重大,固然不敢隐瞒藏匿。然而一想到自己要入宫告禀,宁安公主内心始终觉得有些愧疚。跟自己当年的万幸比,庆王可当真不幸,他所遇到的人非但救不了他,恐怕还要亲手把他推下深渊。
第二天天尚未亮,公主询问起庆王的情形,听说尚未苏醒,竟暗自松了口气,她实在不知如何与庆王见面,这下正好两相避免,当下匆匆上车,踏上回京之路。
永寿宫,光明殿,汪皇后正安逸地坐着喝茶。在经历了那些个不眠不休的日子之后,她现在终于能够安逸地坐下来喝茶,或者说,皇后娘娘要做出这个安逸自在的样子给别人看,能笑到最后的人,自然总是安逸的,在如今的京城,在永寿宫大内或长庆宫南内,谁人敢说不是呢?
侍者进来禀报:宁安公主求见。
汪皇后放下手里的茶盅,脸色有点不悦,外命妇都进宫朝贺过几回了,她这会儿才想起父皇母后,让她先等着吧。
刚由宫正监升为御府监的何知书,因受了公主的请托,赶紧上前回话:公主早想进宫庆贺,只因昨儿下起暴雨,不得已在扬州多担搁了两天,今儿一早就急忙往京城赶,连自家的府邸都未曾去得,也因此公主连大衫礼服都没有换上,只说是有要事禀告。
汪皇后皱了皱眉头,说:那就叫她进来吧。
宁安公主进殿,磕拜之后,皇后赐座赐茶,宁安公主的心这会儿又跳得急促,她想借喝茶来掩盖心中的不安,只是她控制不住颤抖的双手,茶水都被抖出杯子,淋淋漓漓地溅洒在胸前的衣襟上。
汪皇后显然注意到了宁安公主的异样,她不发一言,只是略带狐疑地看着公主。
宁安公主被她看得越发慌乱,她低着头,竭力躲避皇后的眼光,她觉得母后的目光象极了两枝利箭,一下子剌穿她的身体,把她钉在那儿动弹不得。
定了定神,宁安公主蠕动嘴唇,吐出似乎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请母后摒退左右,儿臣有要事禀奏。”
声音虽然低微,然而皇后竟是听见了,她轻轻一摆手,殿中的宫婢侍从都悄然退下。
“你是不是有了庆庶人、唐庶人的消息?”汪皇后看着公主,若有所思。
宁安公主心神一凛,小声回道:母后料事如神,儿臣正为此事而来。
闻听此言,汪皇后竟也动容,她身子前探,宽大的袍袖不意间扫落了手边的茶盅,这声落地的脆响吓了宁安公主一跳,她不敢抬头,眼睛死盯着皇后脚下那摔成几瓣的茶盅。
汪皇后这时反到显得平静,她换了个坐姿,淡淡地说:诸逆乘船下行应该是到了扬州府的地界。想来公主是知道庆庶人母子的下落了。
宁安公主赶紧趋身上前,将袖子里的牙牌递给皇后。
汪皇后初不知何物,待细细看过,眉头一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见牙牌如见其人!散骑常侍的牙牌既然在你的手上,自然他和庆庶人也都在你的手上。
宁安公主低声道:“母后明察,正是如此,详情容儿臣细禀。”当下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向皇后娓娓道来。
汪皇后听罢,眉头舒展,点头笑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语毕却收起脸上的笑容,长声叹息:可怜你兄长竟没有等到今天!他要是泉下有知,当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宁安公主赶紧起身,整衣下拜:请恕儿臣不孝,惹母后娘娘伤心。
汪皇后说:你起来吧,我只是想起你兄长了。唉,说来也有好一阵子没有梦到他了,以前总是害怕梦到,怕看他伤心难过的样子。可是这两日,你兄长又频频入我梦来,依稀还是少年时的模样,蹦蹦跳跳地走在我面前,时不时地回头瞧我,却不肯好好跟我说话,我刚要追上的时候,他就在梦里消失不见了……哎,如果下次梦到,我一定拉住他,好好跟他说上一阵子……
殿中静默,汪皇后低头抚额,宁安公主陪坐在侧。过了一会,汪皇后象是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地说:寂寞了这些年,你兄长终于不再孤单冷清了!
宁安公主有些紧张,她绞着手,思忖着怎样进言求情,才能为庆王请命。当下长跪磕头,求告说:庆庶人狂悖不孝,神人共弃,虽罪无可恕,念其年幼无知,情有可悯之处,儿臣斗胆敢请母后网开一面,格外成全,以存其一命。
汪皇后怔怔地看着她,脸上全无表情,说出来的话也冰凉似水:若你兄长仍在,你们出面替幼弟求情,或可法外施恩,恕其不死,可是你兄长竟因此殁了,离他二十二岁的生辰还差了三月!这些事别人或早已忘记,为人母亲又岂能忘得?
宁安公主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还请母后节哀顺变。
汪皇后沉声说:这些年每逢你兄长的忌辰,我都不敢去春华宫,就怕触景生情,徒增伤悲,每每想起你兄长英年早逝就心如刀绞,这些年我忍住眼泪,百忍千忍,忍得十分艰难辛苦,就是想着哪天能够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
宁安公主还欲再说,汪皇后却打住她的话头,说:公主一路劳顿,想也是累了,先回去歇着。这件事容我静一静,想一想。
宁安公主自然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磕头告退。
看着宁安公主拜辞而去,汪皇后有些愣神,想起故去的晟儿,两行珠泪不知不觉垂挂在脸上,要是她的晟儿不死,她会这么赶尽杀绝么?身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本当以仁厚之心、慈爱之怀,抚育黎民百姓,而庆庶人虽说狂悖忤逆,罪不容赦,但诚如公主所言,因其年幼无知,自有可悯之处,倘若皇上心生怜惜,法外施恩而恕其不死,则未免不成为将来的祸患。所以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即使再情有可悯,庆庶人也不得不除!想当年因为自己一时的妇人之仁,没能当机立断把唐觉之除掉,结果反让其一步步坐大,最终酿成了承运八年的惊天之变,也因此害死了晟儿,一念之差,妇人之仁,可恨可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唐家既做得了初一,怨不得我做十五,自作还须自受!庆庶人若不遭此恶报,吾儿又如何能够安心瞑目。”汪皇后慢慢拭去脸颊边的泪迹,心里反复盘算,如何干净利落地处置庆庶人,才能既不露痕迹,又不落骂名。
皇后为此颇费了一番思量,幸而她酷爱读史,尤其熟知历朝历代的后妃列传,所以思量之后,心有所得,当下叫何知书取来《唐书》,翻到《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传》这一篇,命何知书当面诵读了一遍。
何知书有些诧异,不知皇后此举何意?捧读史书之际,心中便在揣摩体会,正浑然不知要领,却听汪皇后说:读史使人明鉴,象武则天行事,就往往出人意表,真不愧为千古女帝。何大监可知方才公主进宫,所禀何事?
何知书垂手道:老奴愚鲁,祈请娘娘明示?
汪皇后把牙牌递与他看,淡淡地说:刚刚公主禀报说,庆庶人如今在扬州驸马的官衙,所以少不得要让何大监陪同公主往扬州去一趟。
何知书心思敏捷,当即明了皇后话中之意,忙道:娘娘差遣,老奴自当遵令奉行,必定使娘娘满意。
汪皇后点头道:你去吧,事宜速决,以防夜长梦多,更宜隐秘,万不可让外间生出闲话。
宁安公主回到府中还不到一个时辰,御府监何知书便悄然而至。相见之后,何知书并没有虚言伪饰,反而开门见山:老奴此行,专为庆庶人的事而来。依老奴的意思,此事不妨按照唐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的旧例。事既隐秘,里外难知,时日一久,一切湮灭如过眼云烟,岂不是好!此去扬州,若公主不嫌弃,老奴当侍奉左右,以供驱使。
宁安公主大吃一惊,昭成顺圣皇后的旧事,她依稀知道一些。想想这位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命运多舛,令人唏嘘。其本是唐睿宗的德妃,因生下唐玄宗而被追谥为昭成皇后、皇太后。当年因遭人诬陷而不幸遇害,然而蹊跷的是,并无人见过或能举证窦氏被害于某时、某处。只知道长寿二年正月初二那天,窦氏与皇嗣妃刘氏一道进宫朝觐武则天,然而就在入宫朝觐之后,踪影全无,此后再也没人见到过她们,两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落从此成迷。
睿宗复位和玄宗登基都下诏征求过知情者,以便收敛二人的骸骨迁葬山陵,只是一直无人知晓,就是当初二人入宫朝见的地点——嘉豫殿,后来被掘地三尺搜求,也是一无所获,最后只能以招魂的方式为已故肃明皇后刘氏、昭成皇后窦氏落葬。
宁安公主听说要援此旧例秘密处置庆庶人,内心极为惶恐,慌忙道:母后于此可有懿旨?庆庶人非比常人,若无明旨,岂能擅行诛戮?
何知书一笑,拱手道:公主此言差矣。皇上复辟重祚,这头一件事就是诛凶戮逆。若依皇上的敕谕,庆庶人、唐庶人以及罪妇唐陆氏一干人等,皆系祸国殃民的元凶首恶,天下军民,人人得而诛之!获其首者,以功封侯!活捉来献者,封之以伯。诏敕俱在,岂不是明旨?老奴乃一内官,并不求侯伯之封,只是愿为皇上、朝廷略尽一点微薄之力。且因事涉宫闱帝胄,所以不宜以刑律加以诛戮,而改用家法伺候,故需里外隐秘,以策万全。
宁安公主仍不死心,恳求道:“请公公稍待,容我进宫,再去求求父皇母后,姑念庆庶人年幼无知,望能饶其一死,也算是救人一命,万望公公成全。”说时深深一揖。
何知书赶忙下跪回礼,正色道:公主所请,老奴本不敢不从。只是老奴忝为御府监,职分所在,故不得不为,尚请公主多多体念老奴的难处。事不宜迟,迟恐生变,敢请公主早备车驾前往扬州,老奴愿为前驱,效力于鞍前马后。
宁安公主长叹一声,知道事不可为,庆王性命难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