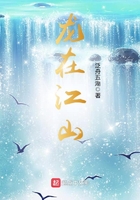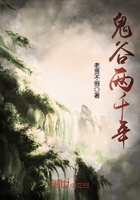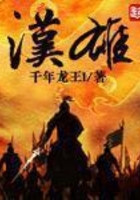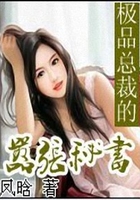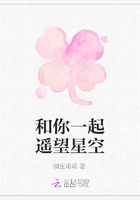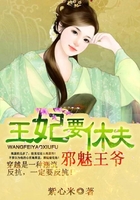汪皇后虽说有些不情不愿,但册立太子妃的事终究拖宕不过去,周太后那里因为怕夜长梦多,也是不断的催促,所以一挨到立冬,皇帝就派了陆太师和唐太尉为正副使,分别前往京兆尹周如乐和左相唐会之府上,宣布敕命。
周如乐的孙女周鸾顺利的被册为太子妃,而唐会之的女儿唐媛则成了太子良娣。
入宫的那一天,获封为太子良娣的唐媛哭哭啼啼不肯上轿,她明明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早被列为淑女而进宫接受调教,怎么事到临头却忽然降级成了太子良娣。
良娣之母南安郡夫人陈氏流着泪又哄又劝:好孩子,别哭了,进宫后好好侍奉太子,幸好宫里还有皇后娘娘站在咱们这一边。
唐媛委委屈屈的上了喜轿,当太子良娣的舆轿经过宫廷的正门丽景门的时候,唐媛潸然泪下,她知道朝廷迎娶太子妃的鸾驾刚刚才从丽景门通过,而她自己这一生却是再也没有机会能够让大婚的喜轿从丽景门走一遭了。
太子良娣的舆轿是从西边的偏门青华门抬入到春华宫中,唐媛在喜娘和嬷嬷们的引导搀扶中下了轿,还没有见到太子,到先见着了婆婆汪皇后。
唐媛含泪下拜,汪皇后扶起她,对她说:本宫知道你受委屈了,记住要忍着,忍到出头的那天,你的苦就算熬出来了。
皇后的温言暖语在太子良娣唐媛幽怨愤激的心中点起了一盏照亮前程的明灯。唐媛闻言拜伏在地,哽声道:儿臣进宫,一切全赖母后娘娘栽培教导……
汪皇后点点头:好孩子,你起来吧。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不要太过伤心了……
青华门里的春华宫雕梁画栋,装修一新。这里是太子晟大婚的居处,也就是俗谓的太子东宫。
唐媛的舆轿被引入到春华宫,然后在喜娘和嬷嬷们的陪伴侍候下,孤独的呆在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洞房里。
洞房其实也分成了两个,大殿的后寝是属于太子爷和太子妃共度良霄的正室,西边的配殿才是她这个太子良娣的侧室,她得在这里呆到太子和太子妃的大婚仪典结束。
只是这场婚礼的仪典好象永远不会结束,热闹始终在延续着,喧嚣的鼓乐和鼎沸的人声,一阵一阵的传来,冲天的璀灿烟花在空中欢欣鼓舞的闪烁变幻,这些既与唐媛有关,也与她无关,她只是一个陪衬,用自己的冷清去陪衬别人的热闹。
唐媛越想越不是滋味,所以她的眼泪慢慢的就涌了上来,虽然在进宫前就被一再关照,在宫里除非是丧事,否则是不能暗自伤心的,更不允许流泪哭泣,但是唐媛还是流泪了,在这个洞房花烛之夜,在她自己将要成为人妻的晚上。
因为太子的大婚,皇帝大赦了天下,并赐宴于群臣。
婚后的第三天,太子领着自己的元妃和良娣到显德殿拜见父皇母后。皇帝照例是嘉许勉励了儿子媳妇一番,汪皇后却是仔仔细细的端详打量着太子这一家子。
成家后的太子好象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他有模有样的坐在那儿,神态恭谨而端庄,呵呵,好象几天前,她跟前的晟儿还是个牵着自己的衣角,不谙世事的孩子,现在呢,已经有七八分象个大人了,一个小大人。
汪皇后想到这些,心中忽就泛起一阵伤感,孩子大了,娶亲了,成家了,再也不在自己的眼前身边嬉笑玩乐了,而皇上和自己却都老了,老了!眼睁睁的一天比一天的老去,总有一天,会老得跟陈太后一样,那样岂不可怕!人的这一生可是怎么活,也活不够的啊!
汪皇后的目光从太子的身上慢慢移到太子的妻妾脸上,她先盯着太子妃周鸾看,直看得太子妃弯腰缩颈,把头越埋越低。
太子妃的那张圆盘大脸,汪皇后怎么瞧都觉得不顺眼,想到将来她将要取代自己,成为皇后、太后,母仪天下,主宰后宫,汪皇后觉得她的命真是生得太好了,女人这辈子所梦想希翼的一切,轻而易举的就都加诸到她身上,这真真有些太便宜她了。
看完了太子妃,再看太子良娣,唐媛的眼睛现在还有些微微发红,汪皇后不禁多了点怜惜,这可怜的孩子,离太子妃只差了那么一步,就是这么一步,就误了终身。哎,这人算可见得总是比不得天算!但是也不是就从此没有机会了,想想自己当年也不过才是太子的嫔御,姓宋的太子妃那时可是何等的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结果呢,没撑上几年就死了,皇后的宝座也终于不是她的!
汪皇后还在浮想翩翩的时候,太子已经起身,正率他的妃妾向父皇母后行儿子媳妇的家人之礼。受了儿子媳妇的叩首礼,皇帝笑呵呵让人去请太后娘娘的圣驾并叫各殿的诸妃嫔都到场,同时也让宁安公主和驸马爷带上他们的孩子进宫来庆贺太子的新婚之喜。
其时,显德殿里,众人欢会,公主的儿子“奴奴”被王宁妃和陈康嫔逗弄得“格格”直笑;庆王昊跟张福嫔她们绕着柱子玩捉迷藏;周太后一手拉着太子妃,一手拉着太子晟,笑吟吟的要他们早生贵子,最定根基,使江山后继有人,以此告慰祖宗;而汪皇后则叫过唐良娣,关照她凡事不要拘谨,放自在些,这宫廷也跟平常人家无甚分别,只不过地方显得大些,杂七杂八的人也多些……
皇帝的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的会集于一殿,到也显得母慈子孝,家和人兴。
这样的阖家欢聚的融融快乐从腊月开始,一直延续了许多天,因为宫里接下来就过年了,过完了年还有元霄灯节,还有种种迎春纳福的仪式,都是些相会团聚你来我往的喜兴事。
国家安好,宫廷祥和,除了河山只剩半壁这样一件令人扫兴泄气的事,否则取号“承运”的这几年真可以比拟前朝的那些所谓的太平盛世。
太子的大婚好象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吉祥好运,跟普庆四年的祸不单行相反,承运四年的正月刚过,喜讯就接二连三的传来。
首先是靖王的老巢蜀地西川来人了。靖王的部下,驻节于蜀地的成都留守准备奉南都的朝廷为正朔所在,这个叫方大用的成都留守派出心腹参军秘密潜来南都,欲与朝廷方面密议归顺投诚的事宜。
周太宰闻讯,内心狂喜,亲自出马与成都来的参军会商。参军表示:靖逆谋篡,天怒人怨,方镇帅深明大义,不肯助纣为虐,为祸天下,愿意归顺效忠皇上。但是有个条件需要皇上恩准,皇上和朝廷如果肯以方镇帅为封藩的王臣,允许其子孙世代驻守于西蜀,则蜀地立即可以易帜反正,共讨大逆元凶,报效朝廷和皇上。
周太宰赶紧进宫去奏明皇帝,他把会谈的情形大致向皇上一一说明,然后周太宰叩首对皇帝说:方大用前来输诚投效,可见靖逆已是众叛亲离,覆灭指日可期。方大用此举虽有要挟朝廷,裂土封王之意,但是蜀地如今非我所有,不妨顺其所请而封之,一来使天下明朝廷正朔所在,二来方大用据蜀中称王,靖逆必不肯罢休,两下争斗,而我可得其利,三来可再派使节前往东胡,或合纵或连横,只要能够剪除靖逆,澄清宇内,皇上都可以试而为之。臣以为方大用表明降意,实乃千载难逢之机,皇上应予笼络,并能有所示意。
周太宰情绪激动,他在御座前慷慨陈辞,脱口而出的飞沫几乎都要喷溅到皇帝的脸上,皇上也几乎沉迷在周太宰所说的那一幅光明灿烂的前景里头。收复中原,还都洛上,快要放弃的梦想,这下似乎又有了实行下去的可能。
皇帝被周如喜的话所打动,当下也不含糊,指示周如喜说:太宰与蜀地商谈,一切须以大局为重,细枝末节可以勿论。方大用既然能够向朝廷输诚,朝廷应待之以礼,示之以诚。只要方大用能够弃暗投明,从此与靖逆一刀两断,其所言裂土封王一事,朕可以允其所请,封他为巴蜀郡王,其爵位子孙世代承袭,为朕永镇西川,亦不失为朝廷膀臂。
周如喜依据皇上的圣意与那参军商谈,自然满足了方大用所提出的种种条件,双方以此为基础,谈得极为相投。
那参军告辞前,周如喜亲往送行,并淳淳告之说:弃暗投明还是助纣为虐,相信方镇帅自有判断,只要巴蜀愿意归顺朝廷,朝廷亦将不计前嫌,除方镇帅将晋号王爵之外,镇帅以下的官吏僚属亦能同沐皇恩,皆将得到朝廷的授职赠官,其既往罪愆自然也就一笔勾销。
这事过去后不久,房州又传来大捷,房州太守带人破了盘踞在神农大山中的一股土匪。
这股土匪本系房州襄阳一带的猎户和农户,承运元年,皇帝和靖王相互攻战,靖王欲将此地的居民北迁,当地一些人故土难离,于是落草山中成为匪盗,由于房州襄阳地与巴蜀北国接壤,神农大山又山高林密,朝廷虽屡屡用兵剿匪,却皆不得其效。
这一次房州太守却借山匪过年之机,突然带兵围攻进剿,居然让他偷袭成功,将山中匪寇一网打尽,于是上表朝廷奏捷请功,同时请皇上降示如何处置这些山匪巨寇。
皇帝看了眼表文,立刻提起朱笔御批了一道上谕:一干贼人据山为寇,自弃于天地,均应就地正法,以明正典刑,且为作奸犯科者戒!
搁了笔,皇帝想想还须再批上几句话以示对房州太守的嘉许,但是眼光不经意的一扫,这才看到表文末了的,差点被他忽略的一段话。
“……山匪中有被掳的妇女凡三十余人,臣一一鞠讯,其间有人当堂指称,云先帝文宗之女亦在被掳妇女当中,臣再三问询,详情难获一二,事关皇族帝姬,臣不敢擅自处置,现将一干涉嫌女子送往京师,以待陛下派人查验,自然真伪立现……”
看着文中的这段话,皇帝一时有些发怔,已至于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他皱着眉头细想,这文中所说的先帝文宗之女岂不就是皇姊燕国长公主么?只是皇姊若是获救,怎会这么风平浪静,她不大哭大闹大耍威风,就已是谢天谢地,何至于太守再三询问也难获详情?皇帝转念又想,莫非有人诈称帝姬皇亲,以骗取荣华富贵?
皇帝思虑了一番,决定派内廷令王守礼前往详察明细。
这一来一去约莫七八天,王守礼回到宫中,见了皇上,便禀告说:奴才此去见过了,不过实在难以辩认清楚,或者先请进宫来,让太后陈娘娘识别一下。
皇帝诧异道:莫非外形有改观?居然连你都认不出?就算你认不出她,她难道也认不出你?现在人在何处?待朕去见见。
王守礼道:奴才已将人接到了宗人府,皇上既然有兴,不妨亲自去看视一番。
宗人府就在宫城南门的丽景门里,皇帝当即启驾前往。
到了宗人府,王守礼一路引着皇上来到一间屋子前,皇帝悄悄走过去,站在窗子外面朝屋里窥看。
屋里有两个民间妆扮的女子,此时都背对着皇上,其中一个年青的女子正在替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梳头,她一边梳理,一边喃喃的自言自语:你说,皇上还会认得你么?皇上要是认不得你,你跟我可就死定了……啊,我忘了还有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怎么会不认得你……太后娘娘只怕高兴都来不及……
“……太后娘娘……你说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她在哪里?……”那女子闻声转过头来,四下里张望着。当她的脸转到窗口这一边时,皇帝已经瞧出来了,这女子虽然看起来变化颇大,然而的的确确是自己的长姊——燕国长公主福姬。
皇帝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步踏进屋子,王守礼紧紧的跟在后面,口中也适时地拖起了长音:皇上驾到!
屋里的两个女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喊给吓了一跳,梳头的女子失手丢掉了手中的梳子,身子哆嗦,不知所措。那个貌似燕国长公主的女人却是慌忙起身,满屋子的找地方躲藏。
王守礼抢上前去将她拦住,满脸堆欢,笑嘻嘻的说道:长公主,您这是要往哪儿去?您可瞧瞧是万岁爷来了,万岁爷可想你得紧……
燕国长公主想走走不脱,想逃也没地方可逃,突然间怪叫一声,一把抓起王守礼的手,张开嘴便往他的手臂上咬去,咬住了便不肯放松。
王守礼“呀、呀、呀……”咧嘴大叫,使劲挣扎了半天才挣扎了出来,当下苦着脸溜到皇上身边,低声说:不是奴才敢瞒骗皇上,奴才只是不敢将实情告诉皇上,皇上如今也都瞧见了……
这下皇帝终于看出来了,燕国长公主似乎有点不对头,她两眼无神,表情呆滞,行为也象是有些疯颠。
皇帝想不到他的姐姐燕国长公主会变成现在这般疯疯颠颠的模样,他注视了她姐姐一会儿,就别过脸不忍再看,只是吩咐道:先送她进宫,注意千万不要吓着她,也不要惹她发怒,另外叫太医来给她看看。
燕国长公主当天就给接进了宫中,皇帝为此特意请来汪皇后,告诉她燕国长公主的现状,汪皇后听了,也跟皇帝一样意外。
当下去往宗人府看视长公主——离得远远的,提心吊胆的看,(听说王守礼差点被她咬掉手臂上的一块肉),隔了好几个护主的内监,汪皇后和颜悦色地跟她说话:长公主,你还认得我是谁么?
燕国长公主看到这么多人涌进屋子,吓得有些魂不附体,身子蜷缩在墙角,抖抖索索地拿衣袖掩住面孔。
汪皇后连问了几声,长公主都没有回应,无奈之下,汪皇后叹息一声,心道:长公主这个样子,到怎么跟陈娘娘说起呢?她现在病得这么重,只怕经受不住这样的场面。
汪皇后想了想,让人去叫宁安公主过来,告诉她,燕国长公主,她的福姑姑回来了。
宁安公主又惊又喜,急急忙忙地想去看她。汪皇后说:她情形不大好,你可不能惊动她!当下领着她来到长公主的居处。
宁安公主乍见之下,大笑大嚷:福姑姑、福姑姑,你可回来了!咦,这不是了缘小师父么?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没人告诉我一声,早知道你们回来我应该亲自去迎接……
燕国长公主看到一拨人刚走,这会又来一拨,心中害怕,慌慌张张的想往帘子后面躲。
了缘拉住她的袖子,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慰她说:别怕,皇后娘娘她们都是来看你的,你快瞧瞧,小公主也在这儿呢?
宁安公主这下也瞧出了燕国长公主的异样,她张目结舌的轻声说:福姑姑她、她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她这是怎么啦?了缘小师父,这、这、这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