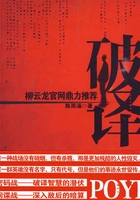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小时候觉得天经地义。大了我却反复琢磨,太阳为什么不能与月亮同时升落。
伊琼那年到美国,我没去机场送她,我在零乱的窝里睡到日上三杆。我那时是时间的富翁。我想象着一个叫曼格尔的美籍瑞典小伙子随侍她左右,高大强建,无微不至。登上飞机舷梯的那个女星绝对不会涕泗滂沱,至多对生养她的国土,用上犹抱瑟琶半遮面的匆匆一瞥。
“一个令世界不能小觑的东方。”
上述这句话,其实是三年后的今天,我心里对伊琼的评价。当时我决没有如此轻松。在那段黑白交错、流荧迸闪的年月,伊琼是迷乱我生命舞厅的频闪激光灯,使周围风景纷呈怪诞,而我是灯下一个蹩脚的舞客,借了她的磁激,抖擞出一路荒唐。后来的柳荻开玩笑说我是“扶不起的刘阿斗”,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与伊琼的罗曼史,屈指算来也只一年。如果伊琼本人可以在我的人生座标图中用一个交叉点来表示,这个交叉点便是个体户何轩的摄影室,与三年前那个微醺的夏季黄昏。
我去何轩的摄影室参观时,他正忙得鼻塌嘴歪,要向首届南方16省新潮摄影大奖赛呈上得意之作。
说来荒唐,何轩与我知青时并不十分要好,以后十年音讯沓然。可现在我们一见如故。假如不是我因未婚妻到南京短训而百无聊赖,以及与机关里庸俗自私的同事无法沟通,何轩那身随便怎么也不能遮住的匪气,是决然不会令我那肃然起敬的。
何轩告诉我,他是无师自通的摄影天才,曾跻身两届全国摄影大展,使省摄影协会诸多历年老将没处活人。
这话不错。何轩在他布置豪华的摄影世界里,是模特儿的上帝。五个妙龄女性在门厅里啜茶,目光粼粼,莺声细细,等待何大师聘用。何轩屈尊征求我对她们的看法,我很自知之明地说客随主便。他大乐,但没有表示指定其中谁人上场的意思。
对我疑问的眼光,他避而不答,笑容里,藏着识货者宝物在手的狡黠。
“你总会大开眼界的,”他说,“没问题。”
伊琼在六点差一刻跚跚到来。
最初一下的感觉是震聋发聩,或叫云开日出。干了数年发财勾当并号称腰缠十万贯的何轩、以及他精心装璜的摄影室和五个明丽少女,统统在伊琼进门的瞬间黯然失色。她的美不可言说,只能用小提琴拉出来。
当时的印象中,伊琼绝对是一只成精的媚狐,猎人看见她,猎枪只会瞄着自己的脚趾头打。她的脸很古典,有一种既奢华又守旧的宫庭情调。不过千万别想让她只有一种固定模式。她在与摄影室相连的另一间小屋里脱光衣裙,全身按狗日的何轩要求抹上褐色的稀泥,又用七、八只500瓦的灯泡烤成龟裂的旱田以后,再次站到摄影室的聚光灯下,野性阳光、原始沼泽、沙漠蜃气和雌兽的浓腥,立即扑面而来。
何轩在揿动快门的过程中悄悄赞叹,说此种尤物千年一见。他说话时牙齿微微磕碰,全身痉挛,仿佛一幅定名为“终极”的抽象派作品,已呼啸着打倒了半个中国所有上万名高手。
呆看着伊琼,我忽然忆起几年前游峨眉山九老洞,我和三女两男在洞中迷路,感受到生命将在黑暗中一点点流失,阎罗的触舔实在而冰凉。后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出,就想疯狂地对着太阳下跪,把肉躯当作牺牲敬献上它的祭案。
现在面对伊琼这颗太阳,类似的感觉在体内油然萌生。
“还记得伊明亮吗?知青点里那个有名的小人物兼笨蛋?”
谁,是谁在说话?是何轩。
我的思维回到了现实。谁不知道伊明亮谁就没在我们知青点插过队下过乡。伊明亮在乡下过19岁生日时,我赠过他一本印有李铁梅高举红灯的剧照的硬面笔记本作礼物,扉页上题着当时流行的句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初冬改土造田的山坡上一声剧烈轰响,忽然爆炸的哑炮将伊明亮粉碎后送入黑暗的历史。全知青点九个男女知青在冬日的寒风中嘶声哭嚎,用火钳从山边地坎挟回伊明亮半爿耳朵和三个手指,把他葬入了知青点背后的菩萨山。
伊琼到换装室去了,我转身走出摄影室的门。我不敢再看将穿上艳丽衣裙的她,我仿佛跋涉在远古的荒原上,九颗太阳辉煌了天际,浴化了我已不年轻的心。
骸骨难收的哥哥,动人心旌的妹妹。
当时我一下就决定,打死我也再不走进何轩的摄影室。
我以为我的心早如死水,我怕失去自我。
同样,那会儿,你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命运居然会变成妖姬般艳美的伊琼,借她的魅力作杠杆,玩笑般地撬变了我人生的一小段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