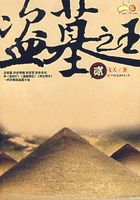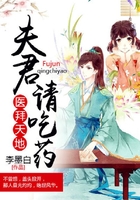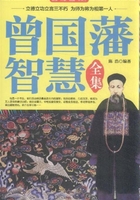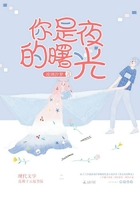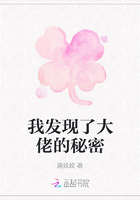1977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7月,邓小平再次出山,第一件事就是为知识分子平反。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立即恢复中断十一年的高考。
12月,许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者结婚生子或还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与在校生一起走进了考场,年龄相差达十几岁、几十岁,成为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空前绝后的一次高考。这个高考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在离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的宕渠县下辖的一个山村,在这样的一个八月盛夏的一个中午,瓦蓝瓦蓝的天空上不见一丝云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在田间地头忙活的农民。
二十五岁的农家女人杨召珍梳着两条长辫子,挺着个大肚子,脚上穿着一双土布鞋,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在打扫院坝里的卫生。她扫扫停停,不时将目光投到远处田里打谷子的陈建川身上。陈建川和村民一起在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
陈建川是杨召珍的家属(丈夫)。他们同年同月但不同日生。陈建川出生在月末,杨召珍出生在月初,彼此一米五的身高不相上下。陈建川方脸型,大眼睛,一年四季保持着不变的平头,他长得特别精神,随时脸上都挂着微笑。
他头上戴着顶破了边的草帽,上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衣服,下身穿着一条灰色的烂裤子。说是烂裤子,是因为裤子的左右膝盖上有两个口子,活像一双大眼睛,屁股上补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疤,而且还是补了一层又一层,腰间系着一根草绳当裤腰带。他赤着脚,扬起双手,一上一下地在拌桶里打谷子。他额头上的汗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用衣袖擦了一把脸。他有些累了,歇了片刻,又继续弯腰拿起谷子扬起来继续打。与陈建川分到一个组劳动的还有同村的陈建星、王丙全、贾柏燕、陈玉英、刘梅芳、张志行。
刘梅芳和张志行十七八岁,家在达州市,1974年高中毕业,他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到了陈建川所在的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和村民一起下地干农活。一年后,刘梅芳嫁给了当地唯一的赤脚医生陈三虎,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张志行除了劳动时间外,剩余的时间都用在看书上。他个子不高,有些瘦,他戴着一副眼镜。
贾柏燕的丈夫陈建江与陈建星是一奶同胞。他们的母亲张万青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丈夫在五年前生病去世后,就跟着陈建江家一起生活。
张万青一生生育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都分别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老大陈建军是村里的队长;老二陈建星是剃头匠,闲暇时候走村串户给乡里的人理发;老三陈建江是军人,也是张万青最为满足的地方;老四陈建英有点憨,缺根筋那种,二十出头的大姑娘,鼻涕还往衣服袖子上擦。为了将她打发远点,眼不见心不烦,家里托人把她嫁到了大山里。但陈建英有点福气,结婚没一年,丈夫久儿去当兵,成了军人,在部队上喂猪;老五陈建兰人聪明,嫁到邻乡。张万青一家,在村里也是条件最好的一户人家。因此,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张万青的孩子们年龄与陈建川相差不大。
田里干活的人,有的用镰刀割谷子,有的传把子,有的打谷子。陈玉英一直弯着腰割谷子,有些累了,直起身,伸了伸懒腰,又向四处张望着。她的目光停留在了远处的杨召珍身上,说:“陈长辈,你家快生了吧?”
陈建川一边打着谷子,一边笑着回答:“就这两天。”
“那就快了。”陈玉英感慨着,顺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也怀孕四个月了。
陈玉英的丈夫杨友林是宕渠县煤炭厂的工人,虽说有工资,但也不高。在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要按人头出工挣分的,因此,即便陈玉英怀孕后,本着多收入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她还是坚持出来挣工分。
贾柏燕也直起腰,用手捋了捋额前的刘海,说:“陈玉英,你也快生了吧?”
“我还早呢,你家都两个娃儿了,我这一个还揣在肚子里呢。”陈玉英说。
陈玉英不知道,贾柏燕的肚子里又怀上了,已经一个多月了。是陈建江六月份从部队回来休探亲假时怀上的。她前面已经生了两个姑娘,大的陈玲玉三岁,小的陈秀兰一岁,为了生一个儿子,所以怀上了第三胎。
陈玉英比陈建川还大一岁,她是村里结婚最晚的姑娘。
在她当姑娘时,给自己找对象定了一个目标,非工人不嫁。她认为找个工人,意味着旱涝保收。因此,从她十五六岁起,每年都有媒人说亲,但都没成,直到二十四岁那年,遇到了煤炭工人杨友林。
杨友林个子矮小,陈玉英高他一个脑袋,尽管个头悬殊大,但陈玉英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杨友林的父亲就是煤炭厂的工人,因为下井出了事故去世,他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当上了工人。
“揣在肚子里比没揣着强。”贾柏燕说到这,停留了一秒钟,又说:“我看,陈建川家这次要生个田边转(田边转是指男孩)。”
“都一样,儿子和丫头都一样。”陈建川说。
陈建川想到婆娘要生娃儿了,心头热热的。第一胎生的是个丫头,快三岁了。这一胎,他不知道会是丫头还是小子。但有个答案是肯定的,无论生啥,他都喜欢,他明确地告诉过他的婆娘。
自打杨召珍怀上第二胎后,常常问他喜欢儿子还是丫头,他就一直说无所谓,生啥养啥。就在昨晚睡觉时,她还在问:“陈建川,你说,这次我会生儿子,还是丫头?”
“不管生啥子,都是我们的娃儿,都一样带。”陈建川说的内心话。
“可我想有个儿子。你想,都是姑娘,以后她们嫁出去了,谁管我们,谁给我们养老?养个姑娘是贴钱的货,给别人家养的。”
“也不能这样想,要是我们的姑娘以后个个出息了,也不会比有个儿子差。你现在也别想那么多,这事谁也说不准。我已经知足了。凭我的家庭条件,能娶上你,这辈子没打光棍,已经是感恩戴德了。你也知道,我爸妈过世得早,我爸生病去世时,我才十二岁,他去世后,没有给我们兄弟留下丁点财产。为他治病,我们还借了不少钱,到他去世时,欠了100多元的债。我一下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因为我的妈妈是个莽子(傻子),家里啥事都不晓得。那时,我大弟陈建良才八岁,小弟陈建安才四岁。我是既当爹,又当妈,带着两个兄弟和妈妈艰苦度日。我妈妈去世时,我刚满十八岁。唯一的一个姐姐陈建芳也出嫁了,家境也困难,我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等于是三个孤儿。因为你,我这个家才撑起来了。你跟着我,也受了委屈,结婚后,还一起帮我还完了欠债。再说了,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还不知道形势啥变化呢,解放前,我爷爷积攒了不少钱,结果形势变了,那些钱成废纸了。”
陈建川一股脑儿说着自己的家史,从心底对杨召珍充满了感激。童年家庭的变故,使陈建川更加明白一个家对他的重要。世事无常,国家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谁也说不清楚。再说了,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现在不是听说又可以高考了吗?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很多人的无奈选择。他非常清楚,在农村,想成个家很难,特别是穷人,自己能成家,已是万幸了。
“我和我哥哥嫂子都觉得你老实,人好,心好,所以当时就同意了这门婚事。想想,跟你结婚时,你还是借陈建星的衣服穿的,这还不说,我跟着你,连一个多余饭碗都没有,三兄弟就三个碗和三双筷子。”杨召珍摸着肚子说。
“还得感谢杨德碧给咱们说的这门亲事。”陈建川说。
杨德碧是陈建川同村陈建忠的家属(婆娘),她的娘家与杨召珍的娘家是房子挨着房子,邻里关系走得非常近。看着陈建川二十出头还没对象,就把杨召珍介绍给了他。
杨德碧嫁到山东村七年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老大陈硕六岁,老二陈梅四岁。
“是啊,要不是她介绍,我还不认识你,说实话,我们相信杨德碧,毕竟你知我熟。你还记得吧,跟你结婚后,我才知道你们家连挑水的水桶都没有,还是将挑粪的桶洗来挑水吃;还是我把当姑娘时存的点私房钱拿来买的碗筷和水桶。水桶买回来后,陈建安高兴得满屋子跳,说终于有水桶了,不用吃用粪桶洗来挑的水了。”
“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陈建川从心底感到愧疚。
“现在比我刚嫁来那两年好多了,两个兄弟都逐渐长大成人,都在挣工分了,等他们以后结婚了就分家单独过。”杨召珍停了下,接着又说:“日子是过到哪算哪,一天天过下去的!”
陈建川想到这些,一丝温暖荡漾在心头。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快速地打着谷子,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一首川东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他唱道: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郎啰/挑起扁担郎郎采/咣采/上山岗吆后/啰喽喂……
陈建川的歌声迅速在田野里飘荡开来。大家看着他放声地歌唱着,也跟着唱了起来,田间顿时响起了一阵阵快乐的歌声。这歌声也传到杨召珍的耳边。杨召珍远远地望着干活的丈夫,会心地拿着扫帚走进屋子里。
几缕阳光从屋梁上直射进来,将原本黯淡的屋子照得透亮。墙壁上的蜘蛛拉着网在缓缓地一圈圈地挪动。地下的老鼠时不时地在屋子里窜来窜去。
杨召珍看到老鼠进进出出,像过大街一样,狠狠地拿着扫帚打老鼠。她笨重的身体哪里对付得了聪明狡猾的老鼠。往往是刚拿起扫帚,老鼠就迅速钻进洞里去了。
她恨透了老鼠。本来家里就没几颗粮食,老鼠总来糟蹋,自家几口人的口粮只能常年喝稀饭勉强维持。老鼠幸运地逃掉了。杨召珍放下了手里的扫帚,嘴里咕哝着:“打死你个死瘟伤。”
“妈妈,你打死啥子?”红琼从地坝里走进屋里问着。
“打死老鼠。”
“我帮你打它。”
“下次看到了,你再帮着打,现在时间不早了,妈妈去煮饭,你自己耍,不要乱跑哈。”杨召珍说着转身去灶屋里煮午饭了。
红琼又来到地坝里,她没有目的地走来走去,最后去了贾柏燕家。张万青用背篼背着陈秀兰,一边烧火煮饭,一边在给陈玲玉梳头发。陈玲玉梳的是丁丁头冲天炮,上面是用红绸布扎上的。
张万青看着红琼,说:“来,婆婆也给你把头发梳了。”
杨召珍坐在灶屋里的灶台前烧柴煮饭。她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挽柴火。灶台里红红的火焰,欢快地笑着。她在心里想,火在笑,家里是不是要来客人了。这年头,最好别来客,本来家里就穷,来个客人啥的,多少要加把米,现在粮食又紧张,一年到头就分那点粮食,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发展。你越是不愿意,越是担心,它就越会来临。杨召珍不喜欢来客人,突然间却听见了喊声:“幺妹、幺妹。”
她听出了声音,是她二姐杨召群。
杨召群虽然比杨召珍只大三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老大是一个女孩,已经七岁;老二也是女孩,已经四岁;老三还是女孩,一岁半了,现在肚子里又怀上了,已经两个月了,她还想生个儿子。孩子多,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岁月已在她的脸上过早地留下了衰老的痕迹。
杨召珍赶紧从灶屋里走出来。她看见二姐用背篼背着三女儿,手里还提着一个布袋子,便帮忙把娃儿从二姐背上接了下来。
杨召珍上下打量了一下杨召群,说:“二姐,你看你,衣服都穿成啥样了,也不洗洗,都看不见本来颜色了。”
“成天到晚忙不完,忙了地头忙家里,哪有时间,一天连脸都来不及洗一把。”
“撒泡尿的工夫就把脸洗了,有那么严重。”她瞧见二姐的脸上像花猫,好几处黑灰黏糊着,说:“姐姐,你去把脸洗一把吧。”
杨召群把手里的布袋子放在地上就去洗脸,还一边说:“女人啊,就是女人,家里家外操不完的心哟。”
说话间,杨召群已洗好脸了,她捡起地上的布袋子递给杨召珍,说:“今天逢场,我顺便过来看看,我们也没啥子好带的东西给你。”
杨召珍打开袋子,说:“来就来嘛,又带鸡蛋和挂面,你家的条件也不好,还要养三个孩子也不容易,以后别带了。再说,你现在肚子里也揣了一个,也需要营养的。”
“你就别担心我了,就这十个鸡蛋和一把挂面。姐姐家只有这个条件,多的还拿不出。”
“你给我们送吃的,二姐夫不说啥呀?”
“你姐夫让我拿来的,说幺妹家目前比较困难,加上又要生孩子了,总得让坐月的人吃好点,坐月不吃好,以后对身体不好。”
“姐夫真是个好人。”
“人是个善良人,就是不爱干农活,除了好那一口酒,还好到巴子沟水库钓团鱼。”
姊妹俩一边拉着家常,一边走向了灶屋。杨召群把娃儿抱在怀里,就坐在灶台前的小木板凳上烧火,还问:“兄弟呢?”
“在田里打谷子。”杨召珍一边回答,一边往锅里放米和红薯,还不忘用勺子在锅里搅拌了几下,以防粘锅底。
娃儿在杨召群的怀里不安分地晃来晃去。杨召群把娃儿放到地上,说:“王芳,去找红琼姐姐耍。”
“王芳长得真快,都能走路了,娃儿就像根小树苗儿,见风就长。”
“娃儿是越带越欢心,不像带个老人,越老越招人烦。”说到娃儿,杨召群的脸上荡漾着暖暖的幸福。女人的柔情好似只有在孩子身上体现。虽说她已生了三个孩子,但她从没感觉到累过、苦过。
也许女人是因为孩子而活着,也是因为孩子而逐渐成熟。孩子是她们的天,是她们的地,更是她们活着的动力。即便再苦再累,回家看到孩子的笑容,也是一种幸福,也算是苦中有乐。
杨召群接着又对在地上走动的王芳说:“去找红琼姐姐耍。”
“红琼!红琼!”杨召珍接连喊了两声,见无人回应,从灶屋走了出来,一边咕噜着:“这贱人跑哪去了?”
张万青给红琼梳好头发后,叫陈玲玉去外面喊她妈妈回家切(吃)饭。她俩走到半路上,遇到了一条小河,就停下来了。
小河沟里的水清澈见底,缓缓地流淌着,洁白光滑的鹅卵石躺在水里,河水里的浮漂被小鱼拉得上下飞舞,小鱼时不时地吐出小水泡泡,可爱极了。
红琼和陈玲玉看着河沟里的鱼儿,心里痒痒,双双光着脚丫站在小河边。她们望着河里那些欢快的鱼儿,高兴地嚷着:“看,那哈(那里),那哈!”
陈玲玉是第一个下河的。她甚至没有卷起自己的裤脚,就下河了。红琼见她下河,也跟着下去。水淹到了她们的膝盖,她们走在河水里,把两只小手轻柔地埋进了水里。她们见哪里有鱼,就将手伸到哪里,有时看见小鱼在手掌里了,但一捧起来,小鱼又迅速溜掉了。
小鱼儿看着她们欢快地游啊游。她们的到来似乎给鱼儿带来了更多的欢乐。鱼儿一会游到她们的脚边,用嘴顶顶她们的小脚,一会又迅速地逃离了。
陈玲玉见红琼好几次鱼儿到手里了没抓住,说:“我来我来!”
红琼站在陈玲玉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陈玲玉逮鱼。陈玲玉每次都小心翼翼的,生怕鱼儿被吓跑了。鱼儿好像读懂了她们的心思,每次都主动进入她们的手掌,但在关键时刻,都能顺利逃离。
好几个来回都没逮住一条鱼,她们放弃了,开始在水里跳起来,一跳就能溅起好多水花。
水是温柔的,站在水里也是舒服的。两个小娃儿在水的世界里畅快地闹着、嬉笑着。她们一会跳水,一会相互泼水。水在娃儿的世界里是最好玩的玩具。娃儿在水的世界里给水增添了不少生机。
太阳照在两个娃儿身上,水面的倒影是一幅生动的画卷,人与自然的融合是那般完美。清澈的水,波光粼粼,单纯可爱的娃儿,扬着单纯的笑脸,真是一幅天人合一的景象。
她们在水里无拘无束地闹着,彼此早已成了落汤鸡。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傻乎乎地哈哈大笑起来。陈玲玉把婆婆交代的事情忘了十万八千里……
杨召珍头顶烈日,拖着笨重的身子,沿着屋前屋后找了一圈没见着红琼,就往小河沟走去。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少娃儿爱去的地方。
当她看见红琼时,红琼和陈玲玉都弯着腰在玩水,她接连喊了几声,红琼都没听见,还是陈玲玉最先听见的。
陈玲玉站直身子,用小手擦了下额头的汗水,说:“你妈妈来了!”
红琼听见说妈妈来了,吓得赶紧从水里钻了出来。杨召珍见红琼整个衣服都是湿的,气不打一处来,走上前去,扬起手要给她一个耳光时,突然,感到腰胀痛得钻心地疼,扬起的手放了下来,豆大的汗水像泉水一般汹涌而出,“尿”顺着裤脚流了下来。她有过生孩子的经验,知道这不是尿,一定是羊水破了。她有些控制不住了,只感觉下身的水在不停地流出。
红琼看着妈妈,妈妈的脸变得扭曲了。她没见过妈妈这样,赶紧拉着妈妈的手,害怕地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妈妈……”
杨召珍强忍着痛,说:“快去喊你爸爸,喊你爸爸。”
红琼一路像汽车抛锚似的发疯地跑着,一边大声地喊着:“爸爸……爸爸……”
“我也去!”陈玲玉在后面追着。
陈建川在专心致志地打着谷子,红琼的喊声没能进入他的耳中,还是贾柏燕听见了,她说:“陈建川,你家娃儿在喊你!”
陈建川放下手中打完谷子的稻草,顺着喊声望去,看见了远处两个幼小的身影在一前一后地跑着,一个喊着爸爸。
陈建川大声喊道:“红琼,红琼,你跑啥子?”
红琼没有听见爸爸的声音,只是一个劲地跑啊,喊啊,突然,一个跟斗栽了下去,她甚至不知道疼,爬了起来,继续跑着。
陈建川还站在原地不动。贾柏燕又说:“你去瞄看,究竟是啥事,我家玲玉也跟着跑啥?”
接着陈玉英也说:“陈长辈,是不是你家快生了?”
陈建川说:“我先回去看看。”
“你赶紧回吧,这也马上收工了,得回家切午饭了。”王丙全说。
红琼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爸爸。当她跑到陈建川干活的田边时,陈建川已从田里走了出来。
红琼焦急地哭着说:“妈妈……妈妈……”
杨召珍一只手搂着肚子,一只手插在腰间,艰难地迈着步子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她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最难受的还是总感觉有尿要流出来。
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到家门口。她喊着:“二姐……二姐……二姐……”
杨召群立即从灶屋里出来。
杨召珍满头大汗,紧咬牙关,整个脸型因为难受而变得扭曲。
“二姐……二姐……我可能快生了……”杨召珍有气无力地说着。
“快,快,上床躺下!”杨召群扶着杨召珍进屋上床。
杨召珍说:“快去喊她爸,让他喊琬幺婆来。”
“我回来了,老杨!”陈建川对杨召珍说,“我马上就去喊接生婆来。”
陈建川憋着一股劲,一口气跑到了琬幺婆家。接待他的是琬幺婆的儿子贾富贵。他说:“我妈出诊去了,你得等等,估计快回来了!”
“大概啥时回来,兄弟,我屋头快生了!”陈建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由于过分激动,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你先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喝一口。”
陈建川哪里坐得下去。此时,他忐忑不安地走来走去。接着又问:“你妈妈去哪儿了,我去找找她。”
“又是哪家找我?”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语调里中气十足。她就是琬幺婆,她正提着一个木箱子回来了,木箱子上有个红色的十字。
琬幺婆年过六十,长得慈眉善目,是当地专门接生的婆婆,非常有口碑,乡里乡外都找她接生。无论是哪家生孩子,基本上都是她接生。陈建川兄弟三人当初也是她接生的。
琬幺婆看着陈建川,问:“建川,啥事?是不是你婆娘又要生了?”
四川人说话有个习惯,即便知道是啥事了,也喜欢重复问。就如明明知道你吃饭了,还问,吃饭了吗?
还没等陈建川回答,贾富贵说:“妈,他等你好一哈了。”
琬幺婆说:“哦,那赶紧去!”
此时的杨召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感到身上难受。她一边紧紧咬住嘴唇,一边用手按住腰。杨召群给她把裤子已经脱掉了。
琬幺婆到陈建川家后,立即吩咐他赶紧烧开水,将剪子消毒。
一切准备就绪后,琬幺婆让陈建川出去,不要待在生孩子的屋里。在农村有个习俗,家里的男人不能看女人生孩子,看了,男人要倒霉的!因为生孩子要出血,男人不能见女人的血!
陈建川只能待在外面,但他听见屋子里杨召珍的喊叫声,一点也不安宁。
屋子里的琬幺婆给杨召珍摆正姿势待产。杨召珍尽管生过孩子,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些不知所措。琬幺婆一面给她摆姿势,一面给她讲怎样吸气。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琬幺婆看了看她的子宫,说:“宫口已经张开了近十厘米,马上就要生了,现在能看见孩子头了。放松,放松,吸气吐气,好好配合我,一下就生了。”
杨召珍忍着疼痛,大滴大滴汗水不停地向外渗透出来。
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是无法体会的,生过孩子的女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生孩子的那种疼是不好形容的,腰胀痛胀痛,又感觉像气体一样,一圈绕着一圈。
杨召珍的双手又紧紧地抓住床架,她一使劲,将所有的力量释放了出来,在那一刻,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她才感到如释重负。
琬幺婆提着孩子,轻轻地拍了一下,孩子哭了两声,就睁着一双小眼睛东张西望,好像外面的世界比娘肚子里要精彩得多似的。她红润的小脸蛋,满头黑发盖过耳朵,头发湿湿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攥着。
琬幺婆将孩子清理干净后,放在秤上称了称,说:“孩子体重六斤。”
孩子顺利生产出来了,杨召珍感到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迫不及待地问:“是个啥子?”
琬幺婆说:“一个聪明的姑娘!”随即放在了她身边。
杨召珍有些失望,说:“又是一个菜角豆!”
琬幺婆说:“菜角豆怎么了,你看这孩子多聪明,看那双眼睛就知道,你们以后还靠享她福呢!”
陈建川听见了屋里一声婴儿的清脆哭声,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知道,生孩子就是他婆娘过鬼门关。在村里,有好几个女人因为生孩子,难产死了,大人小孩都没了。自己婆娘能顺利生产就是万幸。他赶紧走进了屋里,去看了看杨召珍以及躺在她身边的孩子。
琬幺婆接生完后,杨召群赶紧将煮好的醪糟鸡蛋端了上来,摆在了饭桌上,说:“琬幺婆,你切点东西!”
接着,杨召群又给杨召珍端了一碗过去。
杨召群看着孩子,说:“这孩子多机灵,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陈建川看着孩子,说:“老杨,赶紧切吧!”
“本来想生个儿子,嗨,这就是命。”杨召珍说。
陈建川说:“儿女都一样!”
杨召珍说:“谁说儿女都一样,女儿养大就嫁出去,没个儿子,以后养老都成问题!”
杨召群说:“妹子,你赶紧切,生啥子哪个晓得,肚子里的东西,只能见天才晓得。”
琬幺婆说:“放宽心,好好把孩子养好,千万别乱想。”
杨召珍点了点头,随即又叹了口气,然后埋着脑袋无声地吃着醪糟鸡蛋。
杨召珍对于这个小不点到来的态度被琬幺婆看在眼里,从她内心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她不知道,这个让她亲手接生过的女孩会在这个家庭面临什么命运?从她以往经历过的事件中,往往不讨人喜欢的女孩,不是被父母遗弃,就是换了别人家的男孩。想到这,琬幺婆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脑袋。
陈建川递给琬幺婆一个红包,是接生费用。琬幺婆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药箱,挎在肩上,准备回家。
走时,她又看了看孩子,孩子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她,表情好似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