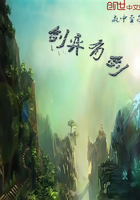“我家公子的画艺不错吧。”小子踮脚把怀里覆了布的笼子放在我怀里,里面有咕咕声响起,小子隔着布不舍的摸了摸笼子,“这是公子养的鸽子,公子说了,襄城路远,凭此寄言语。”
我再次看了看墙上的画,捏着笼子的手紧了紧,我抱着鸽子,心情沉重复杂地往外走去。
“不过你要是饿了,可千万别炖了它们。”小子在关门那刻,伸出个圆圆的脑袋恳求我。
我点头,无声离去。
夜寒轻透罗裳,凝露染白茶心。襄城条件艰苦,阿言走得匆忙,又快要入冬,不知带足了冬衣否。
我不曾掌灯,就着月色,铺开纸张,磨好墨水,笔在手中却也久久不能下笔。总嫌纸薄,人情怎盛?反反复复如此几次,都不知写什么给阿言。
难道问他有无人温衣送水,教他小心身体吗?我终究与他不过是朋友而已,再也不能逾越过多。
怔仲间,笔尖墨汁落在纸上,染了好大一块黑点,我揉乱纸张,再也无心写下去,胡乱睡下。
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单衣。
我着了一袭素白色的织锦,早起也懒得精心打理。
我蹲在一簇五颜六色且品种名贵而不知其名的菊花前。
抬手轻轻掐住一株开得雍容的瑶台玉凤菊,层层相绕的花瓣上有露水凝成珍珠的模样,煞是好看。日色虽然正盛,凉气依然凝结。我呵了一口气,如雾蒙蒙洒在近前洁白的花上,如我在建州的王涂山山顶见过的雪景一样。
稀薄的阳光照耀在山顶的雪峰,水汽聚集而成的雾,浮在青白的山头。
我再长长地呵了一口气,未束的发丝因我身体前倾从后背滑落至胸前的花瓣上。
突有一指暖意携了我散落的长发从额前缓缓带至我耳后,“若是你喜欢这些菊花,叫人搬进屋里,随便你怎么欣赏,但不能不顾清寒,在这里蹲着。”
我折了手边的墨菊,飞速扑过去按住他的肩头,一朵朱紫色菊花就熠熠生辉地在他耳上挂着,我忍着笑,正色道,“这情形倒是让我想起一句诗歌来。”
他也不恼,任由我胡闹着,整理了一下被我揉皱的衣裳,并不准备取下他耳上的花。
他今日又穿了一身朱紫色的便服,与那朵花倒是相互辉映,格外相称。
但他铮铮铁骨的男儿被我饰以鲜花拿他来取笑逗乐,他也能忍,我倒是觉得他对于我向来格外地宽容。
我拉长声音,“问郎花好奴颜好?郎道不如花窈窕。”
他忽而笑了,犹如寒意薄缭的雪里绽放红梅般令人惊艳,我很少见他笑得如此温柔迷人……
他摘下耳边的花放在他掌心,指腹柔柔地抚摸着花瓣,“揉碎花打人的事我自是不会做,但你这比喻我很是受用。”他……他的意思是以花比他他很开心?
他见我一幅懵懂的样子,又使出刚刚那个迷死人的笑容,“不懂我受用的地方,没关系。”
我抬眸望了他一眼,默默把那首诗歌想了一遍,突然面红起来,这诗是讲新婚夫妻恩爱的。
他低低轻喃,“昨夜海棠初着雨……”我捂住耳朵,提裙疾步跑回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