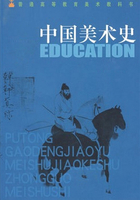“你还好吗?”
这个是凯莉——就是我老婆——最近一直在问我的问题。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种,比如问我昨晚是不是喝了太多酒,或者问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脸书上了。那样问,就只是轻轻推我一把,提醒我最近做的决定可能不太好。不,这次她问的时候,声音里带着担心。就像她是真的在担心我的情绪健康。
“好极了。”我告诉她。
她站在我办公室门边,紧盯住我,看我敢不敢真的坚持这个说法。
她不用解释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她感觉这么不对,因为实在显而易见。大中午,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电脑关了,没在干活,盯着我的《杜利特》唱片,就是我几天前从“轻率冒险”买的那张。这张碟片我当然还没听过,因为我们没有唱片机。但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就像鳏夫到处带着他亡妻的照片。
我知道我心里难过,但我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希望背后的原因没那么直白明显。我已经四十过半了,人生不像二十二岁那样,不再那么简单,不能自我放纵。地球再也不围着我转了。但谁不会最终明白这一点呢?你结了婚,有了个孩子——或者很多孩子——你的日子突然就井井有条了。你不能对你老婆说:“让我们赖一天床,把《教父》全系列都看掉。”肯定不能在周二做这种事,在周二狂看你早就看了上千遍的电影真是最不负责任(因此也是最好玩)的事了。
我不希望背后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成了最糟糕的老套人物。中年危机?我真的这么简单吗?变老了,我就成了这么好猜的伤心人?我简直像杰克逊·布朗歌里的人物。我为什么不直接买辆跑车,找个情妇?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郁闷的不是自己老了。我挺喜欢变老的,这样人们就不会对你有太高要求。没人会因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四十五岁老家伙觉得累了,在晚上十点离开派对而不高兴。没人会取笑在泳池边穿防晒服、不想硬把肚腩吸回来的四十五岁老家伙。没人会对穿化纤保龄球服、戴及膝钱包链的四十五岁老家伙多看两眼,他这身行头自从《全职浪子》上映以来就再也没有酷过。对中年男人的要求真挺低的,我很高兴。
但有些东西丢了,我没法迈过这个坎。丢的不是我的青春。
我遇见凯莉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芝加哥。我们都在第二城市喜剧剧院工作,在那里,传奇喜剧明星开始他们的征程,比如约翰·贝鲁西、比尔·莫瑞和斯蒂芬·科尔伯。我在售票处工作,她是主持人——工作内容主要是保证每个观众都能有个座。我们拿的都是最低工资,没有医保,但我们整晚熬夜,和才华横溢的人喝酒,里面不少人以后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有时候我们直接就在剧院里睡觉,在吉尔达·瑞德尔和克里斯·法利的巨大黑白照片下紧紧地窝在一起。
恋爱四年后,我向她求了婚。订婚戒指是葡萄味的棒棒糖戒指,因为我只买得起这个。但这还是足以让她喜极而泣。我们决定离开芝加哥,试着去一个新城市,因为我们所有朋友都是这么做的。没人会永远留在芝加哥。它就像大学一样——你在这里学会一切需要的东西,好去另一个城市,做个成年人。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住遍了全国每个时区——住过洛杉矶,我们都尝试做编剧,失败了;住过犹他州的盐湖城,她为圣丹斯电影节工作,我是家庭主夫;住过佛罗里达州的好几个城市,我们当时觉得只要能一直保持温暖就够了;住过加州的索诺玛,我们当时觉得只要能喝价格贵的葡萄酒喝到醉就够了。我们一直漂泊,不断寻找下一站,停留一阵,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再次启程。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芝加哥,租了个小小的二楼公寓,只有一千两百平方英尺,朝北。我们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名叫查理,精力充沛,有着美丽的金发。我们还有无止境的账单。我们日子过得很快,快得让人发昏,好像永远找不到足够时间把一切该做的事做完。要陪孩子和朋友玩,要收拾买来的杂物,要叠衣服,要填学前班申请表,要清空存款账户,因为我们完全忘了交过期的车款,还要提醒儿子:“不,不,你不能把小船放在火鸡肉上!”或者:“你绝对不能光着身子浑身乳液地跑出去!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外星人!”
当我听见自己抱怨时,我想给自己哼哼唧唧的脸上来一拳。我并不是在三个工作之间疲于奔命好图个糊口,也不是如果漏了一期按揭没还就会无家可归,也没试过和保险公司吵架,说我孩子得了癌症却得不到应得的治疗。我愤怒,是因为我的时间再也不是自己的了,我的日子都花在保证我们有电可用,保证我们记得付电费单,保证我儿子不要看太多电视,保证我妻子觉得我确实在关注她而不是边点头边查电邮。我在生活和工作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即使这意味着我一般直到晚上十点才能挤出一点时间留给自己,而且到了那时我只想爬上床,看《宋飞正传》重播看到睡着。
我的人生挺不错,甚至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我最近很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因为老友的妻子被诊断出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到了脑部,最终扩散到了全身。这混蛋癌症终于还是胜过了她,医生让她回家,说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她只剩几个月的命,可能更短。所以我们开车去向她道别。站在临死的她床边——真的是临死的她床边,她真的会死在这张床上,可能就在我们站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不知该说什么话的时候——感觉很不真实。我探望过病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已经放弃了抗争,没有一个人只是单纯在等死。尤其是这个人岁数和你差不多大,你关于这人的最后记忆是去年夏天,你请她和她丈夫来吃晚饭,你们喝红酒喝得太多,酩酊大醉,聊备孕的话题(她和凯莉是孕友),拿过去的事开玩笑,聊过去的时光过得多快,取而代之的是大人应承担的责任,这真不公平,不过没事,把音乐开大点,再开一瓶酒。而现在她躺在这里,红肿的双眼,紧紧闭着,她的嘴大张,就像在模仿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她只吊着最后这么一点气,以至于看她胸口起起伏伏都像是奇迹。
我们待了一个小时,开车回家时,凯莉和我什么都没说。我们深受震撼。如果我们需要人提醒,生命珍贵而短暂,每分每秒都值得感激,那这提醒得太到位了。我们对自己发誓,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有多幸运,有多少东西我们应该感激。
只过了几天,这种感觉就消退了,我们又开始抱怨。是啊,是啊,我们的朋友得了癌症。生命珍贵,我们懂了。但今天是垃圾回收日,我还没把可回收垃圾分出来,而且查理该洗澡了,凯莉不知怎么地认为这次该轮到我来洗,这简直是一派胡言。而且我明天早上有个故事截稿,还有几十封电邮要回,我们的信用评分又狂跌了,因为有人(我不是在指责谁)忘了付有线电视费,而且我好几个小时都没看脸书了,上帝,我甚至没时间听听我自己在想什么!
当我看着凯莉和我的旧照片,看着二十多岁的我们,我惊奇不已。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年轻,不是因为当时保持苗条多么轻松,而且是因为我们看上去多么无忧无虑。我们的日子曾经多简单,即使我们当时并没意识到这点。我们曾经这么轻松,身上没有任何负担。在那些照片里,我们表情放松,像没有繁重工作、责任和承诺的人(只有对彼此的承诺)。穷困不好玩,但如果你穷的时候才二十三岁,你知道山穷水尽之时,你还可以打电话给父母,求他们帮你付一下房租,那好吧,穷肯定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
只要我们想,就可以随时消失。我们可以躲上几个星期,把身上那一点点责任都丢开,因为我们要“寻找自我”,或者做和这同样重要的事,把周末花在听新的Beck乐队的专辑上——我是说认认真真地听,直到把每一首歌都听得滚瓜烂熟,可以不假思索地跟着唱。
凯莉和我在三十岁时结了婚——我父亲证的婚,他是个牧师——然后生活如常进行。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买房子,或者做一份工作超过一年,或者找到一个熟悉以后再也不想抛弃的城市。还会有孩子。我们想要孩子,当然啦,不过这是以后的事。这总是以后的事,处在差不多要到来但肯定离现在还很远的将来。等我们有了孩子,噢哥们儿,那肯定棒极了。我们不会做那种家长,只想培养小小的、粉嫩版本的自己。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孩子会很酷,单纯又开心,因为我们已经足够成熟了,不会再掉进我们父母二十多岁时掉过的坑里。我们会和他们一起看《星球大战》(他们比我们还爱《星球大战》),我们还会把所有超酷的音乐和流行文化都教给他们,他们绝对会很感激的。但我们也会管着他们。如果他们想要一个中性牛奶饭店乐队飞行留声机的文身,我们会说绝对不行,除非你到了十八岁。不好意思,当了次坏人,但家长就得这么做。
我们直到四十岁才设法怀上了孩子。就像在动作电影里面,主角滑进正在关闭的金属或石头门里一样,刚刚好钻过去,墙壁差点就砸到了他的腿上。我们试着自然怀孕,然后试了生育治疗,差点就放弃了。不过有天晚上,我们喝了太多伏特加,用老方法怀上了。
查理出生后,生活变化得很快。原先也一直在变,一般都只是稍微有点小改变,直到有一天我醒来,看着镜中的自己,难以置信我看上去有多疲惫。不是衰老,而是疲惫。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落得这么个境地,在我的办公室坐立不安,感觉脑子已经死了,莫名其妙地难过,抓着一张定价虚高的小妖精乐队唱片,仿佛它是我的救生筏。
我正恍惚间,查理走进房间,把《杜利特》从我手里拿走。他坐在地上,细细地看它。他把唱片从封套里拿出来,手指抹过黑胶表面,像要唤醒平板电脑那样。
“这怎么用?”他问。
“它不会自己响的,”我解释道,“要用一个叫唱片机的东西才能播放。”
他看着我:“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机器,上面有个盘子不断旋转,你把唱片放在转盘上,有一个小机械臂上面装着一根针,你把针落到唱片上,音乐就播出来了。”
他做了个鬼脸。他整张脸都皱起来了。三岁男孩很少做这样的表情,除非被逼着吃蔬菜,或者在浑身泥巴的快乐时刻被逼着去洗澡。但我向他解释唱片机的工作原理,就足以让他皱眉了。
他的注意力又转到《杜利特》唱片的封面上。“这猴子是谁?”他认真地问。
“我不知道,就是随便一只猴子吧,反正它也不在乐队里。”
“乐队里有谁?”
“有布莱克·弗朗西斯和金姆·迪尔。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的乐队叫小妖精乐队,爸爸以前超爱他们。”
“你现在不爱他们了?”查理问。
好吧,我的小查理,你刚刚可是问了个特别不合时宜的问题。我当然还爱他们。我以前听他们的歌就像那是我的工作,就像我能靠这个赚钱,就这么坐在黑屋子里,脑袋上顶着耳机,听他们的歌,直到它们已经严丝合缝地融合进了我的记忆中。我会跳进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的车里,只因为一个模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认识的人或认识的人认识的人可能有办法帮我们搞到小妖精乐队演出的票。
但到我这个年龄,对摇滚表演的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几个星期前,一个老朋友——我年轻的时候和他看了好多场小妖精乐队的表演——说他有票给我,是小妖精乐队重聚表演,在芝加哥。我上一场小妖精乐队表演就是和他一起看的,是几年前在底特律那场。当时的体验乏善可陈。小妖精乐队音乐会,二〇一一年,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都有些奇怪。一方面,你听到的音乐里天然带着无法无天的灵魂。可是,你回头一看,发现观众都是一大群四十多岁的哥们儿,和你一样,已经像布莱克·弗朗西斯那样,胸前乳头胖得凸了,人生从今往后只剩下坡路能走。那股想要毁灭一切的激情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你们纷纷觉得“我得趁他们唱慢歌的时候坐下来”。
即使如此,我也不想推掉又一次看表演的机会。如果我这次说了不,那就有着重大的意义。就像你发现你已经几个月没有和老婆做爱,你们俩都觉得没什么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拒绝这张票,理由有很多。我有工作压着——好几个访谈,今天内至少要把录音转写下来——而且凯莉已经和其他妈妈朋友有了安排,她有权出门去。而且,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能找个人来看孩子,可是这就意味着我要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我们的友情基础基本上只限于他那个年龄达标、可以看小孩的女儿,这一切实在是太麻烦又讨厌了。
当晚迟些时候,我把查理哄睡了,他手里还抓着小妖精乐队的唱片,可能他明白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背后的原因。他对那些我们不愿意给他仔细解释答案的谜题,态度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他的施皮茨爷爷去了哪里,以及人死了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在把他哄上床、给他读杂耍小狗和晚间厨房的故事的时候,我都没告诉他,我本来可以去看小妖精乐队表演的。我不想让他难过。这不是什么悲剧。这是好事,是幸运的事。在两个选项里,我选了唯一值得选的那个。但你还是会觉得怅然若失。
他不停问问题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记得最清楚的那场小妖精乐队表演。我脑海里的记忆巨细靡遗,就像一个尤其精彩的梦。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在芝加哥的里维埃拉剧院。我去看表演的时候,嗑药上了头(我没和他说这个),银行账户里只有两美元,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或者能不能)回到家。我没法告诉你当时表演了什么曲目——我很确定他们表演了我喜欢的所有曲子,只是我没有仔细记下来——但我很清楚,我少有这样的时候,充满活力、兴奋异常、满心感激。
查理在听故事的时候打了个哈欠,问:“那里有机器人吗?”
“有啊,”我让了一步,“有机器人。”
“他们的手会射出激光吗?”
“绝对能。”我说。因为在我记忆里,他们也和这差不多了。然后我亲了亲他脑袋,走到客厅,在那里和我老婆一起喝了瓶红酒,同时看《要留还是要卖》[18]的重播。因为我是个该死的成年人。
第二天,我开着我们的本田CR-V驶过湖畔街。我这一趟车开得很有黑帮范,从金边装饰、暗色车窗、丝绒座椅、三十寸镀铬轮圈到特制的链条方向盘,该有的都有了。不对,其实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它就是辆普通的本田CR-V,后备箱够大,能放得下手推车。但这里面确实有一样东西,是我和凯莉在一起的二十年里,因为我们偶尔有工作所以到最近才买得起的:卫星广播。
“接下来一小时,我们请来了威豹乐队、柯瑞·哈特以及大家都最爱的霍尔与奥特兹二重唱组合。”
如果凯莉是最后一个用车的人,广播都会像这样被调到八十年代频道。这个小时的怀旧节目由阿伦·亨特主持,他是原来在MTV工作的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之一。但当然啦,每一个听八十年代主题卫星电台节目的人都不需要别人告诉他阿伦·亨特到底是谁。这个男人(至少对我而言)——虽然是在电视机里——参与了我在八十年代经历的几乎所有性行为。他还在说话呢!他一直在背景里,干巴巴地介绍施潘道芭蕾合唱团的视频。
“接下来有些邦·乔维的歌,”他说,“实在是,这把我带回了过去。”
是《祈祷度日》。我没有立刻换台,一般听到邦·乔维的歌,我会直接转台。
我让那首歌放了下去。我听这首歌,真真正正地去听它,把里面每一句关于工人阶级年轻人和他们的破工作的陈词滥调听了进去。甚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就觉得它太刻意、太自以为是。我不相信歌里托米和吉娜的困境,就像我不相信莱昂内尔·里奇能在天花板上跳舞。
所以我为什么要在意?我为什么这么了解《祈祷度日》?我明明可以直接……
噢,对了,是海瑟·G。
海瑟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但在她成为我女朋友前,我就在高中乐团的另一边,有点走火入魔地盯着她看。她吹的是单簧管,我吹的是长号。光是这点,我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长号手在历史上一般是追不到女孩的。)更糟的是,她还是啦啦队长,会在来排练的时候穿着啦啦队的小裙子。我第一次想靠音乐给她留下印象时——我也只能靠这招追女孩子了,我体育不好,也没有迷人的下巴——结果简直是个灾难。我主动提出送她去学校,开一辆普利茅斯勇士,车里唯一的亮点就是磁带播放器。我把粘手指乐队的磁带塞了进去,我以为这就能显示出我确实有那么点性感又危险,即使我的车后座上躺着一个长号盒。我知道《婊子》里每一句歌词,可以咆哮着跟唱,我觉得这就能显出我的坏男孩气。
但可惜的是,这趟车时间太短,磁带播的是《死花》,这首歌就没这么强的威胁感了。
“你喜欢乡村音乐?”她问我,困惑地微笑着。
“不是乡村,”我抗议道,“是滚石。”
她又听了几秒。贾格尔如弦乐般慢吞吞的歌声没怎么帮上我忙。
“不,绝对是乡村音乐。”她一锤定音。
对于住在一九八五年南芝加哥郊区的少女来说,没什么能比乡村音乐更不性感了。她喜欢的是杜兰杜兰乐队、警察乐队和邦·乔维。尤其是邦·乔维。每个在她小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最爱哪个艺术家,就是那位真正理解她痛苦内心的摇滚乐手,她幻想的情人,琼·邦·乔维。
我得向她证明,我们在音乐上是相通的。我受不了邦·乔维和他那种毫无说服力的“我是个牛仔”的装腔作势。但如果这意味着我和海瑟之间能有机会,我愿意跟着格利高里的圣歌弹空气吉他。所以我买了张《难以捉摸》。我不是从平时的渠道弄到的专辑。我去的地方没人愿意去,因为那附近的灌木丛里死过一个女孩。
我买下专辑,带到学校,随意放在我打开的长号盒里,去参加排练,等着海瑟发现它。当然,她发现了。
“这专辑实在太棒了,对吧。”她说,抓着唱片套,好像抓着爱人的胯骨,好爬到他身上去。“你最喜欢哪首歌?”
“《社会疾病》。”我说。我挑这首,是因为它不热门。如果我在唱片店花的那些时间教会了我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真正的粉丝爱的都不是热门歌,他们爱那些还没被路人嚼烂的曲子。
她看上去很受我触动。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她正和我四目相对。
我们约好晚点再聚,听几首歌,好好聊聊邦·乔维这哥们儿。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写在了专辑封面上。我希望这能让她意识到我有多认真。我不是只把她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那可能会丢或者被扔掉。我把她的号码像刺青一样留在我最爱的专辑封面上,让她成了这唱片套的一部分,这张专辑,我每天晚上都盯着看才能入睡,嘴里哼着《永不道别》之类的歌。我会看着她的号码,心里想:“没错,这是另一个漂泊的灵魂,她爱乔维,就像我爱乔维一样深。”
这张专辑,我们开始约会的时候,我留着;她甩了我,让我心碎的时候,我留着;我把它带去了大学,在芝加哥搬的头几回家都带着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天知道我根本就不听这专辑。但上面写着她的电话号码,感觉太私密了,不能扔掉,也不能卖。我猜我最后还是把它扔开了,和我手上每张专辑一样。但天啊,我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
再一次……看见它……
就在车里,开车驶过湖边短路,听着《祈祷度日》,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突然就清楚意识到自己该干什么。我得找到这张专辑。不是随便一张,就是那一张专辑。上面写着海瑟电话的那张。就是我曾经拥有的那张,对我有重大意义的那张,它就是我走向成年的某种仪式。
我前往南边的郊区,去“唱片交换”。我十五年没去那家店了。我不知道海瑟那张专辑还在不在那里,但从那里开始找最符合逻辑。
为什么要光找一张专辑呢?为什么不全给找回来?它不是那些我根本认不出来的重新发行版本,就像我副座上那张《杜利特》。它看上去像是以前对我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但它只是个复制品。它虽然音质比较好——高音甜,低音劲——却不意味着它就更好。
我想要我的唱片,我拥有过的唱片,我原封不动的老唱片。我想要它们回来。
全部,至少是我能找到的全部。
Questlove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