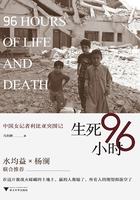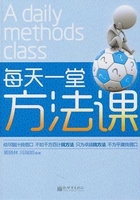沈佳觅小心翼翼提醒官家表态。
没想到官家突然间哈哈大笑:“我还在想,你这话是否真心,不过见你如此焦急,又这番打扮,是情窦初开了?我就说嘛,白相公一表人才,哪有姑娘不会动心。既然你都开口求我了,那我就承你的情。但是,白相公是否承情,我可就做不了主了。”
其实官家的想法又有谁人得知,此举也是正中下怀罢了。
“多谢官家!只要我今晚能亲口向白相公致歉就好。”沈佳觅嘴上回得乖巧,心里却想,只要我今晚见到他,就不会让他离开。
随后,官家就命人准备了一艘游湖的小船,船内如何陈设,一律听从沈佳觅的安排。并且差人跟白相公说,太子想泛舟游湖摘百草,请白相公一同去。
官家盘算着,谁让太子去筹备伏案司了,反正太子也不是第一次坑他了,再怎么样,白相公也不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沈佳觅选了一艘小船,船上灶房一间,下房一间,货房一间,厢房一间,还有随行的八个宫女。如此,她既能一整晚看住白相公,也不怕白相公真对她做些什么。
沈佳觅烧得厉害,怕风寒传人,带了面纱,只坐在船头吩咐宫女们做事,一动不动。若不是她偶尔出声,宫女们真以为她已经睡过去了。
天将要黑了,白相公还没来。人受了风寒本就疲乏,沈佳觅眼皮快撑不住了。好有个宫女一声尖叫,让她清醒了许多。
白相公来了。
沈佳觅起身拍拍尘土,抬头一步远便是白相公,于是行礼:“白相公万福。”
白相公见此,还礼问到:“是沈家姑娘?”
“正是。”沈佳觅装作将要提问,就要上前一步。
船板早让丫鬟们洒了水,就是为了佯装摔倒,正好,此刻就能派上用场。
“啊——”不想,白相公从容地往左边踏了一步,沈佳觅结结实实摔了一跤,脑子也像被人砸了一样,似乎有东西在里面晃荡;再加上手脚无力,连爬起来也十分艰难。只要她双手发力,头就更痛了。
白相公见此,始终没有去扶,反而质问:“近日未曾下雨,船面怎会湿滑,沈家姑娘不妨与我说说?”
沈佳觅此时听不进话,一心想着要赶快爬起来,不然,今晚的任务定会失败。想到这儿,沈佳觅一鼓作气,忍着剧痛,硬是撑着船面站了起来。但是,还没站稳就重重地摔了下去。
这一次白相公出手了,可惜,沈佳觅已经不省人事。
“浑身发烫,手脚无力,风寒有些时日了。”白相公伸手轻轻探了她的额头,很快给出结论,于是把她抱去厢房。
沈佳觅意识混沌,嘴里一直念着“好热……好热”。面纱不能再带了,白相公随手摘下,一时间有些恍惚。
喃喃说:“在绝味楼时,就觉得你似曾相识。”
为首的大宫女慌忙进来,问道:“白相公万福!觅姑娘这是怎么了?”
白相公吩咐她们灭了熏香,撤掉晚膳,开窗散味;还要用凉水给沈佳觅擦洗身子。
大宫女难办,这熏香刚刚点上,一桌子美味佳肴都是沈佳觅钦点的。
随后,只见他叫了艘小渔船走了,一时没了主张,但沈佳觅昏迷不醒,只好先照他的吩咐行事。
凉水擦洗确实有点效果,半个时辰后,沈佳觅身上不那么烫了,人也清醒了一些。恍惚间看见宫女们忙碌的身影,突然想起方才明明见过白相公,急忙询问宫女。
那宫女心里也急:“白相公方才划船走了。”
“什么?”沈佳觅一听,这还了得!直接掀了被子下床,一口气跑出门,口口声声说着,“划得什么船,他往哪里去了?”
身后四五个宫女惶恐不安,一个个连声劝她:“觅姑娘,您这风寒还没好呢,外边儿风大,千万别去!”
沈佳觅哪里肯听,一心想着,拖不住白相公,就拿不回簪子。上了一旁的小船,拿起船桨就要自己动手去划。若不是宫女们拉着,小船早就动了。
“白相公早回来了,正在灶房煎药!”一个宫女从船尾着急忙慌跑来报信。
沈佳觅二话不说,赶紧跑去灶房。
到门口,看见白相公正安安静静地倒药渣,沈佳觅这才消停下来。倚着柱子,死死地盯着他。
白相公一转身,看见她光着双脚站在湿漉漉的木板上,难得皱眉,训斥道:“胡闹!”
沈佳觅习惯了白相公的温文尔雅,从没见他发脾气,小声嘀咕:“你凶什么!”
宫女们也是头一次见他严肃,都愣愣地看着二人。
敌不过脚下阵阵凉意,脑子又犯疼了,沈佳觅不由得眉头紧蹙,浑身发抖。
白相公见状,快步走来,将沈佳觅拦腰抱起,吩咐宫女端药。
沈佳觅眯着眼睛,有气无力地去拽他的衣襟,含糊不清地说着:“你别走……你别走……”
等白相公小心把她放在床上,却见她眼眶泛红,一颗豆大的泪珠挂在脸上,嘴里依就含糊不清地说着“不要走”。
白相公无奈,为她擦去泪珠,看着她说:“我又不走,你哭什么?”
“阿娘生病就没人陪着,于是我再也没见到她。”沈佳觅声音哽咽,小脸皱成一团,难受极了。
一旁的宫女们见她这般模样,心里也难受地很。见白相公沉默着,大宫女便与她回答:“觅姑娘,我们都在这儿陪着,您会好的。”
半晌,沈佳觅没有反应,大宫女刚要发问,白相公就开口了:“过于激动,耗光了精力,昏过去了。”
“那怎么办?”
白相公摸了沈佳觅的脉搏,言语间有些担忧:“马上喂她喝药。”
白相公坐在床头,把她搂进怀里,大宫女用汤勺怎么也喂不进去,一送药就全部漏下去,打湿了沈佳觅的衣领。
大宫女一边擦一边着急:“这药喂不进去!”
其他宫女们看着也心急,都等着白相公想办法。
白相公慢慢放平沈佳觅,说了一句“把碗给我”,随即喝了一大口,捏住沈佳觅的下巴,轻轻撑开她的牙齿,把药渡了进去,很快一碗药见底。
白相公又吩咐宫女们让船工开船,不许任何人来打扰;此外,明日未时再熬一碗药,倘若他没叫人进来,绝不许人走进半步。
宫女们一时还震惊在方才一幕里,白相公又问了一句“听明白了吗”,宫女们才反应过来,连连称是。
带上门,宫女们再也抑制不住,小声讨论着白相公和沈佳觅的关系。
“我看他们二人早就相识,白相公何等人物,向来是波澜不惊、喜怒不形于色,偏偏到觅姑娘这儿,做了多少出格的事儿,简直是泰山崩顶啊!”
“说不定他们早就定下终身了,觅姑娘都病成什么样子了,千言万语都听不进,非要见到白相公不可。”
“快住嘴罢!”大宫女赶快止住了她们,“这些事儿我们彼此间小声议论也就算了,切不可说给外面的人听。万一毁了觅姑娘的名节,官家定不会轻饶了我们!”
“姐姐说的是。”这些宫女平日里都是照顾官家起居的,兹事体大,她们自然明白。
第二日未时熬好药端到门前,听见白相公准她进来,大宫女推门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相公穿着衬里散着头发坐在床上,正给沈佳觅擦汗,示意她放轻动作。
大宫女愣住片刻,赶快轻轻走进来。
准备离开时,白相公又发话了:“去准备银骨炭,屋里四角都要安置;等屋里烧暖和了,伺候觅姑娘沐浴,隔半个时辰就要加水,切不可再让她着凉。你先去准备罢。”
“诺。”
大宫女一路上心里忐忑,总想着,白相公为人端正,应该没有对觅姑娘做出逾越之事。
银骨炭很快找来了,大宫女再回来时,沈佳觅也醒了,白相公已经穿戴整齐,正坐在床头,端药给她。
突然听见白相公问了一声:“可知昨日这药你怎么喝下去的?”
“喝药还能怎么喝,是不是桃酥姐姐亲手喂的?”沈佳觅只觉得他说话没带脑子,反而看见桃酥进来为她忙前忙后,心里感激,“这药一定很甜,是不是桃酥姐姐?”
看沈佳觅满脸期待,桃酥却觉得不太好意思,她不敢看白相公,更不敢抢了他的功劳,只好向沈佳觅微微一笑,欠了欠身,继续手头上的事情。
好在,白相公及时接过话:“确实很甜。”
桃酥手里顿了一下,认为这话值得细品。
沈佳觅不想搭理他,只记得此人一肚子坏水,万不与他牵扯过多。此时已经天明,任务也算完成了,沈佳觅一心想着停船上岸,将要吩咐桃酥行事,不料白相公满目柔情,让她喝药。
沈佳觅被他一双眸子盯得发憷,心想昨晚我高烧,也没色诱他,怎么回事。大抵是有些惊吓,沈佳觅木讷地接过药碗。真以为这药很甜,一大口咽下去差点儿喷出来,还好她生生忍住咽了下去,一张精致的脸蛋瞬间皱成苦瓜。
白相公轻声一笑,吩咐桃酥:“停船靠岸吧。”随即大步离去。
沈佳觅纳闷,这话不该我说嘛?
不一会儿,船停了,沈佳觅简单梳洗,出门时,白相公已经不见踪影,连桃酥等人也已经走远。出乎意料地是,官家的亲卫兵来了,为首的竟然说她偷了官家的宝贝,证据确凿,现奉旨抓她去见官家。
沈佳觅莫名其妙:“什么宝贝什么证据,你好歹跟我说明白吧?”
“一只鹤舞银簪。”官家催了许久,不能再等,为首的言简意赅,说完就请沈佳觅赶紧随他们回去。
沈佳觅一惊,这是她娘留给她的簪子,不是被黑衣男抢走了吗?他偷东西,掉什么不好,怎么掉我的簪子,难不成是故意的?这下真是百口莫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