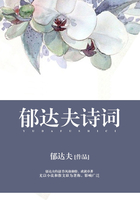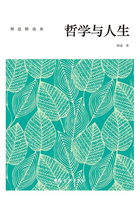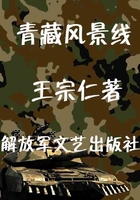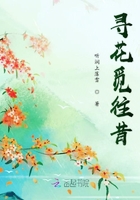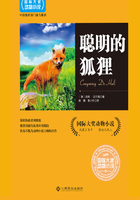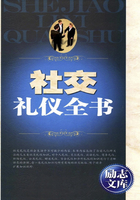斯琴毕力格 著
哈达奇·刚 译
斯琴毕力格
蒙古族,正蓝旗人。1953年生,察哈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1986年开始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迄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约四百余万字。多次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烤羊腿》获内蒙古改革文学评奖优秀奖。
哈达奇·刚
又名那顺,蒙古族,哈达沁氏,1949年出生于鄂尔多斯乌审旗。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评论和民间文化研究,发表著译约五百万字。多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萨日纳”奖、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荣获“自治区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全国德艺双馨民间文艺工作者称号。
我家跟前有一口水井,叫饮马井。
饮马井到底于何年何时由何人所掘,无人知晓。常听老人们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这口饮马井。”这说明饮马井确实有了些年代,并经历过漫长而沧桑的世事。谓其饮马井,从前许是口专为饮马而掘的野井(古时草原上散居的牧人担心井水招引狼群,总要离水而居,而吃水往往到很远的地方去拉),原先在这光有井,而没有人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天下太平,盗贼灭迹了,豺狼逃遁了,我家和饮马井浩特的老住户们才从沙漠深处、柳林丛中来到这片从背靠的青山缓缓而下的辽阔舒展的旷野上,驻牧于这口古老的饮马井跟前,并用饮马井命名了这个新生的浩特。
饮马井的水极旺,像是永无枯竭之日。东西两个浩特共用一口井,好几个棒小伙子轮流汲水,饮了几大群牛马羊,累得满头大汗,饮马井的水别说干涸,连一寸都不往下降。不过井水虽然如此之旺盛,但不会充盈上升,溢至井口,任你拿瓢勺去舀。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其水位始终在一个高度上。她没有那种高兴时升一升、气恼时降一降的轻浮脾气。饮马井就像草原上的牧人一样,直内方外,凝重笃实,锲而不舍,坚忍不拔。饮马井的水,是那么清澈,盈盈的,亮亮的,全无杂质。有时我们掉了颗衣扣在里边,趴在井口遮住阳光往下瞅,会清楚地看到沉在井底、孤零零地躺着的那颗纽扣。
“饮马井的水来自阿儒·布拉格泉,所以才不枯竭。”长辈们偶尔讲的这句话或许有些道理。尽管他们不懂现代科学,无法解释清楚远在三十里外山里的阿儒·布拉格泉水怎么流入了饮马井,但我相信。奇怪的是有人曾在饮马井滩上又掘了不止一口井,相距并不多远,但井水绝无饮马井那么旺,更无那般纯净。这就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饮马井果真有可能与阿儒·布拉格泉同脉相连。由此我想到,当年能够准确找到阿儒·布拉格泉的水脉而掘出饮马井的那位古人,一定是位名扬遐迩的水文专家。
我可算是有幸畅饮饮马井的水长大的人。我的第一串天真稚嫩的笑声即跌入饮马井里,直到如今仍在那里熠熠而动。烈日似火的酷夏,我放牧犊群或羔群归来,总是先到饮马井那儿汲一桶水跪在井边上,像一只小羊羔或一头小牛犊那样,将脑袋伸入桶里,喝得小肚肚鼓鼓的,才腆着肚子往家去。但我从来也没有因为喝了生水而闹肚子或身体有什么不适。现在想起来,饮马井的水很可能有奇异的药用价值。在朔风狂啸的冬天里,我站在结冰的井口上汲水饮畜群,也常常是汗流浃背,周身灼热,从未感到天气有多么凛冽、严酷。可以说,我童年的欢乐、童年的甜蜜、童年的怡情和童年的淬炼,都和饮马井紧紧地连在一起。
饮马井的前边,有一条大道向着东北和西南延伸。我知道往西南去的那条路可直达旗府,但往东北去的到底到哪儿,我至今也不清楚,大概是到更深更远的草原吧。自我记事时起,这条路上就不曾断了行人。有时,远方的路人到饮马井饮了骏马,然后将骏马拴在我家的拴马桩上,进屋打尖。来得最多的是东部沙漠的行人,他们的骏马一个个都很迷人,人们的穿戴也非常讲究,都是既华丽又合身的长袍。尤其到了春末夏初,行人更多,而且大都要来我家坐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为了使刚刚吃到青草的骏马,将头年冬天没有发出的汗出透出尽。)每次,当听到有人在外边以咳嗽打招呼或听到有人在马桩上的下马声,父亲母亲就急忙下地,出外迎接。他们见了面,互相间问炎凉道牛羊,推推让让地进屋。客人喜欢在进屋前跺跺脚,好像那脚上有多少尘土需要抖搂干净似的(其实哪有什么尘土,只是因为草原上有这种苛礼,人们恪守不渝,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而已),然后上炕围着方桌坐下,接过热腾腾的漂着油的酽奶茶喝起来。
我们是小孩子,素来不得跟着客人凑热闹,所以每当有客人来,我们就立即跑到外边,去欣赏拴在马桩上的那些骏马。
“这马跑起来肯定特别快,看那鼻孔多大啊!”
“咦,这马鞍全是用银子做的。”
“快来看,这马鞍有多新,缠在上面的熟皮条还这么白!”
我们围着那些名马奇鞍嚷嚷的当儿,不免在各自的脑子里做些未来的打算,诸如自己长大了也要调理出这样一匹骏马,制作出这样一具漂亮的马鞍,然后到旗里逛一圈等等。我们在外边疯够了,又蹑手蹑脚地溜回屋里。这时,客人们正在兴头上,边喝茶边聊天,不停地从怀里掏出手巾揩拭满面热汗。我们屏声静气,躲在大人们身后,贪婪地听着那些似懂非懂、充满魔力的闲聊。南来北往的旅人就这样倒完满肚子的奇闻异事,便又上马远去。他们带来的是陌生和新鲜,留下的是欢乐和甜蜜,使我们在马桩上的最初幻想不断得到充实,渐渐变为更远大的雄心壮志,开始暗暗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饮马井。有饮马井,我们才得以看到、听到和想到了那么多。
在饮马井西南边的草坪上,偶尔也会有拉脚的车队来宿营。夕阳晚照,众多的勒勒车中间,有座帐篷泛着白光,一炷炊烟袅袅升腾,在火一般燃烧着的天空中描绘着变幻莫测的各种图案。每到这时,我们几个孩子便奔走相告,约定第二天早晨到宿营地去捡车队留下的牛粪。这一夜,我们会整夜地睡不好觉。然而当我们起个大早跑过去时,车队早已无影无踪,连灶坑也已经用头天晚上起下来的草皮复原。蒙古人驻牧于偌大个草原,却这般珍爱每一寸绿,任何人从不轻易去破坏,即使由于不得已挖了个坑取了块土,事后也要尽可能地去修补和复原。我们捡牛粪很卖力,都争着要比别人多捡点。那些为车队拉套驾辕的犍牛因为饱饮了饮马井的水,高兴得会多拉几泡粪下来,使我们捡到比平时多得多的牛粪。有了收获,我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向父母炫耀今天捡了多少多少牛粪,渴望能听到他们的夸赞。那时,不知有多少拉脚车队在长途跋涉中来到饮马井的西南草坪上宿营。因此,在那片草坪上,我捡到了牛粪,捡到了绿色,捡到了喜悦,捡到了勤谨。
我们这些草原儿童不像城里长大的孩子。我们从小会劳动,懂得做大人们的帮手。当然,我也不例外。记得我最早干的活儿,就是母亲去饮马井挑水或饮畜群时跟着她替她拎帆布水斗。后来,我自己也能挑水了,开初挑一次水,中途要歇三次,以后就减到两次和一次了。于是我拿出哥哥的派头,向弟妹们摆功:“今天,我只歇了一次!”那时我感到饮马井离我家相当远。可是那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却觉得那么近,我挑着水甭说中途歇腿,还没来得及拿出架势走得平稳些以免跟以前一样将水泼洒一路,却早已来到家门口。可以说,我是挑着饮马井的水脱去童稚,迈向人生之旅的。饮马井叫我挑的不仅仅是水,还有心气、心力和做人的学问。我的心儿曾让饮马井的水洗礼,我的血液曾由饮马井的水造就。我挑着饮马井的水,肩膀适应了重量,我挑着饮马井的水,肌腱习惯了风寒。
哦,饮马井!
我有多少年没有喝到你的水啦!难怪我竟变得这般羸弱,已不像是一个饮马井的儿子。我太思念你啦,但愿你的水还像从前那么充足、那么清澈、那么纯净!总有一天,我将回到你的怀抱,再次畅饮你那曾哺育我长大成人的清冽而甘甜的井水。
啊,我的饮马井!
1986年7月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