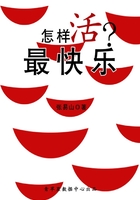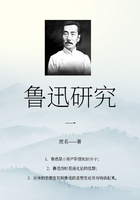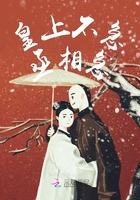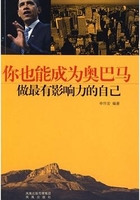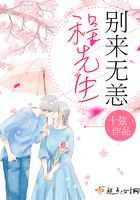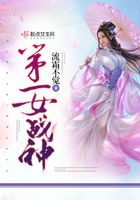吴象
《从太行山到渤海湾》是范银怀同志从事新闻工作的通讯报告选集。他是新华社一位老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一位老朋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记者,我在山西日报工作(注:总编辑),两个单位同在一个大院,关系尤其密切。
范银怀开始当记者,主要采访工业。被称为“煤铁之乡”的山西,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发展,引人注目。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采访。在大同煤矿,随工人钻进薄煤层,看如何充分利用资源;采访太钢工人劳动竞赛,日夜蹲在炉旁跟班,和工人交朋友,写出了《师徒炉》这样生动的稿子,表现了一个记者的敏锐和勤奋,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的更有价值的优秀作品,我认为还要算1964年初与沙荫合写的《大寨之路》。山西老根据地多,著名的劳动模范也多,直到60年代初期,陈永贵还不是太出名的。范银怀是昔阳县人,老家离大寨不远。他认识陈永贵比较早,也早有心想下功夫报道大寨这个山区建设的典型。1963年夏秋之际,大寨遭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但是大寨人没有气馁,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再接再厉,重建家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报社派记者深入采访,进行突出的连续的报道。一段时间,关于大寨的新闻、通讯、评论、照片在省报上频频出现,陈永贵在山西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范银怀也在新华总社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与沙荫共同深入采访,写出了《大寨之路》。这篇通讯,同《山西日报》的报道相比,显然又高了一个层次。它虽然只有八千多字,却概括了报纸上前前后后许多报道的主要内容,而且观点更鲜明,细节更生动,因此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启示更多。新华社播出后,中央和各个省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大寨从此名扬全国,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中南局一位原籍昔阳的领导人李一清,返乡探亲时特意去大寨参观了一趟,很是赞赏,曾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报告,进一步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4年3月毛泽东主席南下视察工作,路过河北邯郸时电召陶鲁笳去汇报。陶详细的口头汇报了大寨的情况,又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报道。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这很可能就是农业学大寨最初的由来。后来,农业部长廖鲁言奉派亲自到大寨蹲点考察二十天,进一步总结大寨经验;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外宾去参观大寨,对大寨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关于大寨的好文章、好报道数不胜数,《大寨之路》反而逐渐不被人多提起了。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利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把这个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榜样,人为地拔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把大寨经验歪曲为“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等等,使农村中原已广泛存在的“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大寨之路》当然更没有人提起了。经过了多年的农村改革,情况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大寨的功过是非,应该可以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今天回头来看,《大寨之路》这篇通讯,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站得住脚的。它为新中国发展过程中这一段并非不重要的历史保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显示了典型报道在重大决策酝酿进程中的威力。通讯本身以事实说话,颇能使人感到记者的才思和文采。“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双肩担来了幸福”,对于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拼搏的人们来说,这两句话仍然是值得深思、令人鼓舞的。
我同范银怀同志成为老朋友。主要并不是由于新闻工作上的交往,而是由于一起在一个村蹲过点。时间是1964年秋后至1965年夏初“四清”运动期间,地点是原平县平地泉,一个近千户的村庄。当时我是县工作团副政委兼村工作队长,他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三个副队长。队员有四五十人,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强调“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扎根串连。我们队部几个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条炕。白天各干各的,晚上就在一起碰情况,讨论工作,处理问题。谈完了正事,还要闲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之所至,无所不扯。互相熟悉和了解程度,是机关里多少年也比不上的。
1966年5月,那场大风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奉派去接管“修正主义”的北京日报,可是不久,我自已也变成了“反革命修下主义”而被打倒。后来又被揪回太原,成了《山西日报》的“头号走资派”,也是省内最重要的批斗对象之一。这当然要株连到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同我接触较多的人,被迫同我划清界限,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尽管我当时思想很混乱,情绪很低沉,但对写大字报的同志并无太大反感,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被迫的。反正我已经成了这副某样,说得轻一点或重一点,材料再添一点或去一点,对我都无所谓了。这类大字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越到后来越觉得荒唐可笑,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则难免也引起我内心的鄙视和愤懑。奇怪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字报高潮中,我始终没有见到范银怀对我做什么揭发。这也许由于报社、分社虽然同住一院,毕竟不是同一单位,他却受到的压力较小。新华社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渠道,受到军代表的支持、保护,可以摆脱派性斗争的干扰,当然借此派性闹得更凶的人也有,可范银怀绝不是这种人。像我在“四清”中早知道的那样,他憎恶见风使舵的人,更不会干落井下石的事,这使我在对他的好感中增添了几分敬意。
七十年代,我重新出来工作,虽然离开了报社,但同范银怀仍有工作来往。1975年他被调到天津分社,从此就很少见面了。后来我也离开山西,辗转来到北京,京津相距不远。他每到总社开会或送稿,总好来家里坐坐。我有时到天津,也总要到他家里去看看,还一起到天津大邱庄、南郊区做过两次调查,后来又一起去过一趟新疆、一趟广东、海南、黑龙江。见面总是嘻嘻哈哈,可以放言无忌,随便倾谈,感到十分愉快。岁月流逝,忽然已年近花甲,头上的白发快赶上我了,而我仍然习惯地叫他小范,老改不过口来。好在他不以为忤,仍然乐于接受,我也就打消了歉意。最近,他来看我,送来一摞稿子,就是这本《从太行山到渤海湾》,要我写几句序言。我们是老朋友,当然不能推辞,说实在的,见到他几十年记者生涯的劳动成果、心血结晶,终于得到成书出版的机会,不由得衷心的为他感到高兴。当前还很讲“官位”,在不少人眼中,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往往以职位高低为标准,这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颇欠公允的。范银怀从初当记者之日起经常深入农村、工厂采访,一直没有离开过第一线的岗位。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对一些有争议的典型和重大的建设项目又作过有价值、有卓见的报道。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辛劳地工作,离休后仍然坚持写作,正像一个真正为人民而工作的人没有什么离休不离休一样,记者也无所谓离休不离休。没有固定任务,正好更主动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写更有价值、更有深度的作品。当了几十年的记者,经历过那么多事件,接触过那么多人物,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脑子里问题一定不少。坐下来静静地读书、思考,有重点的继续深入调查,选准专题潜心钻研,此其时矣。记者与学者、作家是相通的,不少学者作家本都是记者,不少记者兼学者或作家,托社会主义之福,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对小范老弟有厚望焉。在我看,来《从太行山到渤海湾》,既是记者生涯的总结,又是攀登新台阶的起点。在今后岁月中,我相信可以读到作者更好的作品。叶帅诗云:“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若有志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针主义,都应有这样的胸襟和心境,愿以此自勉并作为银怀同志赠言。
(吴象,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