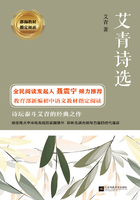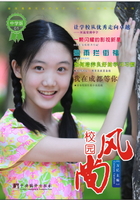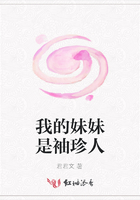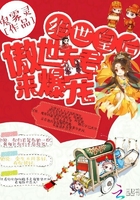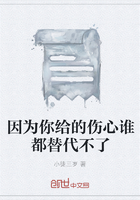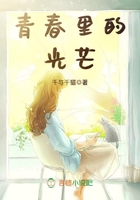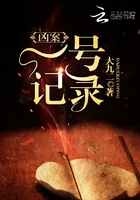矿井里的战斗者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坐上舒适的列车,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旅行的时候;当你们把一铲煤放到刚生起的炉子上,准备烧饭的时候;当你们看见一炉钢炼出来,一度电发出来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过那些终年战斗在地下的矿工?
矿工,正是他们,把祖国地下的宝藏开采出来,供给了工业充足的食粮,供给了人们光和热。
9月下旬,在大同煤田的同家梁煤矿,我们在迂回曲折的巷道里,在工作面和顺槽里,在矿井下的各个角落里,访问了那些终年劳动在地下的矿工们。他们的那种热诚的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不能不写出这篇报道。
巷道侦察兵
深夜,一、二号钻机发出隆隆的响声,从九号井向西南部地表——七峰山顶钻进着。
这里,距地表越近,煤层情况就越复杂,古塘和积水也越多。现在,钻机又碰上了在大同煤田里少有的坚硬岩石。领班工人刘保玉非常谨慎地把着机柄,两只眼紧盯着水表,不时侧耳细听机器声音,想在那里找出五十多米以内的秘密——究竟是偶然遇上石棱呢,还是遇上断层?
突然,机器响声急剧增大,水表的拨针跃升到十五个大气压以上,显然钻眼是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刘保玉赶紧摇动把柄,开足马力,想用水力把跑进钻眼里的东西赶出去;但是,他前后费了大半个小时没有成功。后来他又检查了吸水管,提水冲灌了机器,还是没有一点好转。这时,这位学钻探才满一年的年轻人刘保玉,很在行的对伙伴们说:这一定是石块横堵在钻头圈眼里,看来得大动手术拆卸了。这时已经深夜十一点,离下班时间很近了;但是,他们不愿把麻烦留给下一班工人。于是,刘保玉招呼他的四伙伴立即动手,消除了机器的故障,使机器又正常地转动了起来。
就在这一天,刘保玉和他的伙伴创造了日(班)进37。15米的钻进记录,超过一般钻进速度一半左右。同时,还配合另一架机器,查明了整个三矿西南约二千四百多公尺长的地区内煤藏量和古塘积水情况,为掘进工人探出了前进的正确道路,并且有力地扭转了8月以来勘探赶不上掘进的局面。
开路先锋
电灯把新开拓出来的巷道照耀得如同夜市。刚掘进了九米的煤洞,像一张张开的大咀,高度仅仅二尺一寸。马国富和他的掘进组的工人正躬着腰坐在这张大咀里开动着电钻;电钻发出均匀的突突的声响,煤屑四溅。张德华和郑艮友两个人,曲着两腿坐在煤洞里,低着头,好像忘记了一道道流着的汗水,一锹一锹地把刚打下来的煤铲到面前的一个裁成两半的汽油桶里。一桶煤装满了,站在这张咀外边巷道里的工人,就赶紧拉着系在汽油桶上的长绳,把装满煤的汽油桶拉出来,然后再抬到运煤车上,倾倒出来。
这一切,进行得那样紧张,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只手停顿下来:他们正在为大同煤矿开采薄煤层打着先锋仗——在这二尺一寸的煤层上开凿出大巷来,开凿出供回采的小巷道来。
在二尺一寸高的地方掘进,人站不起来,也不能坐直;但是国家要求煤矿工人们节省国家的资源,把一切可能开采的煤都采出来。马国富掘进组的工人们,在八天以前,勇敢地担当了第一次掘进薄煤层的工作。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这些出色的矿工。他们把原来的弯把锹改为直把锹坐着铲;因为打下来的煤不好往外运,工人们就设法把汽油桶劈成两半,往外拉。他们有时坐着,有时蹲着,有时干脆躺下来干。就这样,他们打开了向薄煤层掘进的困难局面。
出色的炮手
一早,张占孝和他的助手们就带着一天用的火药、炮药和雷管到了工地。工作开始了。等放完第一次排炮,在烟尘未落的当儿,他们又动手绑扎下次用的雷管和炮药;炮烟一落,又立即拿起电钻钻新炮眼。这是张占孝创造的新工作法。用这种办法,不但能按时打眼放炮,永远不误出煤,而且活干得多,还能腾出一个干零活的人去装煤。
张占孝是个在井下劳动了十多年的矿工。六年以前,九号井刚建成开始掘进的时候,由他放了第一排炮。从此,他改掘进为放炮,并且逐渐成了出名的炮手。
最近几天,他在一次上班的时候,遇到一种特殊情况:割煤机发生故障没有割断煤根,前班工友因此也没有按规定打出30个炮眼。当时,回采工人和他一起来到工地等着装煤,眼看就误了生产。怎么办呢?他没有犹豫,马上帮助开动割煤机,并且经过协商,破例地在破根之前打炮眼。结果,这一班工作虽然很紧张,但是活不仅没有少干,而且照例给下班工友留出了30个炮眼。
“顶天立地”的人
八七二工作面的“正规律环”又挨到准备班上班了。支柱工贾维带他的一伙战友在4米多宽、60米长的工作面上开始了工作。
沿着刚刚采完煤的空地,支柱工人们匆忙地把一根根粗大的木柱支起来。斧头敲打着“柱帽”,发出此起彼伏的声响。出色的支柱工王富,干的真快。他把一个2米长,直径六寸多的柱子轻轻地竖起来,然后拿起一块柱帽,拍拍拍三下,就结结实实地顶住了顶板。一排密集的支柱有三百多根,支柱工人们只在六小时内就都把它们竖了起来。
在二十四小时内,八七二回采工作面的十一个支柱工,要在那片采完煤的空地上竖立起四百多根支柱,把回采工作面建设得像一条整齐的地下街道。
前边的煤层采完以后,后边300多米厚的顶板对下面六尺高的空间加上了大到无法计算的压力。支柱工人——这些干着“顶天立地”事业的人,就用他们的劳动向顶板的压力作着终年的无休止的战斗。他们在防止顶板塌落上,先后推广了密集支柱、大冒顶、木板假顶等许多先进经验,使得矿井下最艰难的作业——顶板管理,也在他们的手中得到了顺利解决。八七二回采组从1952年以来,从来没有因为顶板塌落而发生过死亡或重伤的事故。
康拜因司机
被职业病损害了健康的康拜因司机刘振亮常常对别人说:在井上往往想起,不行了,干了这么多年,还能干个啥?可是一出家门,脚就不由已地向井口走,劲头就不知从哪里来了。9月25日下午,他又怀着这种心情来到井下。这是他在井下劳动的第十八个年头了。当时他的两个助手因为水管有故障正在停机修理,累得满头大汗。他一见几乎是跳到了机器跟前。接着就东摸摸,西动动,不过几分钟便排除了故障,使这架巨型的康拜因机又发出怒吼。井下的工人们都知道刘振亮是个不识字的技术工人。刘振亮确实因为没有文化吃了苦头。有一次他参加检修一部机器;这部机器拆卸开以后三十多个珠子上的不同号码,他连一个也不认得。但是勤能补拙。刘振亮苦学多练,两支眼睛紧跟着传授技术的张保和的手转。现在,他不仅能讲出机器的构造,检修一般毛病,而且能用听觉鉴别机器好坏;有时眼睛被煤灰迷住,他睁一只眼合一只眼也能照常操作。
青年技术员
青年技术员安怀国来到八七二回采面,立即招来几个工人,用八九分钟开完了“诸葛亮会议”;随后,他又同大家一起把腐朽了的“荆笆假顶”换成了竹笆,使顶板管理步入正规,在完全无事的情况下开始了分层采煤。这位和矿工同甘苦共患难的青年技术员,常常在矿井里给工人们解决那些意料不到的问题。在八七二工作面里,工人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题目:过去一向在二、三米厚的煤层里进行“一次采高”的矿工,在五六米厚的煤层里要用什么办法呢?这把工人们难住了。这时,安怀国向工人们详细地介绍了分层采煤法的先进经验,介绍了淮南煤矿用竹笆做假顶的经验,并且立即组织工人进行推广,因而帮助工人解决了难题,同时还保证了生产的安全。
安怀国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井下,工人们把他当做出新主意的朋友。最近他被提拔为副段长以后,和老工人正段长协作得象一个人一样。他说:我从老工人那里不仅学到了技术管理的方法,生疏的生产管理也摸到了头绪。
电钻的女“医生”
天刚亮,21岁的女机电检修工梁桂云迈着匆忙的步子,顺着斜井走进了大巷道,然后钻进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小洞——检修室,开始了她的第413个地下工作日。
在这个方圆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小洞里,梁桂云把掘进工和回采打眼工送来的电钻搬到那张被油泥完全浸渍了的工作台上,一只手拿着钳子,另一只手拿着螺丝锥,很熟练地把一部构造复杂的波兰式电钻拆开来。接着,便开始了紧张的检修。她细心地锉着每一个接电的地方,检查和修配了所有的螺丝……;很快地,一台损坏得不能使用的机器,就被这个姑娘修理、安装好了。
这个两年前才到大同煤矿的姑娘,现在已经是深受矿工们热爱的四级工人了。她常常突然出现在煤灰飞扬的回采工作面或正在掘进的顺槽里,去帮助打眼工人检修电钻、架设电线。有一次,她听说青年掘进队的电钻出了毛病;这台电钻是她检修的,她不相信自己修过的电钻没有用就会出毛病。于是,她急急忙忙赶到掘进队,亲自在厚厚的煤层上打了个眼才放心了:原来电钻没有毛病,是青年队的工人使用得不好。
在终年不见阳光的巷道里,在时时可以听到大地震动的地下,年轻的梁桂云,始终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她在井下工作的413天中,从来没有请过假或缺过勤。有时一天连跑相隔成千米的几个回采工作面,两条腿酸得抬也抬不起来,她也不肯休息。老工人向她开玩笑,问她在矿井底下怕不怕?她微笑着坦率地回答说:“下来以前怕过,可是当我戴上安全帽和安全灯,穿上矿工的衣服的时候,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井下保健员
井下一座完全用木板钉起来的小房子里,灯光照耀得象白天一样。这里是九号井的“井下工人保健站”。满屋里陈列着消毒器、蒸溜水箱、电器消毒锅,以及治疗外伤和防御矿工职业病的各种器材和药品。
19岁的井下保健员郭燕威放下八七七回采工段打来的电话,背起急救包一溜烟地向大巷跑去。
八七七回采段的开溜子工冯炳义的手触电烧伤了。郭燕威蹲在这个工人面前,一边耐心地询问触电的原因,一边用消毒剂敏捷地拭去工人手上的尘土,涂上药品,然后又用纱布轻巧地包扎了起来。
刚包扎好伤口的郭燕威,随即又安然无事地开始了工作。他用那只包纱布的手合上电闸,煤溜子哗哗地开动起来,煤炭象滚滚的河水一样沿着溜子向大巷外流去。
这时,这个井下保健员又突然出现在工作面里了。这里的工人正等待着放炮。郭燕威利用这个空隙,向工人们讲解了预防流行性感冒和痢疾等病的方法,并且一再嘱咐工人们要小心,不要受了外伤。
在井下有不少年轻的保健员,他们不分昼夜地守护着矿工。有时出现在顺槽里,有时又到了回采工作面;就连井下厕所,他们也要常常去检查检查。他们就这样和地下矿工经年累月地共同战斗着,帮助矿工们战胜了许多疾病。
(与冯建伟、莎荫合作,新华社1956年10月4日电)
阳泉——精干的工业城市
搭石太铁路客车西行的旅客,进娘子关再行一个多小时就看到一片美丽的山城景色:山腰上接连不断的煤车像黑色的长龙。红色房顶的矿工住宅建筑,依傍山城层层高上。入夜,矿山上闪烁着繁星似的电灯;炼铁厂倾泻出的铁流,映红了天空。这就是山西省的阳泉。
阳泉市区座落在狭长的盆地的山脚下。一条横穿市内的河流把市区分成两半,由市区伸展出去的铁路支线,横跨河流桥、便桥,同工厂、矿山联系起来。
就是这个不足二十万人的城市,每天产出万多吨无烟煤。色泽乌亮、坚硬耐烧的“阳泉块”,受到许多省市居民的欢迎。这里也是有名的手工业地区。除大量冶炼土铁以外,阳泉出产的硫磺,质量之优,在中外都享有盛名。这里,每年以大批硫磺运往天津、东北等地,当作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原料,同时有大宗硫磺出口。
阳泉,在五十多年以前出版的中国详图上,还找不到这个城市的位置。那时它还是山西平定县的一个村庄。1901年英法帝国主义就垂涎于这个富饶的地方。他们修建正太铁路,开拓煤矿,兴办小型炼铁工厂。近三十年来,军阀阎锡山在这里专设实业机构,垄断矿山和贸易市场。阳泉,逐步具有城市的雏型。
但是,阳泉是在解放以后才发出青春的光辉。沿市区向西伸延的矿山上,一簇簇的树木,新的房舍环包着生产矿井,村落。矿区中心的山脚下是矿工俱乐部、医院、副食品供应站……。在这里,解放以前因为无人管理地下资源,把矿山挖成千疮百孔的痕迹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阳泉矿务局所属的生产煤矿,一般都经过改建或扩建。矿山上,正在新建和扩建着五座限额井,目前正式生产的矿井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五座增加到八座。矿井下,已经由爆破采煤法、截煤机开采代替了过去手镐采拉、牲畜驮运的状况。矿工们开始从极其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国营煤矿的生产量已经等于解放前的25倍。
在市区两侧的山脚下排列着林立的厂房建筑群。以近代冶炼设备生产的阳泉铁厂,是由一座小型炼铁厂成长起来的。要改装设备,增大高炉容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的生产量将比现在提高五分之三。修配矿山设备的机器厂,加工粉厂和耐火材料厂都是近年来新建的工厂。解放以来阳泉地区新建的中小型工厂不下二十座。这些工厂的职工多者几百人少者几十人。
阳泉市郊区的山上蕴藏着巨量的铁矿、硫磺和耐火粘土。这里的铁矿、硫磺最适于手工开采。现在阳泉地区的土铁、已经比解放初期提高了5倍以上。这个手工业集中的地区,正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向前进。
阳泉,在祖国工业建设中正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煤矿的新建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煤的产量将高一倍。地质勘探人员不断在附近山上发现新的矿源、矿种。石太铁路的复线工程也由石家庄伸延到阳泉地区。
阳泉市城市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说,阳泉是在改造旧矿井,逐步建设新矿井和中小型工厂中成长起来的。解放以来,经济增长率也比较平稳。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阳泉的城市建设投资并不太大,主要资金用在了扩建沟通市区、厂矿的桃河防洪河堤、河坝。全市主要街道也都平整了路面。市区建筑了二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的房舍。电影院、地下水道设施也适度增加了些。工业建设在迅速发展中的阳泉,没有显出十分臃肿和过于庞杂的现象。
按照城市建设规划,阳泉市仍向着中小型工业城市方向发展。
(新华社1957年7月19日电)
“现场办公室”
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建设工地上,有一座挂着“现场办公室”木牌的简陋小屋。这是不久以前华北太原工程局的几位处地工段长、主任工程师的办公地方。10月中旬的一天,记者来到这里访问时,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记者向围拢在混凝土结构厂房前的人群走去,才看到主任工程师刘邦闻和工段长正同吊装工人们一起,仰头凝望着一架屋梁。暂时停了工的工人们焦灼地等待着工程师拿出主张来。这件事情在工程单位说来显然是质量事故。但是不一会就有了解决屋梁弯曲的办法。主任工程师向记者说:“像这类质量事故,以前是在上边听汇报才能发现的,召开专门会议才研究解决,就地办公以后,从发现到解决只用一两个小时。”
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建设工程今年进入综合立体施工以后,吊装、电器安装等许多工种在同一厂房交错工作,工作中常常互相干扰。每当完成不了计划时,工程单位埋怨安装队不顾整体;安装队却觉得工程单位没有为他们创设好生产条件。7月份,华北太原工程局为了减少工种间的纠葛,决定调派领导干部到工地办公,统一调度生产。
这个工程局的局长、处长、工程师在工地同工人们接触中,不断听到安装工人们提出编订计划脱离实际给他们带来困难,有时把目前不能完成的工程项目列入月计划,有时却遗漏了当前正在进行的主要项目。因此常常形成忙闲不均的现象。过多地埋怨安装单位的领导干部,发现过去依靠进度表格派定计划的作法跟实际出入很大。于是,采取了自下而上编订、审核的平衡计划的办法。照这样下达的计划,都能被各个队组的工人接受,并且连续三个月超额完成。
担任了三个月的现场“总指挥”的主任工程师刘邦闻,颇有感慨地说:“领导干部不长期到现场是会闭塞耳目的。”他的办公室里常常看到下边要求增加机械设备、追加原料预算的预算表。但是因为不知道下边是否真正缺少,也就批准了,到现场以后,发现许多设备并不是缺少,而是调配得不合理,造成了浪费。前些时,一个工段干部向他提出要增购三部价格昂贵设备,因为他摸透了下边的“底”,就把别的工段闲置着的设备立即调整过来,就不用再购置了。这位工程师说:“过去在办公室里,别人提出些问题来,老是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现在却增强了独立处理一些重大技术问题的自信心,因为熟悉了情况。”
(新华社1957年10月21日电)
师徒炉
太钢第二炼钢厂炉群竞赛的旬评比揭晓前,像一场精彩的运动会到了决战时刻那样紧张、动人。厂房前的“战斗快报”上揭示着:到下午三点半,八号炉和十一号炉累计产钢量相等,七号炉拉下二十五吨。究竟这一旬谁来领先,要看最后八小时的决战。
这时,厂房里八号炉的炉火正旺。工人们知道再过两个小时就要修炉了,都忙着加料、清场,抢着多出几炉钢。十一号炉刚修好,正在准备开炉。七号炉工人们正爬在炉身上抢修炉子。按照转炉运转规律,此刻八号炉虽然产量和十一号炉持平,并且正在吹炼,但它快要修炉了,十一号炉、七号炉没有吹炼,可是正站在起跑线上,只要铁水一来,在最后八小时都有超过八号炉的希望。
下午四时整,七号炉抢修完毕。究竟是七号炉,还是十一号炉能赶过八号炉,全看铁水来以后,谁家吹炼得快。工人们都在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可是,不一会,化铁炉上传来消息:现在,铁水只能供应一个炉吹炼。照例十一号炉先修好炉,铁水应该优先供应,于是有人急于为这一场竞赛下结论:“十一号炉领先了。”正在决定关头,忽然十一号炉司炉王富官老师傅摆开手势,指挥吊车工,把一包铁水从自己的炉顶上转倒进七号炉去了。他又跟着铁水包健步跑到七号炉前,向七号炉司炉郭家兴说:“新开炉可要稳些。”他又盯着火色指点说:“摇的角度浅些、再浅些……”
王富官把他们十一号炉争夺冠军的权利让给七号炉,又亲自帮助七号炉操作,顿时引起人们的议论。有的说,这是王富官偏爱徒弟;有的说,人家十一号炉尽是些老师傅,不和青年人比高低。
十一号炉和七号炉是“师徒炉”,并排在厂房的两端。现在七号炉三个班的二十一个人都是青年小伙子,几个月前还都在十一号炉前当徒工。领班的三个司炉郭家兴、义生典、任完印,都当过十一号炉司炉王富官、王虎山等的助手。今天4月间分炉以后,七号炉的小伙子们像刚出嫁的姑娘,操作上一有困难,都随时回来请教。十一号炉的老师傅们对七号炉十分关心,除了从技术上细心帮助外,凡是遇到两个炉子共用一个吊车倒铁水或铸绽时,总是尽先让给七号炉。在十一号炉老师傅们的指导下,七号炉这帮小伙子很快就能独立修炉、开炉了。但是,他们没有拘泥在老师傅的现有技术水平上,在学习十一号炉的吹炼技术的同时,又大胆创造出“三班为一炉,吹炼、周转一齐抓”的一整套经验。从今年5月份以来,七号炉连续被评为全公司的红旗炉。9月上旬,全厂各炉、班、小组都制订出增产节约计划,揿起了“学七炉、赶七炉、超七炉”的竞赛热潮,挑战书、决心书、应战书像雪片似地飞到党委办公室。
十一号炉的老师傅们看着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赶七号炉,也不甘落后,但又不好意思给徒弟们下战书。一天,车间党总支副书记陈兴旺拍着王富官的肩膀说:“老王,你们的徒弟真不得了,现在把你们抛在后面了,你们怎么应付呀?”这句话提醒了王富官。下班以后,他就同另两班的司炉王虎山、杜道荣召开了个三班联合会议。大家分析了七号炉的优点,对照、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共产党员王虎山说:“过去我们老觉得自己吹炼技术有一套,青年人不容易一下学到,可是这帮小伙子们是“一手抓吹炼、一手抓周转”,不只吹炼技术提高很快,修炉时间也比我们大大缩短了。咱们得快马加鞭赶上去!”王富官激动地说:“人家七号炉是三班为一炉,互相创造条件,我们有时只为本班多出几炉钢,到交班时转炉、化铁炉都空了不说,有时渣子也清理不完,给下班造成不方便。”越议论,热气越高,老师傅们都放下师傅架子,要和七号炉比高低。他们当场商定超七号炉的三个步骤:头五天产量上赶上,后五天超过,再过五天把高产、优质的红旗牢牢地插在自己炉顶上。这还不放心。他们像打篮球一样,按炉、按班、人盯人和七号炉展开对赛:甲班王虎山对任完印,乙班王富官对郭家兴,丙班杜道荣对义生典。末了,又都提出保证:“决不能在自己班上拉一吨钢。”
十一号炉研究赶七号炉的对策时,正当丙班杜道荣小组修炉。散会后,大伙说:周转时间缩短一小时,就能多出六吨钢。我们要学七号炉三班大联合作业的办法抢修炉子。他们适当调配了人力,加强了修炉力量,并且改进了操作方法,本来修炉时间计划用三十个小时,实际只用了十五个小时。
炉子修好的第二天,正碰上十一号炉、七号炉同时吹炼。王富官和他的徒弟郭家兴准时来到各自的炉前。他们两人没有当面挑战,但内心里都蕴藏着争第一的炽热的雄心。两个炉的设备、原料条件一样,可是操作技术各不相同。素称老练、沉着的王富官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致胜,每一炉装的生铁比往常多了一吨;号称“快炼闯将”的郭家兴装的料虽然不如王富官多,但二十分钟就能出一炉钢。他们一方面紧张地摇炉、加料,一方面抓紧空闲时间到铸锭台前算计自己的产量,询问对方的出钢炉数。这一班七号炉多做了两炉钢。下班后,王富官觉得自己班上拉下了产量,心里怪不舒服,决心要把拉下的赶回来。他总结了这天的教训,第二天采取了扩大装入量和缩短辅助时间并举的方法,一上班就组织全班工人和化铁炉、铸锭吊车工开展了协作赛。这一班,王富官班做到了多装又快炼,产量超过了郭家兴班。
王富官带领着十一号炉的工人,连续几天超过了七号炉。郭家兴有些着急。9月20日,两个炉子又碰上同时吹炼。这天,铁水含硫较高。王富官炼钢一向是根据原料条件的变化,随时变更操作技术。他知道铁水含硫较多,就得多造渣,因此一上班就组织大伙勤加石灰。但是郭家兴仍是满风、快吹,炼的炉数多,但是有的不合格。在同一个时间里,王富官班虽然只炼了两炉,可是全部合格,一算产量,超过了郭家兴班。这时,郭家兴急忙跑到十一号炉前问:“王师傅,怎么今天废品多?”王富官赶紧跑到七号炉前,告诉他:“像今天铁水含硫高,就得勤造渣,适当延长点吹炼时间。”这一班,王富官一会在十一号炉指挥工人们操作,一会跑到七号炉前指导郭家兴班操作。直到彻底杜绝了废品,他才离开七号炉。
一旬一次的炉与炉评比迫近了,就剩下最后八小时了。当《战斗快报》揭示出他们之间的战果时,七号炉正在修炉。七号炉工人紧张的心情,王富官完全能理解。当铁水不能同时供应两炉子吹炼时,他立刻同全班工人商量:“七号炉是我们全厂的红旗,是我们的标兵,为了保持我们全厂的红旗,我们把铁水让给他们怎么样?”当时个别工人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赶了十几天,临到紧要关头,把铁水让给他们,不是白搭了。”王富官耐心地但坚定地说:“我们是争钢,可不是只为争红旗呀!”全体组员都同意了王师傅的意见。
子夜零点,全厂炉与炉竞赛评比结果揭晓了。七号、十一号两个炉互相激励,互相帮助,钢产量都比上旬提高20%左右。大家都为七号炉保持红旗而喝彩,同时为十一号炉工人们的高尚风格赞不绝口。
(人民日报1960年10月6日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