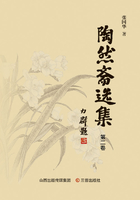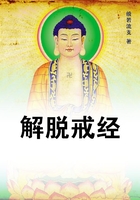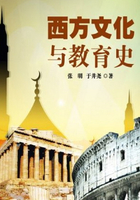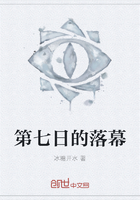成都名诗人钟树梁老先生曾为拙著《辛夷集》题诗一首,结句为“洛神能赋干戚舞,月白风清更促之。”注曰:“作者自序云'无才难以赋洛神,无胆难以舞干戚',信然。”意在嘉许。其实,钟先生注中所引二句只是后学者期之未来的自我鞭策而非自许之辞。因为论才,我少年时只读了两三个月的诗经、左传,并无宿学;中学时,虽有良师如上海诗词家沈轶刘先生(原名桢),却轻舍程门,独攻新诗,失之鲁钝。而今仍属中人之资,何才之有?论胆,倒是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呐喊过,后来也吐过喉头骨鲠,即被罗织,以致“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时下,包容的广度虽有所扩大,要说肝胆相照,唯三五知己而已。
一九五七年的剧震使近而立之年的我坠入了无告无助又无力挣扎的深渊。在呵斥与蔑视下辗转,在无望的劳役中生存。某日,偶得一册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展读之后便立感焦渴的心灵得到了滋润,而且勃然萌发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近乎庄严的冲动。试想,苏轼虽遭贬谪,万里投荒,仍葆旷达的胸怀;辛弃疾、陆游纵然身属闲置,报国无门,而壮志犹存。大师们文采斑斓,才华超卓,于屈而难伸之际,尚能将委婉之情融入豪放的喷泉,这是何等的气概?且宋词多在百字之下,精练深沉,其丰富的节奏与心律几能合拍,便于悄吟默诵,十分适合作为身受困厄者倾诉的文学载体,我何不踵武前贤,以之一抒忧愤?于是,对一些杰作的格律进行了摸索,逐步获得认知,开始尝试缀句、用韵。因为都是藏之于脑,不形于外,所以得以延续。到了六七十年代间,搜查、上交所谓有害书籍,也未能割断我对诗词的探索。这样,暗蓄胚芽,潜酿春醪,就有了一九六四年的“鹊踏枝·哀韩娥”等半成品以及若干素材的积累。为二十二年后的创作做了必要的储备。
一九七九年复归,初步接触到“唐宋词格律”,但还是不谙平水韵,写诗则用词韵。幸而,同里同道同命运的挚友陈侣白兄及时予以提携,在所赠“浣溪沙·答黄稼”里勖勉道:“诗圣草堂千古在,晚晴且理旧吟弦。相看傲骨两依然。”并对拙作加以推荐、评论,使我振奋而起。一九八九年,我又与沈轶刘师恢复了中断四十多年的联系,他从上海来信指出,我的十多首诗词中只有一句“狂流去后崖花艳”可取,强调诗词必具艺术的唯一性,无特色即无所谓诗词,令我茅塞顿开。一九九一年,我去上海拜望沈师,他细询我的境遇并畅谈诗艺,明示“词要学南宋周密”,创作要不惮推敲,力戒孤负。三日相处,终身受益。
流寓蜀乡六十馀年,此地本李杜苏陆流芳的诗词热土,当代人文荟萃,文风鼎盛。本世纪以来,更从而广结诗缘,得到率直真诚的帮助,深感亦师亦友的热情。又承《当代诗词》、《岷峨诗稿》、《中华诗词》和《杏花楼诗词读本》等书刊的不弃以及四川《百坡》、《玉垒》诸诗刊的厚爱,发表拙作,足铭心底,在此一并深致谢意。由于我患“眼底黄斑病变”三十馀年,且现年已过八六,无力对俚句再作纠正,敬希海内方家不吝指瑕,以正谬误。是为序。
作者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于成都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