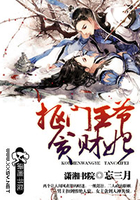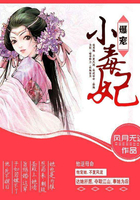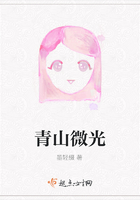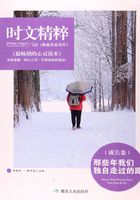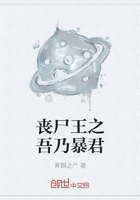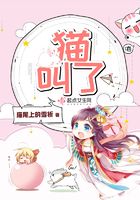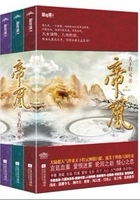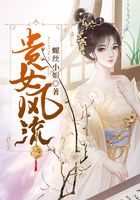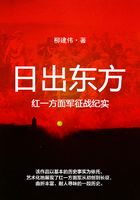妈妈刚去世还不到一年,窦漪房的鞋子上还裱着素色麻布。那本来是一双红色的布鞋,是妈妈亲手做的。窦漪房从小喜欢红色,做鞋的布是妈妈亲手织染的,美丽的土红色,那时候,能染出土红色就已经很不错了。新鞋刚刚做成的时候,窦漪房穿在脚上,惊艳了观津城的小女伴们,她们羡慕嫉妒的眼神让窦漪房很骄傲,她们的妈妈们是做不出这样好看的鞋子的。
鞋子穿上没多久,妈妈就死了。
女童窦漪房对死亡的概念还很模糊,虽然动乱的岁月,经常能在街边看到冻饿而死的流民,她只以为他们是睡着了。妈妈死去的时候也一样,她以为妈妈睡着了,一会就能醒过来,她和小弟弟傻呆呆在守在妈妈身边,直到小弟弟饿了,要吃奶了,却无论如何唤不醒妈妈,无论怎么呼喊,哭喊,妈妈都不会张开眼睛答应,她才感觉到了害怕,哇地一下哭出声。
原来,人们所说的死去就是永远不会醒过来了,就是睡进观津河道边荒郊野外的一个土堆里,再也不会回到他们身边了。窦漪房对妈妈的思念和思念妈妈的悲痛,从妈妈睡进那个土堆开始一日日在增长。
她知道,她和哥哥弟弟从此不会有妈妈的照顾了,她必须快快长大,承担起做家务以及照顾小弟弟的重担。
骤然间少了女主人的家已经完全不像一个家的样子,窦青本来就是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的人,妻子的亡故使他变得更加木讷。将近一年的时间,他老了很多,不到四十岁的人,满脸风霜,头上有了零星白发。孩子们越懂事,他心里越难过,特别是女儿窦漪房,像个大姑娘一样操持着家务,她才刚刚八九岁,还是个孩子。
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有时候,他们还不如一棵小草。
小草在原野上自生自灭,没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孩子的生存要复杂得多,即使最低的生活需要,他们要吃饭穿衣,要有人为他们缝衣做饭。这些事情,窦漪房都学着自己做。虽然缝补衣服的针脚歪歪扭扭的,她能把露肉的衣服用碎布补上了,小手经常被缝衣针扎的鲜血流淌;她能自己到井中提水,提回家洗衣做饭;她做饭的技术越来越高,开始经常会烧糊或者烧夹生,后来能做得恰到好处了。
邻居的张大娘王二婶有时候会过来帮帮她,因为窦漪房的乖巧和懂事,邻里都喜欢帮助她。窦漪房生的瘦弱,却天生好强,她会善意地拒绝好心人的帮助,她知道,别人的帮助只能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最终还是靠他们自己,所以,她一切都学着自己去做,而且力求做得尽善尽美,她是个凡事都要求完美的女孩。
小弟弟窦少君是姐姐的小尾巴,姐姐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乖乖的,不哭也不闹。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哭哭滴滴要妈妈,发现妈妈再也要不回来了,他就不再任性了,他不是个任性的孩子。
农忙的时候,窦青带着十一二岁的大儿子忙田里的活计,不忙的时候,就到河边捕鱼,那个时候,没有人靠养鱼维生,河里的鱼都是野生的,鱼很好捕,许多百姓想吃鱼了都是自己到河里去抓,所以市面上的价钱很低,捕鱼是赚不到多少钱的。窦青捕鱼,一是为了给家里挣点零花,二是为了消磨时光。闲下来的时候,他心中有无限苦闷,妻子故去,家没了家的温馨,世道依然不太平,虽然已经是汉朝的天下了,天下还是大乱,回老家的路依然漫长,依然遥遥无期。
和所有的穷人一样,窦青喜欢夏天,喜欢秋天,夏秋是收获的季节,地里有了收成,下来了新粮,他们一家人不会发愁下锅的米,另外,那些温暖的季节,可以到河边捕鱼,严冬河里结了厚厚的冰,砸开冰层去捕鱼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北方的冬季很冷,两千多年前的冬季比现在要寒冷得多,砸开的冰层很快就会又结上一层新冰,有时候半天也捉不到一条鱼。
冬日捕来的鱼,他一般不去市上卖。冬季家里缺粮,有几条鱼熬汤,可以聊以填饱孩子们的肚子。捉不到鱼的日子,窦青就觉得无颜回家去见孩子们,他们站在寒冷的家门口,一双双充满期盼带着稚气的目光,望着父亲回家的路,他两手空空的,怎么对孩子交待?两个大孩子知道父亲的辛苦和苦衷,小儿子还不懂这些,吃不上饭,他会哭闹着向姐姐要吃的,那时候,窦漪房就会陪着小弟弟落泪,窦青心里酸酸的,却不敢当着孩子们掉一滴眼泪。
他不能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他在他们面前掉了泪,孩子们就更无助了,他必须让他们感觉到,爸爸是坚强的,是他们永远的依靠。
许多时候,只要是到河边捕鱼,不管遇上多大的风雪,窦青都要坚持做到有所收获,哪怕只有一尾瘦瘦的小小的收获,回去对孩子都是个交待。
他期盼着春暖花开的日子。
春暖花开了,虽然依然会挨饿,天气总不至于会冻死人了,又冻又饿,冻饿交加的滋味简直太难受了。
其实,春暖花开对他们一家也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春暖花开的季节,依然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冬季尚有一些存粮可以对付着过去,到了春天,存粮吃完了,新粮没下来,吃饭成了更大的问题,从河中捕来的几条小瘦鱼是解决不了关键问题的。
窦青依然要去捕鱼。
孩子们要到野地里挖野菜。
此时,河边捕鱼的人比鱼都多,荒原上挖野菜的人比野菜都多。
窦青暗暗思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实在不行,过些日子带着孩子们回老家去,在那里自己有块好一些的田地,或许能养活一家几口,还说不定能余下些钱粮供大儿子到私塾读书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