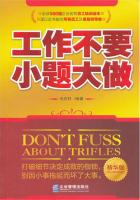“我自己?”秦扬瞪圆了眼睛,满脸的惊愕:“我怎么知道。”
“你当然知道。”
纪檀风远远叹道。要说他什么也看不出来,自然是不会的,女孩子就是这样,娇憨的,需要别人去猜,也罢。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比起苏玉镜那古怪至极的个性,拂芷已经算是小天使了好吗?
“快进来吧,”林拂芷往门口冷冷一瞥道,吓得某位秦姓男子一溜烟的钻进了屋内。却没看清门口少女的眼神。她是那样恳切的看着林拂芷。就好像,故人重逢一般。
“琬琬?快来快来。“见了林琬琬,康同月脸色一变,却又在极快的恢复了笑颜,她拉起了林琬琬的手,恳切的看着她,就好像,故人重逢一般。
“林琬琬?!“康晋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却被眼前景象吓得砸了瓷碗,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将纪檀风扯到一旁:“你们怎么把她带回来了?!”
“我不知道啊“纪公子无辜地摊了摊手,顺便指了指沙发上正吃橘子的秦扬:”他带的。“
“……“康晋一时语塞,气得愣了好半天方才转头,咬牙对纪檀风说道:“那你知不知道,林琬琬是林德寿的女儿。”
听闻林德寿三字,纪檀风因困意而半眯着的眼儿忽然圆瞪,“该死。”他暗骂道,秦扬脑子是给扔了吗,活该林拂芷不理他。
那边厢康同月正和林琬琬愉快的攀谈着,两人似乎还手拉着手,一切竟然颇似岁月静好。
午饭后,众人各自回到了房间休息,而二楼康同月的房间,却迎来了新的客人。
面前姑娘依然身着蓝裙,神色却宛如变了一个人,她垂着眼眸,敲开了那道西式雕花的木门——尽管她知道门背后等着她的是什么。门后面的椅子上,坐着笑意盈盈的女主人。
她坐在了她面前的椅子上。
康同月十分清楚面前人是来干嘛的,就如同林琬琬知道她明天的结局。
“你的姐姐不会有事。“
“我以先生的名义保证。”
少女悲悯的言辞在过分寂静的房间中显得分外冷冽,缓缓流淌的钟声默默宣示着姑娘余下不多的时光,没有人想提前知道自己的死期,何况她只有十七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
颤抖的身形宣泄着无助,她定定的看着康同月,眼中氤氲着些许水雾,她是恐惧的——或者说,谁人不恐惧呢?当权者恐惧生,被统治者恐惧死,封建恐惧开放,王朝恐惧灭亡。总有恐惧的理由,也有,不恐惧的理由。
人们拥有着,所以恐惧着。
“你们要保护好我的姐姐。”
林琬琬哑着嗓子道。言语间,泪水悄然滑落,在明晃晃的蓝裙上,晕出一片深波。面前是深渊,身后是愧待已久的姐姐——这世间哪有真正不怕死的人呢?只是他们在条件的挟制下没得选择罢了。林琬琬自认不算感性,但是条件好巧不巧是她的姐姐。大无畏的意义总归是深刻的,血红方是丰碑最好的底色。
“你看外面天气真好。”林琬琬抹了把脸,站起身来走向窗前,抬手抚向窗玻璃,她疼惜地看着这方天地。
这方充满希望的土地,充盈着阳光,树荫,蝉鸣,还有相亲,所爱,以及携手。
或许,你真的恨透了我的父亲,或许,你要走的路艰难险阻,我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只够帮你挡这一个劫了。
林琬琬,时年十七,林德寿的女儿,康同月的手下,林拂芷的妹妹。
“林琬琬都走了,怎么还在生闷气呢。”苏玉镜站在门口,盯着里面在床上缩成一团的林拂芷。
“那是林德寿家里那个!林德寿!你可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林德寿是谁。”床上的小团子瓮声瓮气地说:“我要跟秦扬绝交。”
“绝交?你俩很熟吗?”苏玉镜半倚在门框上,瞥了瞥人。
“不熟!”
而另一边的房间,秦扬快把地板给跺穿了。
“你慌什么慌。“纪檀风靠在椅子上,慢慢的抿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你说我慌什么慌”一个抱枕给扔过去,差点给泼在衬衫上。
眼见咖啡差点给洒了,纪檀风也不恼,慢悠悠的将手上物什放下,瞥了瞥那人神色,轻笑道:“我怎么知道你慌什么……哦!是不是林琬琬走了,你有什么话没告诉她?”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又一个抱枕飞过来,砸中了纪檀风的头。
“嘿我说你个….”纪檀风吃痛,站起来作势要打:“你再这样我不告诉你了啊”
“那你快说。”秦扬白了一眼人,顺手给扯到身边坐下:“可不许再胡说了。”
“切,怪不得人家拂芷妹妹看不上你,要我说你就是个傻子。”
“你可自己个儿看看吧你,林琬琬是谁家的人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就一个劲儿往拂芷面前带…….”
“啊?“
莫名高八度的疑问打断了眼前激烈而聒噪的连续句。
“啊?你还啊?”纪檀风愣了愣:“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真不知道。”秦扬的脸色略有点苍白,他瞪大了眼睛,脸色复杂。
“她是林德寿的亲生女儿啊……”纪檀风扶额叹道
“林德寿?哪个林德寿?”
“还能有哪个林德寿?”
秦扬的脸色极度奇怪,还有些苍白。诚然,所有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理论的相背,但是令人不敢想象的是相背的理论竟然出在同一个人身上。
林琬琬是秦扬的同事,而林德寿当年不仅亲自将林大人和其亲生母亲赶出了家门,而且还在朝廷上,具有绝对话语权。
“我不信,我绝对不信。”
“事实就是这样。”纪檀风叹了一口气:“你成功触了林拂芷——和大家的霉头。”
“可是……”
这依旧令人不敢相信。
然而.....有些事情是不由得人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