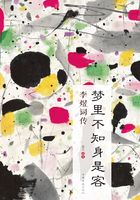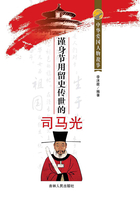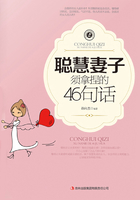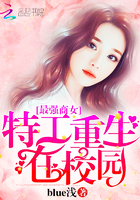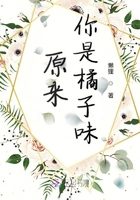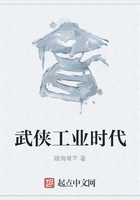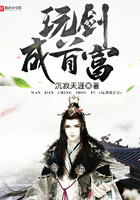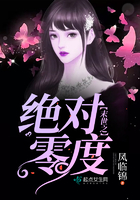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只有关键的几步。告别故乡,走出家庭的鲁迅,来到南京求学,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
那时的人们都认为读书应试是“正路”,而要进洋学堂,学洋务,便会被看做是把灵魂卖给了洋人,要加倍受到奚落和排斥。就在鲁迅报考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在这里供职的本族叔祖,却为他改了名字,叫周树人。一个如此保守的人,却能起出这样响亮的名字,也算是历史的幸运。从中我们也看出鲁迅的人生选择,伊始就具有叛逆性。
1898年,鲁迅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的管轮班,也就是后来的轮机科。
这一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发生了。这个属于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危难的中国,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前,起到了传播新思想的积极作用。
鲁迅还在绍兴时,就看过维新派主办的《知新报》,深为面临垂亡的中国而忧虑不安。可此时的水师学堂,虽然是洋务派创办的“洋学堂”,却连一丝新鲜的空气都没有,每日照例是读古文、作八股、爬桅杆等等,这使鲁迅十分失望,他决定离开水师学堂,改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就在鲁迅进入矿路学堂前的空隙,回绍兴探亲时,发生了一件事。他在母亲和同族叔辈的劝说下,和二弟周作人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县考初试他考中了,而此时四弟不幸夭折,他忙完丧事,就返回南京,没再参加复试。这事不难让人看出,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中的鲁迅,虽然反感封建的科举制度,可为抚慰亲人还能强作敷衍,最后托故不参加复试,也终究表明鲁迅不愿意再走老路的绝决态度。
矿路学堂,开始了鲁迅真正的学习生活。这里学习德文,还有物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和金石学等,这使鲁迅获得了自然科学的初步知识,也都是他过去所不知道的,因而感到非常新鲜,后来他曾经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足见这段学习生活于他是很有意义的。
矿路学堂的总办,倾向维新,这使学校有了开明、清新的风气。校中设立读报处,有《时务报》、《译书汇编》等,广泛地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鲁迅热心于搜求和阅读新书报。最喜欢读的是一本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这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书籍,为鲁迅展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全新的思想境界。他一口气读完,直到背诵如流。他那颗年轻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成为这位东方文化巨人真正的开蒙读物。他开始意识到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在这个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世界上,如果再按照老一套的生活方式,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要“自强保种”,就必须抛弃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虽然那些东西是“祖传”的法宝。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新鲜的事物。
鲁迅读书极其刻苦。他在学堂年龄最小,但理解能力却很强。每逢考试,他不临渴掘井,总是成绩十分优异。鲁迅从不爱虚荣,他把得到的金质奖章变卖,用来买书,也买点心请同学。他总是抓紧时间,追求新学问。他设想要用科学救国,要用先进的知识教育民众。
“新学”的教育,并没有削减鲁迅对文学的兴趣。除了功课,他还很爱看小说、戏曲。《红楼梦》、《西厢记》他喜欢读,林琴南的译本小说他也很感兴趣。从少年时代起,鲁迅对古代文化的学习,就很显示出他的独特眼光。凡是“正宗”、“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另外去找有价值的作品来读,从中汲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为他日后从事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3月,被批准赴日本留学。开始了他文化积累的新时期。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与美洲隔洋相望。明治维新之后,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在精神上、文化上缩短了现代化差距。因此,学西方,就得学日本,日本成了中国了解西方,走向世界的文化桥梁。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
鲁迅到日本,就仿佛登上了一座通往世界的快车。他开始比较完整地接触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为他在文化战线上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料。
鲁迅先在弘文学院集中精力学日语。他夜以继日,以过人的毅力和资质,十分扎实地掌握了日语。这为他了解西方,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鲁迅没把自己关在书屋里。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鲁迅深受影响,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听讲演、赴集会,满怀激烈的爱国之情,使他志在光复。
1903年的一天,鲁迅不顾清政府的警告,毅然剪掉了那根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剪掉之后,还照了一张照片,并在上面写下一首《自题小像》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表达了他反抗种族压迫的决心。
要革命必反清,首先要唤醒愚昧落后的群众。由于身处异国,刺激多端,他便深入思考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中国的病根何在?他想从寻找民族文化的积弱,来探求一条民族解放之路。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文化来装备国民的问题。可见,他一开始就把视点投射到深层的文化方面,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显现出独到的价值。文化发达的日本,使鲁迅感受最深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发展,得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他便设想,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破除中华民族陈旧的思想观念,从传统、保守、封闭中冲出来,才能得以振兴。此时的鲁迅开始致力于译介科普知识。
鲁迅自小对文学的偏爱,使他总能借助文学的笔法,来翻译、写作科学读物,以求实现他科技救国的理想。他介绍科学知识,从翻译科学小说入手。他说:“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
1903年是鲁迅翻译介绍科学小说的丰盛时期,他先是用章回体形式翻译了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科学小说。还发表了《说》介绍关于镭的发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与人合编了《中国矿产志》,翻译了《物理新铨》、《元素周期则》、《北极探险记》。1905年,他又译《造人术》,介绍人工制造生命的科学实验。这在当时是最新的科学项目,直到今天也还处在整个自然科学的尖端地位。
青年爱国者鲁迅,学习、介绍科学,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斗争的需要,他的有关科学的论著,时常燃烧着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流露出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焦虑。出于破除迷信、改良思想的崇高目的,当时的鲁迅,对于颇为风行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是认同的,从中他也确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904年,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抱有坚定理想的他,毅然改学医学。对于这一选择,鲁迅是经过考虑的。他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同时又想到学了医学可为战争尽力,在平时又可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所误的病人,以求改变国民愚弱、振兴祖国的目的。他曾对同学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仙台医专的学习,使鲁迅“日不得息”。他开始学习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等课程。鲁迅非常勤奋,优异的学习成绩曾引起少数心胸狭隘的日本学生的嫉妒、污辱,这些刺激,使他深切地感到生为弱国人民的痛苦。鲁迅一边发愤读书,一边热心阅读那些呼喊复仇和反抗的文学作品,从中突出地感到进步的文学作品在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上发挥的巨大作用。鲁迅在医专的学习,深得解剖学教师藤野先生的赞赏和帮助。
人生旅途,偶然的事件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鲁迅“医学救国”的理想,却被一次“幻灯事件”给击碎了。
这一天,他在老师放的幻灯片中,目睹了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枪决,而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他们竟无动于衷。就在这时,“万岁”的欢呼声,竟从那些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学生口中喊出,直刺鲁迅的心。他怒不可遏,愤然退出,好几天无法平静沉重的心。他明白了一个真理:医学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革,并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如果民众不觉悟,即使体格再健壮,也只是能做枪决示众的材料,或当麻木的观众。他认为,头等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唤醒麻木的中国人,而善于改变人精神,“最有力莫如心声”,应首推文艺。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鲁迅告别了敬爱的藤野先生,离开仙台,奔往东京,去开拓救国图强的新征途。也就是从这时起,鲁迅选择了改造“国民性”这项文化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