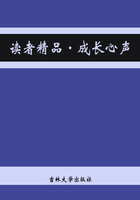我生于1980年,自我记事时起,我家就有辆在村里很显眼的交通工具——“大金鹿冶。由于那时年幼,我最初的记忆是极模糊的,它时而放在门口的胡同里,时而放在南屋的隔挡里,有时候上着锁,有时候没有上锁,有时似乎是俺爹骑着它去大队干活,有时似乎是村里人来借用,统统的记忆都很模糊。
等我慢慢地长大了,各种记忆才渐渐地清晰起来。那时候大人都是很忙的,俺爹当时是大队的拖拉机手,他也很忙,但是他从来不忘见缝插针地向我们几个孩子抛洒他的父爱,每当这个时候,自行车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
弟弟还小的时候,大金鹿前面的横梁上,架着一个三面带围栏一面开口的小座椅,弟弟就坐在那小座椅上,我和大我七岁的姐姐坐在方方正正的后座上,我在前,手扯着爹的褂子,大姐在,紧紧地搂着我的腰。爹有时候会带我们去他工作的大队仓库转转,有时候带我们去他的朋友家坐坐,一个男人驮着三个孩子,一路响着铃铛,走到哪里都是一道让人眼热的风景线,一是大金鹿耀眼,二是计划生育抓得正紧的时候,一家有三个孩子耀眼!
弟弟大些后,爹把小座椅撤了,大姐就侧身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两条腿一前一后,一长一短地耷拉下来,我和弟弟则坐在后面,小我两岁的弟弟在前,扯着爹的褂子,我在后,搂着弟弟的腰。就这样,我们的活动范围开始外扩。
爹会带我们去地里看庄稼。麦苗刚刚返青的春天,到了地头,爹一只脚一支,大姐从横梁上一滑就出溜了下来。爹把右腿往前梁上一绕也下了车,把大金鹿往地头的暄麦苗上一扎,却不抱我和弟弟下来,只告诉我们不要动,免得车子倒掉,说看看麦苗我们马上就回家。我们两个小人是害怕的,想下来却不敢说,本是不想动的,使劲地绷着,却不想由于紧张,意志反而不受了控制,你弯悠一下,他弯悠一下,那立在春天暄地上的大金鹿就倒了!我和弟弟急得大叫,爹明知地暄,又有麦苗垫着,伤不了我们,也不着急,慢悠悠地跑过来扶车子,把我们解放了下来。大姐嘴巴快,免不了回家跟娘告状,当然了,爹是免不了要受娘的埋怨:孩子这么小,吓着怎么办!
爹还会带我们去赶集。从我们村到里岔有五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对大姐这种大孩子来说不远,看看路边的风景,想想开心的事情,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但对我和弟弟这种小孩子来说这路就有些长了,这长长的路足够把自行车上的我们给摇晃迷糊了。爹一是怕我们睡着了从自行车上跌下去,二是怕睡着了受凉,就一路上不住地喊我们的小名,听我们答应得干脆,那就没事,继续骑车;如果听我们答应得迷糊,就空出一只手摸摸我们,再抬起屁股轻微地颠几下,车子一颠吧,迷糊着的我们就猛地惊醒了。如果听到我们没答应那就是坏菜了!爹得赶紧下来查看,不过由于爹喊得勤,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
大金鹿真是载重型的,达到极限时,俺一家五口都坐上面,它也跑得很潇洒。俺大姐坐前梁,俺娘坐后面一手揽着我一手揽着俺弟弟,那是很美丽、很幸福的一幅画面。
大金鹿好,俺爹却很少单独用它驮俺娘出去,那个年代的人还是比较保守的,即便是两口子一起出去也都羞答答的。记得有一次,俺爹用大金鹿驮俺娘去赶集,驮四个人都没出过差错的爹,因为村里人的几句调侃,直接驮着俺娘摔倒在沙土路的沟里,自那之后,俺娘再也不肯单独坐俺爹骑的大金鹿了,哈哈。
大姐长大了,要去里岔上学,大金鹿就归她了。她长得高,学骑车学得快,一根棍子绑在后座上,溜了几圈,大人扶着她蹬了几圈,她就学会了。学会后不久就开始带着我们到处乱窜,去里岔、去甘沟庄、去孟慈,甚至还去过尧王山、牧马城。那时候的我胆子也大,在大姐那骑得歪歪扭扭的大金鹿后座上坐过,蹲过,也站过!当然也没少挨摔,但热情却总是不减的。
我长大了,要去里岔上学,大金鹿就归了我。我个头矮,车子后面绑着棍学了整一年才找到骑自行车的感觉。那时候我够不到座位,开始时是插空骑,腿伸到前面横梁的底下,蹬着脚踏,自行车竟然也骑得走,后来高些了,就把腿放在大梁上,蹬车的时候屁股来回晃着,不蹬的时候就把右腿搁在横梁上休息。由于长得慢,个头矮,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骑车的。
再后来,大金鹿是弟弟的。再再后来我们都长大了,村里家家都兴起了骑摩托车,虽然大金鹿这服役30多年的老伙计还健壮如初,但是也不得不光荣下了岗。俺爹舍不得把大金鹿卖给收废品的,就在俺家牛棚的南墙上钉了个大铁镢子,把它挂了上去。年复一年,时间尘土覆盖了它的本色,却覆盖不了我们的记忆。
(2015.5.26于江苏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