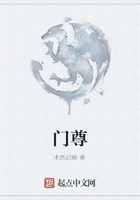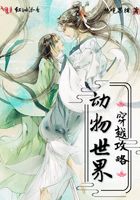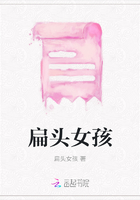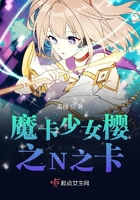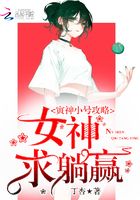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叔那次为了下楼给我开门竟然摔成了骨折。
四叔家住在三楼。那是个寒冬的夜晚,街上的风刮得噼啪作响,震天动地。
那晚,我趁着回市区的空当,想去看看四叔。
那段时间,我一直住在郊外新筹建的项目工地上,很久没有和四叔见过面。
我开车赶到四叔的家属院,时间已经很晚。
四叔家楼道的大门锁着,我进不去,便给四叔打电话。
四叔可能已经睡下,但听到是我,异常地兴奋。
四叔把声音提得又高又亮。
四叔说,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孩子。
四叔的声音,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穿透力量。我一直感觉四叔说话的声音是直接从丹田里迸发出来的,像在野地里或者风中喊人的那种腔调。那种充满活力的炽热元气,响亮,清澈,饱满,极具慈爱与宽厚的内容。
这是四叔将近二十年来一直呈现在我面前的健康而年轻的标志,尽管他已七十多岁。
四叔叫我的那声孩子,让我已经久违了的父爱又悄无声息地回拢到自己身边。
父亲去世后,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再出现过。
我感觉那一刻心中有股温热的暖流,通了电一般瞬间传过我的周身。
四叔下楼的时候脚步很轻,楼道里的声控灯并没有因为他的走动而明亮起来。
直到四叔哐啷一声将楼道大门的锁具打开的时候,那些灯们才像在梦中被突然惊醒了一般,赶紧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亮了起来。
我趁着昏暗的灯光,看到了四叔熟悉的身影。
四叔穿着睡衣,外面裹着一件棉袄,依旧是那种紧凑而轻缓的步幅。
外面的冷风像一伙来历不明却又明目张胆的窃贼,肆无忌惮地打着回旋,从四叔刚打开的门缝中呼啸着冲进去。它们卷裹着尘土和沙粒,击打在靠墙摆放在楼道里为了防盗而专门用铁链与扶手锁起来的自行车和电动车上面,发出咔嘣咔嘣的脆响。
那种声音,生硬,被动,干裂,充满悲情和感伤的味道。
四叔连声招呼我赶快进去。
当时,我并没有发现四叔身体有什么异样。
四叔在上楼的时候,还十分亲昵地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那晚,四叔陪着我说话,坐了将近半个小时。
而在两个月之后我再次去看望四叔时,却发现他的腰部夹着长长的钢板。
我仔细询问,才听四婶说起了原由。
四叔那晚为了尽快给我开门,脚步踩空,仰倒在楼梯上,摔断了腰骨。
我很难想象,四叔当时是怎样忍着断骨的剧痛继续走下来给我开的门,而且他竟然能够表现得那样镇静,那样顽强,那样地若无其事。
我听四婶说完,感到心中针扎一般疼痛难忍。
我说,我那天晚上不该那么晚还来打搅你们,给四叔造成这场灾难。
四叔听着我的话,突然绷起脸,正色道,傻孩子,这咋能怨你,是我不小心而已。
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懊悔和歉疚。
四叔是我四姐婆家叔叔。
因为他在家排行老四,我跟着四姐夫和四姐,称呼他四叔。
我四姐的那门婚事,纯粹出于母亲当初知恩图报的心情。
我小时候得过两场大病。一次是全家人都记不清楚的什么病,已无从考究;另一次是急性脑膜炎。
这两场大病,都是四叔的三哥光甫叔给我看好的。
母亲主动让四姐嫁到光甫叔家当儿媳,因此,四叔成了我们家的亲戚。
四叔家的成分不好,早年被定为地主,土改时期属于管制对象。
既然是管制对象,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会被拉出去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我父亲当年被抓壮丁后,就是在那个时期,随着国民党第一四九旅弃暗投明回到村子里的。
刚回到村子里的父亲,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
大队支书虽然身材矮小,但手段毒辣,飞扬跋扈,横行乡里。
父亲看到支书仰仗权势胡作非为,便义愤填膺,为别人抱打不平。
父亲对着支书的背影,啐上一口唾沫。
父亲大概感觉不过瘾,接着又骂了一句,鸡巴毛,在乎你个碰蛋虫(碰蛋虫,豫西方言,形容人特别低矮)。
父亲这句不仅蔑视而且带有重大攻击意味的辱骂,被已经走远的支书隐约听到。
父亲第二天便被罗织下一大堆子虚乌有的罪名,扣上了“四类分子”的政治高帽。
那顶大山般沉重的帽子,父亲被扣了很多年,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受尽屈辱。而我们姊妹更是恨不得将头低到尘土里。
父亲充满戏剧性的厄运,能够充分借斑窥豹,折射出当年那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荒诞不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严重程度。
用同样的道理,依此类推,当年给某个人或者某个家庭划定成分,简单,粗暴,不负责任,甚至打击报复,带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色彩。
我不知道四叔的祖辈究竟拥有多少田地房屋,有没有坑害过贫苦佃户,最后又究竟因为什么而被判定为地主。但从四叔他们兄弟四个腼腆善良的为人和高尚的品行中,可以十分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并非坏人。
可惜的是,在那个以斗为纲且忽左忽右的动荡年代,人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被权利的代表所认同,即使权利错误地落入那些并不能代表权利的人们手里。家庭成分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将完整的世界分割成高贵与低贱的阴阳两面。
四叔一家当时就生活在这样的阴暗里。
家里的成分对四叔的影响不算很大,因为四叔还是在孩子的时候,村里有人不愿去当兵,让他冒名顶替。迫不得已的四叔,阴差阳错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且转业后被分在省会郑州医药系统工作。但在“文革”中,他也被调查了一段时间。
因为四叔所在单位的军代表在有次洗澡的时候,发现四叔腰部有个伤口。军代表怀疑那是枪伤,其实那伤口是四叔早年长疮留下来的。但军代表不相信,便派人到老家调查。当时的大队支书还算正直,如实汇报四叔的情况,四叔才算躲过那场灾难。
而光甫叔却没有四叔那么幸运。
光甫叔那时候是上店公社卫生院的一名大夫。
尽管光甫叔医术高明,且有良好的医德,救过乡里乡亲很多人的命,但光甫叔这些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并未能换得社会的认同和乡亲们的尊重。
光甫叔一直活在家庭成分的阴影里,在人前难以抬头。
光甫叔很少开心地笑过。即使笑,也是那种迫不得已的虚与委蛇的苦笑。
那种笑,是勉强装出来的,无奈而酸楚,比哭还难过。
光甫叔无论是行走在田野旁的小路上,还是在给人看病的时候,他始终面无表情,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心中的烙痛,不仅让光甫叔自己的内心充满无辜的疑惧和自卑,更让他的几个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体会着被孤立和分割的落寞。
这种孤立,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和幸福。两个已到婚配年龄的孩子,因为家里成分低,始终说不下媳妇。
那年秋天。
我身子打战,发高烧,翻白眼,不省人事。
母亲急得捶胸顿足,不知所措。
光甫叔回家,路过我们村。
光甫叔坐在我们家门口那颗枝叶茂密的椿树下,面无表情地给我把脉看病。
光甫叔听完我的脉象,又翻翻我的眼皮,看看我的舌头,仍然面无表情地掏出笔和纸,龙飞凤舞地写下一个药方交给母亲。
母亲紧抓药方,汗流浃背地跑到大队卫生室,按药方抓了三服药,花了一毛五分钱。母亲掂着那三服药,火急火燎地又跑到光甫叔家。
母亲哭着哀求光甫叔。
母亲说,他叔,你再去给孩子好好看看吧,他的病那么重,你给他开这点钱的药,哪能治好啊。
光甫叔这次笑得很开心。
母亲几十年后给我形容,光甫叔那次的笑就像冬天的阳光那样璀璨夺目。
光甫叔说,嫂子你快把这些药给孩子熬好服下,行不行吃了才知道。
母亲将信将疑,把药熬了给我服下,病竟然奇迹般好了。
母亲登门答谢。
母亲当然知道光甫叔家成分低,孩子不好说媳妇。
母亲说,他叔,我别的没有,只有那几个闺女,你相中哪个都行,给你当儿媳。
光甫叔那次并没答应。
光甫叔虽然对我的几个姐姐都相当满意,但因为他给我看好了病而与我们家结亲戚,有乘人之危占便宜的嫌疑,他怕被几近疯狂的人们抓住把柄再生事端。所以在我的病好了以后,也就当是一种无心的闲话,说说也就过去了。
母亲认为光甫叔清高,看不上我的几个姐姐,所以也没再提及此事。
直到我再次患病住进上店镇卫生院,光甫叔跑前跑后,安排这安排那,母亲才又将当年的话拾起来再说。
母亲让我四姐嫁给了光甫叔的二儿子。
母亲还当起了媒人,又将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说给光甫叔大儿子做媳妇。
光甫叔非常感激母亲的知恩图报,因此他对我母亲一直很敬重。
我当兵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光甫叔还专程跑到我们家,鼓励我到外面好好干,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而在他患病去世前,他还让人把我母亲和父亲叫去,和他见最后一面。
四叔心中时刻装着老家亲人。
四姐生小儿子那年患胆结石,先在县医院动了手术,之后感染,住进洛阳第三人民医院。
那年我军校毕业分到郑州,还没见过四叔。
我想不起当时四姐夫为什么没有直接给四叔打电话,而是让我去告知四叔四姐在洛阳住院,希望四叔能去一趟,到洛阳三院找找熟人。
也许四姐夫认为,派人去告知四叔显得郑重其事一些。
我找到四叔的住处,自我介绍情况,并简短说明来意。
平静的四叔立马变得急躁起来。
四叔从凳子上站起来。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对我说,孩子,因为你姐的病,今天就不和你细聊了,改日我们叔侄再叙,我现在就买票去洛阳。
四叔当晚就赶到了洛阳。
在四叔的全力周旋之下,四姐的病治疗得异常顺利,很快就康复回家了。
那件事情,让我看到了在外多年的四叔内心对于老家亲人饱含的那份真挚而厚重的爱。
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四叔将对老家亲人的那份深爱演绎到了极致。
四叔是我的人生导师。
四叔很健谈,我和四叔几乎无话不谈。
每次去,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们谈到我父亲。
谈到四叔和我父亲当年在县城读完小的情景。
谈到四叔自己早年的经历。
谈到我如何在村子里濒临绝境去当兵,如何阴差阳错来郑州,等等。
在推心置腹的彻谈中,我始终觉得,四叔不仅是我的长辈,更是我别处难寻的人生导师。
我感觉我正行走在四叔曾经行走过的道路上。
我感觉我正在体会四叔曾经深刻体会过的种种感受。
四叔的每句话,于我都是珍贵的经验,迷茫中的指引,颓废中的鞭策,醍醐灌顶般的挽救。
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转折,历来需要一种凤凰涅盘式的艰难跨越。
四叔和我,正是行走在命运这条艰辛道路上,实现这种艰难跨越的两代人。
我和四叔的经历相同,体会相同,对故乡的那份感念和深情相同。
只是我和四叔所处的年代不同,时空不同,脱胎换骨的程度不同。
从偏远、闭塞、贫穷的乡村,走入开阔、文明、发达的城市,这期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的各种感受,只有我和四叔明白,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艰难跨越的人才能真正明白。
我和四叔叔侄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忘年之交。
尽管我不常去看望他老人家但每次通电话,他都会把声音提得又高又亮。
那样充满深情的对话,不仅是对我的一种思想抚慰,更是对老家族人的一种精神支撑。
其实,在我认识四叔的时候,四叔已经退休在家。
作为一名退休干部,在别人看来,他完全可以靠着退休金在家安享晚年。
四叔的心中却时时刻刻装着老家的那些亲人。
那接近蛮荒的乡村里,还生存着他的侄子们和孙子辈,他们在贫困线上煎熬着,挣扎着。
四叔一闭上眼,就能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大人孩子那破烂的衣衫、无奈的表情、干枯的头发、污垢的脸庞,以及四面透风的房屋、坍塌破败的院落。
四叔骨子里的这种对老家亲人生存状态的同情和怜惜,让他不能心安理得地清闲下来,歇息下来。
四叔只有不停地去工作,竭尽全力去挣钱,最大限度地去帮衬和周济老家亲人们的生活,他的心才会得到些许的安慰。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四叔受聘于郑州郊县一家制药企业,开始为期三年的往返奔波生涯。他把自己打工挣得的大部分钱用于老家亲人的衣食住行和看病就医的花销上。
从四叔定居郑州至今,他对于老家人的帮助已经完全超出了他能力的最大限度。
但四叔仍然不遗余力地将这种帮助不断向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扩展,日新月异地向纵深地带延伸。
这种扩展和延伸,让身边的亲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满。
四婶曾经生气地对我说,她甚至不敢再给四叔钱。
四婶说,给四叔的钱,他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花,早晨去河堤上锻炼,他连一碗胡辣汤都不舍得喝,把钱都攒起来给了老家的人。
终于,在四叔又一次偷偷给来郑州上学的光甫叔的孙子塞钱时,闹出了事端。
四叔的儿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爸,你啥时候能对我们也这么好呢。
四叔其实很心疼儿女,但他不担心自己儿女们的生活。
四叔觉得在城里生活的人,永远比老家那些农村人强过百倍。
四婶说,人家并不是过不下去,现在各过一家,你能管到什么时候。
想想也是,这些年农村生活有所改观,并不像早些年那样缺吃少穿。而生活在城市,每一处都需要钱,有时感觉还不如农村。而且作为嫡系亲属,能对兄弟的孩子和孙子们管到啥时候才算尽心?
可四叔对四婶的话十分不满。
四叔说,我自己的钱想怎么给就怎么给。
四叔甚至把自己的工资卡从四婶那里强要过来。
四婶感觉委屈,认为四叔不是个明白人。
家里为此生了场大气。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而且还存在从哪个角度去看的问题。
四婶的话不无道理,但也不能说四叔对老家亲人的那份关爱是一种错误。
四叔酷爱书法,经常练习毛笔字。
国家每遇重大灾难,四叔都会感叹不已。
汶川地震时,四叔决定去捐款。
我知道四叔缺钱,而且知道他心中还牵挂着老家。
我便对四叔说,灾区不缺咱这点钱,还是留着吧。
四叔吵我,孩子,这可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大家能不能在灾难面前共渡难关的大事。
四叔的话令我汗颜。
四叔经验丰富,料事如神,是家族亲人们的精神支撑。
四姐夫得癌症那年,我带着四姐夫先来到四叔家。
四叔对处于惧怕中的四姐夫说了两句关键的话:一是必须解除思想压力,二是必须相信科学。
四姐夫听从四叔的话,那场大病治疗的相当成功。
光甫叔大孙女上幼师毕业,在郑州应聘一家幼儿园当教师。学校待遇很差,还不拿刚毕业的学生当回事。小姑娘很生气,不仅没有和幼儿园打招呼就离开了,而且不知出于某种考虑也没让父母知道自己离职的事情。这急坏了家里人,家长认为小姑娘失踪了,火急火燎地来郑州找。他们找到四叔。四叔对他们说,我相信小姑娘不会出事,你们都放心吧。过了数日,小姑娘主动和家里取得了联系。
四叔对老家人的那份苦心让后代们很感动。
四叔那年患肝炎住院,老家人呼呼啦啦来了一大帮,弄得四婶没法在家做饭,只能到饭店招待他们。
四叔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中乐开了花。
我当时开车从郑汴路的长途汽车站接着四叔二哥的儿子中岳去医院。
中岳五十多岁,包产到户前在老家生产队放羊多年。
中岳留着光头,光秃的头皮被太阳晒得油光发亮。
车到紫荆山立交桥顶端,中岳看着前边一辆挨一辆的车流感觉很稀罕。
中岳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嬉皮笑脸地说:我的娘呀,你看这车,多得像羊一样。
中岳不伦不类又意味深长的话逗得我大笑不止。
到了医院,我向四叔重复了中岳那句话,四叔哈哈大笑。
四叔对着满屋子的老家人,一边笑,一边说,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
200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