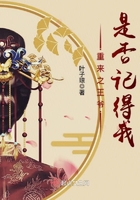逃难的人流仍然源源不断地经过克拉斯诺顿。在正对着公园大门的宽阔街道上,在克拉斯诺顿煤炭联合公司的两层砖砌楼房前,停着一辆卡车。一群男男女女正把公司剩下的最后一批财产从敞开的大门往外搬,装上卡车。
稍微靠旁边一点,就在公司的窗下,站着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谈话,显然,无论是卡车,还是这些大汗淋淋的肮脏的人们,抑或是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比他们的谈话的内容更重要。
“万尼亚,你来了,我真高兴,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歪着头,用闪闪发亮的、不时放出光芒的眼睛望着他说。在他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歪着头的姿势更可爱的东西了。“我还以为我们要走了,再也看不到你了……”
“你可知道,我这几天为什么没有来吗?”他用微哑的男低音问道,一双近视眼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他眼睛里蕴藏着的灵感,好比灰烬里藏着的煤火,马上就会闪光。“不,我想你一切都会明白的……三天前我就该走了。我已经收拾好东西,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想来跟你告别,可是共青团区委会突然把我叫去了。他们刚刚接到撤退的命令,一切都乱了套。你能想象得出吗?伏罗希洛夫学校、高尔基学校、列宁俱乐部、儿童医院——全让我一个人负责!幸亏找到了一个好助手:若拉·阿鲁秋仰茨。你还记得吧?跟我们同个学校的。真是好样的!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我俩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睡过觉,不分白天黑夜地连轴转:找马车啦,找汽车啦,装东西啦,搞饲料啦,这儿车胎爆了,那儿马车又得送到铁匠铺去修理。忙得晕头转向!……不过,我当然知道你还没走。我是听我父亲说的。”他腼腆地笑了笑。
“你知道,我心里真像是一块石头……”她刚想插嘴。
可是他说得正起劲,没有让她说下去:
“说真的,今天我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想,她要走了!再也见不到她了!没想到又冒出一件事。原来有一所保育院还没有撤退。院长就住在我家隔壁,她直接来找我,差点要哭了:‘万尼亚同志,帮帮忙吧。哪怕通过团委搞到交通工具也好。’我说:‘团委已经走了,你去找人民教育处吧。’她说:‘这几天我一直跟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马上可以派车,可是今天早晨我跑去一看,他们自己要走都没有交通工具。等我再四处一跑,回来时连人民教育处也不见了……’我说:‘没有交通工具,它能上哪儿去呢?’她说:‘我不知道,不知怎么就无影无踪了……’人民教育处没影儿了!”万尼亚突然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些人真逗!”他笑着说。“嘿,你能想象吗?我和若拉去搞车,居然一下子弄到了五辆马车!你知道是从哪里搞到的吗?从军人那里。院长跟我们告别的时候,哭得泪水几乎打湿了我们全身。”
“我心里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克拉娃终于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话语,尽量压低声音说,两眼闪耀着热烈的光辉,“我真担心你不会来。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她用柔和迷人的低音说。
这种突然产生的可以跟心爱的姑娘一同撤离的可能,以前从未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而这种可能又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他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望了望姑娘,尴尬地笑了笑。
正巧在这时候,克拉娃的父亲提着两只箱子,满头大汗地从卡车后面走出来。“啊,是万尼亚!你看,变成什么样子啦?”他气愤地摇了摇头。“你怎么样,不走吗?”
克拉娃听到父亲的话,偷偷向万尼亚递了个眼色,甚至拉了拉他的衣袖,自己已经要张口对父亲说什么。但是万尼亚抢了先。
“不,”他说,“我此刻不能走。我还要为沃洛佳·奥西摩兴搞辆马车,他得了阑尾炎,刚动过手术,现在正在家里躺着呢。”
克拉娃的父亲吹了一声口哨。
“你会搞到的!”他讥笑而又痛苦地说。
“再说,还不止我一个人,”万尼亚说,他避开克拉娃的目光,嘴唇却突然发白了,“我有个同学若拉,跟我一起忙乎了好多天。我们约好,办完事一起步行撤离。”
万尼亚说得没留一点退路,他瞅了瞅克拉娃,只见她的深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
“原来如此!”柯瓦辽夫说,他根本没有把万尼亚、若拉以及他们的约定当回事,“那么,暂时告别了。”他刚朝万尼亚迈出步,一阵排炮的响声吓得他哆嗦了一下。他伸出一只汗涔涔的大手跟万尼亚握手。
“你们是去卡缅斯克还是去李哈雅?”万尼亚声音低沉地问。
“去卡缅斯克?德国人马上就要占领卡缅斯克了!”柯瓦辽夫吼叫起来。“我们去李哈雅,只能去李哈雅!我们先去别洛卡里特文斯卡雅,再过顿涅茨河。你们就上那找我们吧……”
可是无论万尼亚办事多么冷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在同学们口中甚至传为美谈,这次他却没能为沃洛佳弄到一辆马车,抑或是在汽车上找到一个座位。若拉劝他,既然搞不到马车,那么就不必到沃洛佳家里去了。但是万尼亚说,他曾答应过人家,应该去把事情解释清楚。
沃洛佳半躺在床上。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绰号叫“响雷”的托里亚·奥尔洛夫,坐在床前的小凳子上。他之所以得了“响雷”的绰号,是因为他无论冬夏总会感冒,咳嗽的声音响亮无比,好像是朝着空木桶咳嗽似的。
“这么说,你根本不能走路吗?”万尼亚问沃洛佳。
“哪儿能走,医生说创口一裂开,肠子都会流出来。”沃洛佳忧郁地说。
他发愁不仅是因为自己走不了,还连累得母亲和妹妹也不能走。
“好,让我看看伤口。”精明能干的若拉说。
托里亚和万尼亚扶住沃洛佳,若拉给他把蓝短裤稍微拉下点,解开绷带。创口已经化脓,而且非常厉害。
“很糟糕,是吗?”若拉皱着眉头说。
“是不妙。”万尼亚表示同意。
他们尽量不看沃洛佳,默默地把伤口重新包扎好。现在他们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他们明知道这个同志有可能遭到危险,却不得不离开他。
房间里笼罩着难堪的沉默。接着,托里亚,就是那个外号叫“响雷”的托里亚·奥尔洛夫,从小凳子上站起来说,如果他的好朋友沃洛佳不能走,那么他也不走,留下来给他做伴。
开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沃洛佳激动得流着眼泪,开始亲吻托里亚,大家也都高兴得不得了。
“太棒了!这才叫同志呢!托里亚真是条好汉!”万尼亚用沙哑的男低音满意地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他突然说,“我和若拉都为你感到骄傲。”他纠正道。于是他紧紧地握住托里亚的手。
“难道我们会无所事事地混下去吗?”沃洛佳目光炯炯有神地说,“托里亚,我们要进行斗争,对不对?区党委不可能不留下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我们要找到他们!难道我们就不能发挥点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