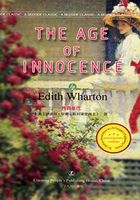万尼亚和若拉跟沃洛佳告别之后,也加入了沿着铁路线向李哈雅移动的难民的行列。他们花了两天两夜的工夫才走到李哈雅。
万尼亚从加入这个难民队伍的那一刻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柯瓦辽夫一家乘坐的那辆汽车。有两种矛盾的心情在他内心挣扎:一方面他已经开始懂得,处境是多么险恶,因此满心希望克拉娃和她的父母不仅早已过了顿涅茨河,而且已经过了顿河才好,但是另一方面,要是他还能在这里遇上克拉娃的话,他会感到非常幸福。
万尼亚和若拉正在逃难队伍里四处寻找从克拉斯诺顿逃出的同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辆马车上有人喊他们的名字。接着,他们的同学奥列格·柯舍沃伊,已经伸出有力的长胳膊拥抱着他们,使劲地吻着他们的嘴唇了。奥列格的脸虽然晒黑了,但仍旧像平时一样干净整齐,他那肩膀宽阔、矫健灵活的体形和长着深金黄色睫毛的、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活力。
他们看到了瓦尔柯和谢夫卓夫乘坐的副一号井的卡车,看到了邬丽亚和奥列格的亲属乘坐的马车,还看到了由于他俩的帮助才得以离开克拉斯诺顿的那所保育院,可是它的院长现在甚至都认不出他们了。
“啊,万尼亚,我们又—又在一起了,真是太—太棒了!”奥列格兴奋地、略微有点口吃地说。他和万尼亚并排跟在瓦尔柯后面走着。“我们又在一起了,真好,我想你想得好苦啊。瞧,你居然还在念诗!嘿,老弟!……”
就像在战场上,担任第二梯队的人很难判断前方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同样,在渡口,如果排在最后一批等候过河的人里面,也很难判断这场灾难的真正规模。越靠近渡口,争相渡河的人们的情形就越混乱,越发不可收拾,人们的积怨也就越深。
管理渡口的军人已经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由于睡眠严重不足,由于从早到晚待在烈日之下,还由于几千双人脚和几千个车轮不断扬起的尘土,他们的脸都晒得黧黑,嗓子叫骂得已经沙哑,眼皮红肿,黝黑的双手汗水淋淋,累得似乎连东西都握不住了。但是他们继续执行这种非人力所能胜任的工作。
奥列格跟同伴们好不容易才挤到岸边,像个孩子一样神情紧张地站在那里,感到既惊讶又失望:只见在一片尘土和炎热中,装满物资的卡车和马车,从坍塌的泥泞不堪的河岸上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车旁边全是人,虽然汗流浃背,浑身尘土,满心怨愤,受尽凌辱,却仍旧往前走着,走着……
突然响起了一声叫喊:
“空袭!”
小伙子们就地卧倒。爆炸声有远有近,震撼着四周的一切,土块和木屑纷纷落下,第一批飞机刚走,紧接着又飞来了第二批,跟着就是第三批。呼啸声、吼叫声、炸弹爆炸声、高射炮和机枪的火力,一时似乎充满了草原和天空之间的整个空间。
等飞机过去了,人们刚开始从地上爬起来,这时从不太远的地方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刹那间,就有炮弹带着巨响在逃难队伍里爆炸开来,掀起了一股一股的尘土和木屑。
刚刚站起来的人们,有的又扑倒在地,有的扭过头去看炮弹爆炸的地方,眼睛却仍旧盯着渡口。看到管理渡口的军人们的脸色和行动,大家明白,一件无法挽回的事发生了。
管理渡口的军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站了一会,似乎在凝神倾听似的。突然,其中一个军人跑进桥头的掩蔽部,另外一个沿着河岸高喊,召集他们的队伍。
不一会,那个军人从掩蔽部里跑了出来,一只胳膊上搭着两件大衣,另外一只手抓着几个背包的背带。接着,这两个军人和警卫班的战士们,也不排队,越过那些重又向浮桥开过去的汽车和在浮桥上开动的汽车,沿着浮桥奔跑起来。
紧接着的事情发生得实在突然,谁也说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一些人大声叫嚷着,跟在守桥的军人后面撒腿就跑。堤坡上的汽车突然乱成一团:有几辆汽车同时涌上浮桥,卡在一起,咔嚓咔嚓地响,把路给堵住了。可是后面的汽车仍旧一辆接一辆地往前开,发动机发出可怕的吼叫声。突然一辆汽车掉到了水里,紧跟着又掉下了一辆,眼看第三辆也要掉下去,幸亏司机使劲一扳,总算把车子刹住了。
万尼亚正惊讶地睁着一双近视眼看着这场车祸,这时忽然大叫一声:
“克拉娃!”
便撒腿向桥头跑去。
不错,险些掉进水里的第三辆汽车正是柯瓦辽夫的车子,柯瓦辽夫本人、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几个人都坐在堆得高高的行李上面。
“克拉娃!”万尼亚又是一声高呼,不知怎么已来到汽车跟前。
车子上的人纷纷往下跳。万尼亚伸手去扶,克拉娃就跳到他身旁。
“这下全完了!……见他妈的鬼!……”柯瓦辽夫这么一说,听得万尼亚心都凉了半截。
克拉娃茫然地斜睨着万尼亚,吓得浑身直哆嗦。万尼亚却不敢握住她的手不放。
“你能走路吗?告诉我,你能走吗?”柯瓦辽夫带着哭腔问妻子。他妻子正用手抚摸着胸口,像鱼儿那样大张着嘴喘气。
“别,别管我们啦……你快跑吧……他们会杀死你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囔着说。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万尼亚问。
“德国人来了!”柯瓦辽夫说。
“你跑吧,快跑吧,别管我们啦!”克拉娃的母亲重复道。
柯瓦辽夫一把抓住万尼亚的手,热泪横流。
“万尼亚!”他含泪说,“救救她们,别扔下她们。你们要是能保住性命,就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那边有我们的亲戚……万尼亚,一切都拜托你了……”
一颗炮弹轰隆一声在桥头旁的车堆里爆炸了。
岸上的人,军人和非军人,都像潮水一般,一声不吭地涌上了浮桥。
柯瓦辽夫放下万尼亚的手,朝着妻子和女儿猛地迈了一步,显然是想跟他们告别,突然又绝望地挥挥双手,就跟着人群在浮桥上奔跑起来。
奥列格在岸上呼喊着万尼亚,可是他一点没有听到。
“走吧,趁别人还没有把我们撞倒,”万尼亚对克拉娃的母亲说,态度严肃而镇静,一面过去挽起她的胳膊,“我们到掩蔽部里躲一躲。听见了吗?克拉娃,你跟着我走,听见了吗?”他严厉而又温柔地说。整个逃难队伍乱作一团,大有土崩瓦解之势;汽车一辆紧接着一辆向前开,发动机发出咆哮,凡是能够冲出去的,都沿着河岸向下游缓缓驶去。
飞机来的时候,玛丽娜舅妈正蹲在火堆旁,把柯里亚舅舅用炮兵短剑砍下来的篱笆条往火里添。邬丽亚挨着她坐在草地上想心事,她的脸上、嘴角旁边和秀气的鼻翼上都流露出了郁闷的神情。后来她又望着坐在卡车踏板上的谢夫卓夫:他刚给那个蓝眼睛的小姑娘喂过牛奶,现在正抱着她,凑着她的耳朵讲故事,逗得她不停地笑。卡车周围还有许多孩子在保育员的照看下做游戏,他们的女院长坐在一旁,显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卡车离篝火大约有三十公尺。保育院的马车、维克多家的马车以及奥列格舅舅的马车,都跟别的马车排列在一起。
空袭来得非常突然,谁也来不及钻进在地上挖的防空壕,纷纷就地卧倒。邬丽亚也扑倒在地,她听到一阵尖啸像旋风般袭来,仿佛越往下声音越响。在同一刹那,一声剧烈的爆炸,像霹雷般在她头上炸响,而且似乎不仅在她头顶上,简直就像在她身上爆炸开来。一阵风呼啸着在她头顶掠过,背上洒了一片泥土。邬丽亚听到发动机在天空中怒吼,接着在稍远的地方又响起这种尖啸声。她一直贴着地面趴着。
她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爬起来的,也记不清她怎么知道应该而且可以站起来。但是当她骤然看清周围的情景,从她的灵魂深处迸发出一声类似野兽般的凄厉的哀号。
在她面前已经看不见副一号井的卡车,也看不见谢夫卓夫和蓝眼睛的小姑娘——他们全都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停卡车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圆窟窿,里面烧黑的泥土都被掀了上来。窟窿周围撒满了烧焦的汽车零件和孩子们支离破碎的尸体。在离邬丽亚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截奇怪的碎块在颤动着,那碎块粘满了泥土,上面还扎着红头巾。邬丽亚方才认出这是保育院女院长的上半身。她的下半截身子和穿在袜子外面的长统胶鞋,却已经统统不见了。
邬丽亚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四周的一切都在奔跑,但是邬丽亚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了。直到奥列格走到她身边,她才恢复知觉。他嘴里对她说着什么,一双大手抚摩着她的头发,似乎想把她搀起来,但她仍旧用双手捂住脸不停地哭。大炮的轰鸣、炮弹的爆炸声以及远处的机枪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但是她对这一切都无所谓了。
突然,她听到奥列格用年轻响亮的声音发抖地说:
“德国人来了……”
这句话,她听进去了。她停止哭泣,挺直了身子。刹那间她认出了站在她身旁的奥列格和所有的同伴:维克多的父亲、柯里亚舅舅、手里抱着孩子的玛丽娜,甚至还认出了给奥列格一家赶车的老头。只是不见了万尼亚和瓦尔柯。
所有这些人都带着异样的表情紧张地注视着一个方向,邬丽亚也朝那边望过去。刚才还围绕着他们的难民队伍,现在连影子都不见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浴满阳光的辽阔的草原,在炽热的天空下闪着暗淡的白光。几辆漆成雨蛙绿色的德国坦克,在阳光灿烂的草原上径直朝他们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