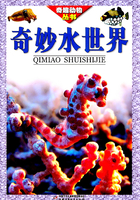当初准备演讲稿时,苏蔚留意到网上有关女性的问题多,男性的问题少。其中一个男生问,我追求一个女孩一个多月了,她并不讨厌我,但对我热乎不起来怎么办?
对于类似“追异性困难重重”的提问,苏蔚统一解释:
大家可能知道心理学经典——温哥华卡皮拉尼吊桥实验,由两位如今已在美国当教授的博士后精心设计。这个实验把男大学生分为两组,一组走过138米长的惊险吊桥,在桥上遇到一位漂亮女子,她交给他们一份带照片的问卷,让他们根据照片写出故事,并给他们她的电话号码,说如果需要请打电话。另一组走过不惊险的普通桥,也同样拿到照片问卷和电话号码。结果,走过惊险吊桥的男生,60%给女孩打了电话,答的问卷跟性有关。走过普通桥的人打电话的不到20%,回答问卷跟性无关。
丹·杜顿和阿瑟·艾郎得出结论,人们处在惊恐中时,会误把恐惧感当成异性造成的性兴奋。另外的实验,让女生走过惊险吊桥,在桥上遇到一位男生,结果类似。
日本大地震后出现结婚潮,再次验证了‘吊桥效应’。人处于恐惧环境中,会对自己的生理反应做出错误的归因,把回避危险的心理需求当成爱情。
对于上述男生的提问,建议他带那位女孩看部惊险影片或者坐过山车。同时提醒大家,一旦处于陌生、惊险、孤独、恐惧的环境中,要尽量排除外界干扰,慎重理性地把握情感。
有时候,惊险活动并不利于追求异性,比如,当被追求者认为追求者很讨厌,在经历恐惧后,他/她会认为对方更讨厌,长得更难看。这是卡皮拉尼吊桥实验后的又一个相关心理学实验。
有位女生,上大学的暑假里独自乘飞机去欧洲旅游。途中遇到恶劣天气,飞机颠簸得厉害,她挺害怕,抓着旁边一位男士的手臂,男士安慰她别怕,一会儿就好。
飞机突然下沉,女生以为要出事,惊慌失措,然而男士镇静地说他天生能化险为夷,跟他在一起就不用怕。不久飞机穿过气流,平稳了。女生松了一口气,望着男士蓝色的眼睛,感觉十分浪漫。随后飞机供应晚餐,两人都点了葡萄酒,像约会似的聊天,仿佛是关系亲密的老朋友。飞机平安到达维也纳,两人结伴旅游,不久成为男女朋友。
后来,女生大学毕业,到别的城市深造,成为一名卓有成绩的医生,而男友一直呆在原居地,没找到安定的工作。周围的人曾对女孩感兴趣,她一直婉言谢绝。几年过去,她动摇了。男友不愿离开原居地,女孩嫌他不思上进,两人总不在一起,最终还是分手了。她后来说,其实跟男友交往期间就觉得跟他不是一类人。她勤奋要强,而男友不求进取、安于现状。两人之所以能交往多年,是因为在飞往维也纳途中的惊恐瞬间里,她爱上了他。
苏蔚换上一张投影,自己当年的维也纳故事在眼前一闪而过。
早上七点半,天已大亮。乔英哲悄悄起床,轻手轻脚刷牙洗脸,做好早饭,开始装车。旅行箱进车以后,又装了一箱饮料和水,最后拿上苹果、橘子。
苏蔚的房间依然静悄悄。
乔英哲吃了饭,洗完锅碗,一看表,八点半了。怎么办,要不要叫醒她?算了,她大概凌晨才睡,反正天黑前到达维也纳就行。
乔英哲想起该拿上相机。这次虽不是旅游,但在维也纳拍张照片的时间还是有的。他忘记相机放哪里了,在客厅里翻找着。
没过多久,卧室有动静。不一会儿,苏蔚穿戴整齐,推门出来,见乔英哲在悠闲地装胶卷,急促地说:“真对不起,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叫我?”
“你大概天亮才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多睡会儿吧。”
“我昨晚影响你了吗?”
“没有,这些天倒时差,睡不踏实。”
“我很快就好。”苏蔚说完,转身进了卫生间。
乔英哲走进厨房,把两片面包放进烤箱,不一会儿端着煮鸡蛋、烤面包出来,见苏蔚把旅行箱放在门厅,对她说:“快吃吧,趁热。”
苏蔚在餐桌边坐下:“真不好意思麻烦你。等有机会,我也给你们做顿饭。”
乔英哲边摆弄相机边聊天,说他的女朋友也喜欢做饭,她叫夏宜,在波士顿读工程。待相机装进包,他便进厨房收拾去了。
苏蔚匆匆地吃着面包、鸡蛋,喝完最后一口牛奶,拿着玻璃杯走进厨房,对正在擦手的乔英哲说:“读工程的女生都是女中豪杰,佩服。”她洗完杯子,乔英哲已经拉起旅行箱先走了。苏蔚锁了门,拎着提包下楼。
车子已停在门口,乔英哲见她走来,忽然想起什么:“等一下,忘了样东西。”
乔英哲提着装三明治的袋子回到车上,苏蔚问:“带这么多吃的东西?”
“开长途就怕路上没吃的。有一次,我从宾西法尼亚的匹茨堡开车到西弗吉尼亚,想省时间,没吃饭就上路,打算路上加油休息时吃饭。结果开出两个多小时,到了目的地也没加油站,没有卖吃的,我差点儿饿晕了。从那以后,只要开长途,我总带吃的,就怕饿着心慌。”
“这种情况西德不会有。无论在哪里,高速公路每两公里就有电话以备应急,每隔50公里就有加油站、吃饭休息的地方。不过,带吃的也好,到奥地利就有用了,那里东西贵。”苏蔚说着系好安全带。
车子出了卡斯弗,苏蔚详细讲解高速公路上常见的德语词,路边有箭头指向,标志距离最近的电话机方向。乔英哲赞扬德国人考虑细节,服务周到。也许正是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才造出奔驰这样高质量的汽车。在波士顿的时候,他读了卡斯弗一位教授写的书,受益匪浅,于是写信希望来做博士后。教授很快回信,同意接受,给的待遇不错,他便放弃波士顿的工作机会,毫不犹豫地来了。现在看来这一步没错,能见识不同的文化。虽然来西德时间短,感触还真不少。
四小时过去,高速公路指示牌一次次预告,慕尼黑就要到了。过了慕尼黑,很快就是奥地利边境。苏蔚说这一段由她来开,边境官通常只问司机几句话,检查护照就放行。
刚换司机不久,前方出现奥地利边境岗楼。车子在岗楼边停下,身穿笔挺制服的女边境官和善地用德语问:“要去哪里?”
“维也纳。”苏蔚一边回答,一边递上她和乔英哲的护照。
“为什么到奥地利?”
苏蔚回答:“旅游观光。”
“待多长时间?”
“三天。”
“以前来过奥地利吗?”
“来过。”
边境官检查了护照,见苏蔚有两个奥地利签证。她把护照还给苏蔚,挥手放行了。
过了境,迎面有加油站,乔英哲说:“先去加油,换我来开吧。”
回到高速公路,很快就要到萨尔茨堡了,乔英哲记得好像是莫扎特故乡,刚想跟苏蔚确认,就听车子嘣嘣响,车身摇晃。乔英哲惊呼:“不好,轮胎爆了。”他慌忙打开紧急灯,在路边慢慢停下。下车一看,果然,车子右前方轮胎破了。车子像瘸了一条腿似的歪着。
苏蔚回到车里找汽车使用手册,乔英哲把后车厢的东西拿出来,掀开底层,搬出备用车轮、千斤顶。苏蔚念着汽车使用说明,不时放下书,帮乔英哲把破车轮换下来,装上备用车轮。
卸车轮、装车轮花费两小时,重新上路时已快到晚饭时间了。乔英哲担心天黑前到不了维也纳。因为备用车轮只能开短途,要到修车铺换轮胎,但愿下一个加油站就有合适的轮胎。
前方出现加油站,两人进去一问,轮胎倒有,可刚才乔英哲一时疏忽,把破轮胎连同轮子一起丢了,合适的轮子没有。没办法,到下一站吧。
高速公路的下一站就要进城了,正是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想省时间也省不了。
在萨尔茨堡的一家修车铺换了车轮,已是晚上八点了。天黑前无论如何赶不到维也纳。乔英哲说服苏蔚,在萨尔茨堡住一晚,天亮起程。
苏蔚本来怕耽误时间,但乔英哲说了,到陌生地方,最好天黑以前到达,黑夜再加路不熟,开车不安全。苏蔚心里也清楚,乔英哲不是李铭钧,如果李铭钧开车带她心急火燎地去找人,她会劝说李铭钧不要在萨尔茨堡停下,直奔维也纳,先赶到再说。一个是相处三年的未婚夫,一个是刚认识的朋友,能相提并论吗?
苏蔚同意在此住一晚。她心里安慰自己,如果半夜赶到维也纳,连李铭钧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很难找到他。倒不如早上九点到,直奔开会的地方,至少能见到他的同事打听消息。于是说,去我住过的学生旅店吧,往前不远,右拐就到了。
这家学生旅店位于萨尔茨堡市郊,价钱便宜。门口登记处的中年女人居然还记得苏蔚,苏蔚跟她说要两个床位,一个在女生宿舍,一个在男生宿舍。
中年女人说:“女生宿舍已经满了,男生宿舍还有一个空位。另外还有一单间,单间的价钱住一个人、两个人都一样。”
苏蔚问:“单间是什么样子?”女人回答:“跟学生宿舍形式一样,两个上下床,可以住四个人。”
苏蔚犹豫,琢磨该怎么办。既然女生宿舍已经满了,她肯定得住单间。而乔英哲或者住男生宿舍,或者也住同一单间。
她问中年女人:“男生宿舍里住几个人?”
“八个。”
住八个人的集体宿舍容易休息不好,苏蔚心想。总有人半夜才回来,进屋说话、吃东西,洗洗刷刷。明天要早起赶路,还是住一起省钱又方便。
于是她跟乔英哲商量,单间住一个人、两个人都一样价,那还不如都住单间,这样乔英哲不必担心男生宿舍里有人打呼噜,就当是两人住男女混住的集体宿舍。苏蔚以前在希腊住过混合宿舍,没什么,都是学生。乔英哲也同意,跟朋友住一间房,当然比跟另外七个陌生人住好啦。
苏蔚告诉中年女人:“我们都住单间吧。”
两人领了折叠整齐的床单、枕套,来到二楼宿舍,打开房门一看,房间挺大,厕所跟洗浴间分开,着实考虑到便于四个人高效率使用卫生间。衣柜有四个门,每个门都带锁,一张长方木桌配有四把椅子,桌面厚实,紧靠窗户。
苏蔚把自己的床单放在上铺说:“我睡上铺吧。”
乔英哲说:“好,我睡下铺。我们算是上下楼了。”
刚才等修车的时候,两人吃了车上带的三明治,算是吃过晚饭了。一整天的奔波,苏蔚感到疲乏,见到床铺就想倒下睡觉。她想早睡早起,明天早些赶到维也纳。她踩着梯子,把上铺的床单铺好。
乔英哲从洗手间出来,手上拿着两个洗好的苹果,递给她一个。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前吃苹果。乔英哲说:“我想开车进城转转。沿刚才的大路一直开,就能进城,是吧?”
苏蔚没立即回答,心想,乔英哲没来过奥地利,一定想看看萨尔茨堡。他专程开车带自己跑了这么远,实在帮了大忙。于是说:“我带你去吧,我认识路。这城市像海德堡,坐缆车上山,能观全景。上次我跟铭钧找缆车口还费了些周折。从这里进城,也就几分钟。”
乔英哲连声答应,三两口吃完苹果。两人关上门,下楼了。
乔英哲开着车,远远望见前方山顶城堡,山下座座教堂尖顶各异,绿水青山衬托,如同渐渐拉近的风景画。不一会儿,车子跨过萨尔茨河。望着墨绿色的河水,苏蔚说这条河途经奥地利和德国,叫盐河。曾用来运输盐,直到后来修建了铁路。
车子来到萨尔茨堡东南的老城,苏蔚又介绍,莫扎特故居在一条小街上,要专门去找。那边还有些商店,现在大概都关了。另外还有拍摄《音乐之声》的地方,你们以后去玩吧。
夏天的萨尔茨堡晚上10到11点才天黑,这时正是傍晚时分,夕阳照在迎面的山顶城堡上,城堡像涂了层金黄色。乔英哲赞叹这依山傍水的景色真美,下次来要住三天。车子在河边停下,两人沿着河边走,湿润的微风吹过,轻拂脸庞,消除旅途疲劳。穿过一条马路,沿着狭窄的小巷朝山脚下缆车口走,没走多远,乔英哲停下,说:“我们回去吧,我以后还会再来。你已经累了。明天要早起,走吧。”
乔英哲说着转身朝车子走,见苏蔚站着没动,又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进城。现在已经看了城区,足够了。”
苏蔚慢慢跟在他身后,望着乔英哲的背影。他走到车子右边,为她开开车门,苏蔚坐进去,他关上车门。以前只有铭钧为她这样开门,第一次坐进去的时候,感到他绅士般细致待人,如今的乔英哲让她更加思念李铭钧。两人都带着温和的微笑,举止斯文。苏蔚眼睛渐渐潮湿。乔英哲有些地方像李铭钧,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有这种下意识的感觉。也许因为两人个头差不多,都学机械工程,专业也一样,流体力学。可是李铭钧不知去向,乔英哲是别人的。空旷的萨尔茨堡,暮色里游荡着的,其实是一个孤魂。
乔英哲进车坐定,刚要发动车子,又停下了,回身拿起后车座上的一盒纸巾,递给苏蔚。苏蔚接过盒子,拽出一张纸巾,擦拭眼睛。两人一路没说话,十分钟后回到旅店。
一进门,苏蔚打开衣箱准备洗漱,乔英哲要到楼下问明天开饭时间。这里房费包早餐。苏蔚明白他有意躲出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于是说:“如果我明天起晚了,一定叫醒我。最好六点半以前上路,九点多就能赶到维也纳。”
乔英哲答应着出门了。
苏蔚洗漱完,到上铺睡下。刚躺下一会儿,乔英哲回来了。他先敲门,而后用钥匙开门,推开一条缝,在门外问:“我能进来吗?”苏蔚说:“进来吧,我好了。”
乔英哲进门先关灯,而后走进洗漱间。不一会儿,他悄悄出来,摸黑上床睡了。
早上五点半,苏蔚醒了,猜想乔英哲还没醒,轻手轻脚从梯子上爬下。见乔英哲闭着眼一动不动,便小心翼翼走进洗手间刷牙洗脸。
其实苏蔚的床一有响声,乔英哲就醒了。只是他闭眼装睡,待苏蔚进了洗手间,他急忙起身穿衣。苏蔚洗漱完毕推门出来,他已衣冠整齐,也要用洗漱间了。
吃过早饭,两人交回钥匙,出门了。苏蔚说出城这一段由她来开,因为有好几条出城公路,去不同方向,到慕尼黑、茵斯布鲁克等等,她可能还记得,一个小时就换司机。乔英哲开长途经验多,能一口气开到维也纳,中间不必再停车。乔英哲答应了。出城高速路线复杂,苏蔚开始紧张,指示牌一个接一个,她有些顾不过来,对乔英哲说:“你帮我看着去维也纳的方向。”
几分钟过去,又有两个指示牌闪过。乔英哲没动静,苏蔚急了,连忙自己察看路标,一看下个路口就要右拐,而自己仍在左线上,慌慌张张打指示灯,还好后面的车及时让开,她仓皇换线,急忙右转弯上了另一条高速公路。上去后再看指示牌,的确没错,是去维也纳。她稍微舒口气,张口就抱怨:“刚才好玄,差点走错路。叫你帮我盯着维也纳,你怎么不吱声?”
乔英哲如梦初醒:“我是一直盯着,不知为什么没看见。我找维也纳Vienna的V,可这么多路标,没一个有V,我想可能维也纳还没出来,再等等看,这一等,就等过了。”
“谁叫你找V?维也纳德语是Wien,你要找W,你怎么不找汉字‘维’呢?”
乔英哲扑哧笑了,他一笑,苏蔚也笑了。两人竟哈哈笑不停,以至于车子压线,乔英哲连忙把手放在方向盘上,谁知苏蔚也有察觉,稍稍转动方向盘,乔英哲没料到苏蔚的手偏移,他的手正放在苏蔚的手上,他连忙移开,两人都不再笑了。
沉静一会儿,苏蔚说,其实都是讲英语的人不好,德语叫Wien,英语跟着叫Wien得了,非别出心裁叫维也纳。
乔英哲道:“叫维也纳就对了,名字好听创出牌子。现在是世界音乐之都。叫Wien的话,译成中文就是‘闻味儿’。‘闻味儿’怎么配得上音乐之都,纯粹移动厕所。”
苏蔚笑出声,车又压线。乔英哲忙说:“前面加油站快下来吧,其实你开车我更紧张。”
苏蔚打指示灯,她要下高速了,在加油站旁停下车,走出车子。乔英哲见她脸上有两道泪痕,心想,她这是笑出泪还是哭出泪?我哪句话不对,惹着她了?
苏蔚坐定,乔英哲开车,重新上路。苏蔚拿着纸巾擦拭眼睛。这话多么熟悉,“其实你开车我更紧张”。
三小时过后,维也纳到了。车子直趋市中心,在离国家歌剧院不远的会议中心找到“机械工程学会”会址。为提高效率,两人分头找,约好不管有没消息,中午12点在一楼大厅碰面。
苏蔚在二楼一间报告厅门外,遇见跟李铭钧同实验室的一位同事。他正随散会人流出来。他告诉苏蔚,刚来时见过李铭钧,这两天没有。还有好些人也都没再见到,会议有好几个场所。今天午饭时间,实验室一行人约定到附近一家餐厅吃饭。下午有人回卡斯弗,其余的人大都明天走,说不定李铭钧会去那里。苏蔚问清餐馆名字,心里点燃希望。
12点钟,苏蔚跟乔英哲在一楼大厅碰头,乔英哲也打听到中午聚餐的事,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一家跟超市紧连的自助餐厅。
正值午饭时间,餐厅人多,苏蔚见到李铭钧的几个同事,大家都说这两天没见到他,待会儿李铭钧的导师来,也许他会有消息。苏蔚和乔英哲各拿一个盘子跟在同事后面排队拿饭。
这家餐厅虽是自助餐,但维也纳酥炸猪排却是现点现做。这道维也纳名吃几乎每个餐馆都有,乔英哲说在波士顿吃过这道菜,猪排薄又硬,没觉得好吃。苏蔚心不在焉地说,那是猪排没做好,在维也纳就不一样了。
头戴白帽的高大厨师给乔英哲盘子里放了一块又厚又大、金黄带红色的猪排,乔英哲觉得看上去跟波士顿的“假冒”维也纳猪排不一样,这个看着好吃。厨师也给苏蔚盘里放了一块刚炸好的猪排。苏蔚的眼睛在朝门口张望,竟没意识到该跟上队伍,乔英哲倒退两步提醒她,她才慌忙拿起盘子跟他去拿菜。
李铭钧的导师来了,他留着络腮胡子,灰白头发,见到正排队的苏蔚和乔英哲,认出他们,朝他们招招手,他排在隔几个人的队尾。
苏蔚和乔英哲端着长方形盘子,跟卡斯弗的七八个人坐在一起。刚坐定,导师也端着盘子走过来了,并在苏蔚旁边坐下。苏蔚说,李铭钧给她写了封信,说要跟学校请长假,还说也给导师写了封信。
导师见苏蔚忐忑不安,安慰道:“我想你不必担心李铭钧的安全问题。从他给我的信上看,他不是被绑架或者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他自愿休学一段时间,处理一些私事,希望我们给他保留位置,他还愿意回来。既然这样,他处理完私事就会回卡斯弗,我们会给他保留位置。”导师和在座的人边吃边聊,把知道的信息一一列出,情况大致是这样:
前天,就是苏蔚接到汉斯带回信的那一天,早晨约七点,李铭钧敲响了汉斯的门,交给他一封信和一提包会议材料、笔记本等跟工作有关的东西,交待了一些工作上的事,说他因私事将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回卡斯弗。大概在同一时间,他在导师的房间里塞了一封信,信中夹着实验室钥匙。导师起床后,到酒店登记处询问,得知李铭钧已退房了。
在这之前的下午,一个学生见到有人到会议报告厅找李铭钧,他出去不一会儿,又回到报告厅,拿上自己的提包走了。那人的样子没看清,是个男的,亚洲人。
苏蔚问导师,除了汉斯和李铭钧,卡斯弗的人都仍在维也纳吗?
导师说,另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罕娜也离开了。她原打算做完报告就走。就是说,她和汉斯都按原计划提前离开维也纳。苏蔚认识罕娜,她是捷克人。
从餐厅出来,苏蔚和乔英哲直奔酒店,找前天早晨登记处值班的人,得知她今晚八点才来上班。两人商量,不管下一步怎么办,都要在此住一晚。乔英哲说,就住这家酒店吧。苏蔚原想到附近找家学生旅店,此刻她犹豫了。乔英哲明白,她嫌这间位于市中心的酒店贵。于是说,我们只住一个晚上,在李铭钧原先住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意外的线索,不必怕贵,仅住一间有两个床铺的标准间,就算你在我房间借宿。我们昨天不就睡在同一房间,你有不方便吗?况且,我一直都在你们家借宿,你借宿一晚不算什么。
苏蔚转身问登记处的人,能否告诉李铭钧住哪间房,如果那间房没人住的话,可不可以住那一间?
登记处的人查了一下,摇头说,你们要有两个床铺,可他那间仅有一张双人床。既然你们已登记,正好那间房还空着,可以叫人领你们进去看看,但是看也没用,房间已经打扫过了。
一位年轻的服务生带他们到六楼,进了李铭钧住过的房间。苏蔚一进门就明白,里面的确已打扫干净,垃圾清除了,一张双人床也换了新床单。苏蔚把所有的抽屉、壁橱都拉开,没找到任何东西。
从李铭钧的房间出来,苏蔚找到打扫房间的清洁工,一位约40岁的黑发女人,苏蔚给她看跟李铭钧的合影,自我介绍说是李铭钧的未婚妻,想询问有关他的情况。那女人点头说记得这个人。有天下午,她正在隔壁房间打扫卫生,听到走廊上有说话声,知道有人回房间。她出来拿床单,刚好见李铭钧正提起地上的提包,边说话边走进屋,她猜测进到屋子里的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苏蔚问。
“不好说,因为没见到另一个人。”
“他们说德语吗?还是说其他语言?”乔英哲问。
那女人想了想说:“不知他们说什么语,但不是德语。”
“他退房以后,房间里有没见到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奇怪的字条、外国包装纸,血迹,甚至……”苏蔚停顿一下说:“特殊场合使用的东西。”女人摇摇头说:“我只记得房间很干净,没什么垃圾,不记得有特殊东西。”
晚上八点,前天早晨登记处值班的人上班了。苏蔚像见到救星,先把跟李铭钧的合影递给她,解释自己是未婚妻,李铭钧没回西德,她很着急,想打听情况。那人拿着照片说记得这个人,因为他看上去很疲倦,付账签字把纸都划破了,似乎很不安。跟他一起退房的还有个女的。
“那女的也住在酒店?是不是罕娜·班尼克娃?”
值班人查了一下说是叫罕娜。她忙于两人的退房,没注意是否有其他人跟他们一起。
离开登记处,苏蔚和乔英哲找到那天值班的门卫。从他那里证实,李铭钧和罕娜都拉着行李同时在门口等车。有一辆黑色中等型号的轿车停在门口,开车的是个亚洲男人,李铭钧上了他的车,坐在司机旁边,罕娜也上去了,坐在后排。
苏蔚希望门卫能详细描述那亚洲男人的长相。门卫说他只见到侧面,而且亚洲人在他眼里都长得差不多,比如,他说着望望乔英哲,又换个角度端详他侧面,“可能就是他这样,或许比他年长一些。”说完,他又觉得不妥:“也不一定,从亚洲人的面孔很难猜测年龄。”
回到房间,已经十二点多了。苏蔚筋疲力尽地在桌边坐下,乔英哲也疲惫不堪,倚在靠门的一张床上。两台比电脑还复杂的机器开始处理所有信息,互相补充,不断修改、剪接,拼凑成这样一幅素描:
李铭钧由于一位亚洲男人的缘故,变得非常缺钱,钱要得急切,他或者跟着这男人弄钱去了,或者罕娜愿帮他,他们都跟罕娜走了。这男人会是谁?如果是李铭钧的亲戚,无非是他的哥哥、堂兄表弟,但他们都在中国,不可能到奥地利。如果是远亲旧友,苏蔚就不得而知了。她想起李铭钧家有“海外关系”。他的母亲有个舅舅,早年在上海做生意,后来去了香港。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的舅舅曾往家乡邮寄饼干、奶粉、猪油,但他从未回过大陆,后来他们失去联系了。这些海外亲戚有可能到奥地利,但苏蔚无从查起,这条线索就断了。还有一条线索就是罕娜,她最可能去的地方是捷克,或者说首都布拉格。
结论一得出,苏蔚忽地从桌边站起来:“我明天去布拉格。”
乔英哲没吱声。苏蔚接着说:“我可以坐火车去,不必麻烦你了。你跟卡斯弗的人明天回去吧。”
乔英哲问道:“你怎么知道罕娜一定回布拉格?”
苏蔚道:“汉斯和罕娜曾经恋爱,不久前吹了。铭钧曾说,罕娜毕业后要回布拉格,而汉斯是德国人,不想去捷克。罕娜对布拉格非常自豪,我跟铭钧就是因为听罕娜讲布拉格如何让人振奋,被她神采飞扬的神情所感染,才决定去那里旅行。罕娜比铭钧早两年到卡斯弗,两人做的课题接近……”
乔英哲又问:“李铭钧跟罕娜有什么不一般吗?”
“没有,也不可能。但是……”苏蔚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说话声音开始颤抖。
“你还记得铭钧给我的信吗?他详细讲了他刚出生算命先生的话。其实这些我早听他说过,他也许以为我忘了,在信上又讲一遍。其实我没忘,事情的结尾我依然记得,不知是不是他有意没提起。那算命先生拿起他母亲给的钱,转身要走的时候又回来,把手里的钱放回到母亲手上:‘还是给这孩子留着吧。’说完他走了。母亲叫回他:‘请给孩子指条路吧。’那男人摇摇头:‘如果是成年以后的事,就跟姓钱的人家结亲吧。’”
乔英哲听了依然不解。
苏蔚说:“罕娜的名字是Hana Banikova,Banikova来自于Banik,意思是银行。”
乔英哲站起身,在屋里踱了一个来回,轻声道:“李铭钧跟着捷克姑娘去布拉格抢银行了?你去布拉格如何找到罕娜?”
苏蔚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李铭钧有可能去布拉格。一年多以前,我们跟卡斯弗的同学一起去野营,汉斯和罕娜也去了。我曾跟罕娜聊天。她祖辈是做生意的,这些年捷克改革,父母承包了酒店。她说,如果我们以后去布拉格,可以住她家的酒店。她家很好找,在查理桥西岸有个店铺,卖纪念品。也许李铭钧为了钱,到她家的酒店工作了?
乔英哲不同意:“到捷克能赚多少钱?要比他的一月两千马克多得多,李铭钧才有可能去。除非……”乔英哲停下不说了。
“不管怎样,最后见到铭钧的只有罕娜。可能只有她见到过那个陌生男人,就冲这,我也要去布拉格。反正捷克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必申请签证。”
“那好,我陪你去。”乔英哲说完打个哈欠,带着倦意说:“不早了,该睡了。”
苏蔚心怀感激。她知道,此刻需要有人商量。如果乔英哲说,他不去捷克,明天跟卡斯弗的人一起回去,苏蔚会失望,现在她很怕孤独。乔英哲毫不犹豫地答应陪她去捷克,让她心里宽慰许多。她望着乔英哲说:“其实从布拉格回卡斯弗,和从维也纳回卡斯弗路程差不多,只是捷克的公路不好。而且明天的路大部分在捷克境内。”
“我不担心公路,就怕看别人开车。”乔英哲说完,微微一笑,样子十分亲切。苏蔚望着他,内心温暖。
“你先去洗漱吧。”乔英哲似乎又精神起来了,他站起身说:“这酒店虽然高级,其实还不如萨尔茨堡的学生旅店方便,厕所和洗澡间分开就好了。我到外面看看夜景,一会儿回来。”说完,他不容苏蔚说什么,拿起钥匙出门了。
苏蔚拿着牙膏牙刷朝洗手间走,见乔英哲脱下的袜子丢在床上,顺手拿起来,进了浴室先洗好袜子,晾在一边,而后开始洗澡。
当她穿着黄色浴衣,头上裹着白色毛巾走出卫生间时,乔英哲已经回来了。抬眼见沐浴出来的苏蔚,洁白的皮肤带着湿润,眉清目秀,神态舒展,他眼睛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欲望。两人视线对撞,他立即收敛,低头拿起睡衣走进卫生间。
苏蔚解开头上的毛巾,脱下浴衣上床,侧面躺下,脸对着墙壁。这样她和乔英哲之间就隔上一堵墙了。不一会儿,听到乔英哲也上床了,不知他的脸冲哪一边。
维也纳的夜晚寂静坦然。乔英哲却睡得不踏实,隐约听到抽泣,声音依稀,不知来自梦里,还是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