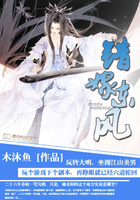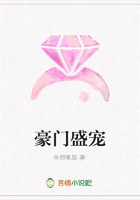韩琳
我在这头——法国鲁昂或者比利时安特卫普,她在那头——古城西安或者海南海滨,或者其他飘远不定的某个神秘地方。我大多宅于家中,她则是游走的行者。
她是唐卡。一个作家。
读过她的一些作品以后我已经深信,她是为写作而生的女子。
她拥有的才情,在诗歌、散文、小说里,挥洒得淋漓尽致。特别当读她那篇有如史诗般的长诗《哭泣的长安》,我惊异于她取之不尽的词汇、无限的想象,更惊异于看似如此安详柔弱的女子,竟有着如此犀利的笔触,把一座城池的古往今来,以诗的韵律吟唱得如此回肠荡气,余味无穷。
她吸引着与她交往的人,以她的才华,她的柔情。
几年前,她突然停顿下来,全身而退。甚至为了退得彻底,还从供职的政府部门悄然离职,归隐于市井。她说,她需要静思,需要反省,需要重新整理,沉淀过后再上路。她是认真的,于是,这才有了我们相逢、相识、相知的可能。
三年前的那个深秋,我回国探望母亲,期间应小妹的好朋友芳的邀请,开车进秦岭赏秋。那是一个有雾霾的日子,红色的小轿车里,挤着四个女人,其中就有唐卡。她刚习琴结束,随约而至。
“作家唐卡”,当芳向我们介绍的时候,因为她坐在副驾的位置,我没有看清她的脸。但她说话的声音别致,有一种磁性的柔婉,娓娓道来,这让陌生的距离感顿时消失。车窗外异常混沌,弥漫着带气味的浮尘,车窗内清爽洁净,洋溢着快乐与轻松。
车在上山的道上缓缓回转,几个女人很快热络起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趣话。话题不断切换,从古琴,聊到人情,聊从前,也聊当下。当聊起如今名利场的百态,唐卡淡淡地说起:一位有些名气的名人出席真人秀,受到追捧,先是被冠以大师,进而又生生提升至骨灰级大师。名人不高兴了:别介,对不起,我还活着,怎么进入骨灰级了!在溢美之词泛滥的当下,该不该较真?她一字一顿,说得平淡,倒平添了些许幽默。于是,我们讨论起可爱的“骨灰级”,到底该不该用,怎么用,这也成了我们一路逗趣的佐料。
到达秦岭山口的那边,下起蒙蒙细雨,我们在半山腰挤进一个小客栈。在一个小单间里,大家围着小火炉就座,啃着热乎乎的大饼,大口品尝着山里人地道的农家菜。话匣子敞得更开,内容翻飞跳跃,好不尽兴。不过是些逸闻趣事,但唐卡的每每表述都让我感觉出她的聪慧睿智,知识渊博。听她说话,有如倾听一股清流小溪的轻唱,时时又能拍激起剔透的浪花,让你的心自然而然跟随着走,很舒坦,也多有收获。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个小女子吸引了,甚至有些相见恨晚。
返回途中,打开车窗,呼吸着被雨水冲刷过的空气,山峦层林尽染,延绵起伏,好个看不够的深秋。脑子里又冒出了“骨灰级”这个多次被当成笑点的词。
秦岭山里的相聚竟这般奇特,难不成会是一次“骨灰级”的友情碰撞?缘分从来都是悄然而至的。大千世界,相遇的人很多,相知毕竟有限,可遇不可求。于是我有了预感,唐卡会距离我越来越近。
果然,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特别回国逗留期间,由于我们都有十足的自由空间。我这个社会边缘人,对其他的社会交往圈子又没有多大兴趣,好多次,竟撇下忙碌于工作的小妹和芳,开始与唐卡单独约会。我们一起去参加文化博览会,去看画展,去美院的湖边散步,去长安大学的操场行走……也去她宽敞温暖的家里,闻藏香的馨香,品她的茶艺,听她弹奏古琴。她自我调侃,京城的四大俗“学古琴,开会馆,修密宗,喝普洱”,她占了三俗。当我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欣赏她养壶、洗杯、沏茶,聆听《阳关三叠》从古琴里缓缓流出,娴熟中的端庄、恬静中的优雅尽显。如果这是俗,俗得大气,我欣赏。
每次相聚,我们都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有说不够的话。渐渐地,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走进对方,关于感情世界,关于个人生活,关于读书写作,也关于出行和修养。我们本来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但我还是被她折服,这大概就在于她的人格魅力。
后来才知道,她的家里,时常接纳着各种各样的朋友。年轻的,年长的。有才艺的,平淡无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她喜爱的写作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她贴近各色人等,感受多样的心灵。自从离职以后,她有了充分的时间,通过多面的观察与交流,积累着更丰富的素材。在她,写作一直是事业。
她告诉我,交流除了积累,更多的是让彼此受益。能感觉到,在开解人心方面,她有春风化雨般的能力,有的朋友居然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让唐卡和他们谈心,做心理辅导。我调侃她的忙碌,你是知心姐姐呀?这浇灌心灵的工程可谓浩大,就算你有老幼通吃的本事,可毕竟劳神耗力!她说,开心快乐的结局有绝对喜感。她还说,至善是她修行的理想。
热心和善良的本能,让她停不下来。
她也确实是一个修行人,虔诚得让我肃然起敬。她用心读佛经,踏实行动。她多次前往西藏拉萨,安营扎寨,去做最朴素的清扫佛殿的义工。
有一段日子,我们间没有了语音交流。正在疑惑,终于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原来,她实践修行中的“止语”。我这个无神论者感觉新鲜,信口问:该不会在闭门思过吧?心底话:现在哪里会有人真正检讨自己呀。没想到,她非常认真地告诉我,“思过”确实是“止语”功课的一部分。这段日子里,她也认认真真回顾自己的所想所言所行,检讨不足和如何修正。她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至诚至真,让我好生惭愧。
现在的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想、我要、我能”。在这个充斥着浮躁和功利的大环境里,何尝不需要那份单纯,沉静下来,理清头绪,自我修养一番,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境界。
唐卡的自律是自觉的,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她曾经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工作的业余时间完成,而她当时的主业,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专业杂志编辑。
即使在离职后没有了朝九晚五的坐班,她心里也有一个时刻表,每天的安排更为严格。为了强化记忆,加深理解,她背诵《论语》《老子》等经典。在拉萨,她除了请教僧人,还和老师常年保持语音互动练习,坚持学习藏文。陶冶情操,修养性情,数年前她开始学琴。从那时起,就没有停下来过。即使每年冬天,移居到南方,在那里也备了古琴,天天习琴。
阅读与写作,是她用心最多的。她的笔不曾停顿,现在只是对作品要求更严苛,创作的范围与形式更广泛。她甚至也尝试了剧本、童话等体裁的写作。她说,她更看重的是过程,坚持去做,让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她就满足了。
我信,一颗安静的心,一种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加上自觉自愿的坚持和勤勉,足以让她的生活充实饱满,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唐卡是我的榜样。我开玩笑对她说,在你面前,突然觉得“鞭策”这个词好有范儿。你就做抽我的鞭子吧。这个感受可能源自于我性格的缺陷,随心所欲,虎头蛇尾。一个人看重别人的那些品质,往往是自己最缺乏的。
唐卡,本是遥远藏地的圣画。而在我心里,是那个温婉端庄、安静娴淑且又充满才情的女子唐卡。
她本身就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我会时常翻阅,滋养我的心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