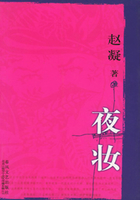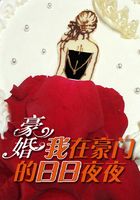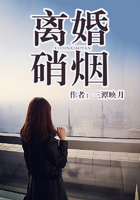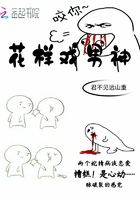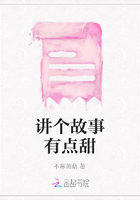1
琅琅的读书声从低矮的土墙传出来。应该是二年级的同学在念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以前伙伴的声音他能听出来,窝在校外墙根下的苏孝华马上接上下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他曾经的同学,住隔壁的苏明教给他的。他们本来是同班的,可现在他再也不能进学校了。
他坐在土墙边的角落,眼睛望着太阳的方向,现在他只有一些光感,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现在很平静,不像刚开始发病、看不见东西时那样焦躁和恐惧了。没有人能救他。这世界没有救世主。当同学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曾经也一样唱得卖力而深情,现在他再也唱不出来了。大救星毛主席也救不了他的眼,能看见五颜六色,美妙世界的他,现在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他平时拿着木棍,摸索着走路,学校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从家到这里的路他以前闭着眼睛都能走到,现在睁着眼也看不到啥。一到上课时间,他就不由自主地来到学校门口。他进不去了,学校对他关上了大门。此刻,那根不离手的木棍,坐在他的屁股底下。他不敢把棍子放在一边,一会儿一放学,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就来戏弄他,抢他的木棍玩,有时候还会故意把棍折断。他们曾经是他的玩伴,他当时还是头儿,玩什么他们都听他的。现在,他们不再当他是伙伴,拿他开玩笑,戏耍他,跟他恶作剧。他们已经不是一样的人了,他是残疾儿童,是个瞎子。
他最不喜欢这个称呼,他想念别人叫他孝华或者小名豆豆的日子。现在那些曾经的同伴不是叫他瞎子,就是喊他倒霉蛋。他本来是全村最可爱英俊最有出息的男娃娃,现在眼睛瞎了的他,还能有啥出息。他拿了个小树枝在地上写字,他熟悉的字。现在只传出老师的说话声,是在上数学课。他听不太清楚,心里一难受,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他听到有脚步声,在他身边停住。太熟悉了,他知道是他爸。爸爸蹲下身子心疼地抱住他肩膀,说:“豆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咱回。”
爸爸这样来找他已经几十次了。他不再哭,不再激烈地怨天尤人,不再对爸爸拳打脚踢。他顺从地站起,拿起他的木棍,拉住爸爸的衣角,慢慢往家的方向走。爸爸走得很慢,说他会想办法给他找个师傅,准备让他学习算卦。孝华答应着,以前小时候经常看到有瞎子来村里给人算卦,很神秘。难道他以后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吗?他想都不敢想。
这一年时间,他从发病到眼睛完全瞎,爸爸情绪无常,常常无端地发脾气。一到晚上,爸爸控制不住的哭声会传到他房间,那粗犷又压抑的哭声很悲凉,像刀子一样刮过孝华幼小的心。他怕伤了爸爸的自尊心,就装作没有听见。在这渭河边的仁厚庄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他似乎理解了爸爸。当然要听他的安排,爸爸是为了他好。孝华眼睛看不见,但心里跟明镜一样。
孝华他妈是最后一批来农村的知青,是上海人,爸爸是返乡知青,都是村里有名的知识分子。孝华有好的遗传基因,长得像他爸爸一样英俊,跟他妈妈一样聪明。他想当初如果不是爸爸先下手为强,凭着当村支部书记的便利,把妈妈肚子搞大,妈妈肯定跟她同伴一同回上海那个大城市了。姐姐不是什么爱情的结晶,随着慢慢长大,出落得倒很漂亮,那股劲儿就像上海囡儿。妈妈一改曾经的厌烦,喜欢上了这个叫英华的女儿。一拨乱反正,政策宽松时,妈妈就把她送到了上海外婆家里,她想用足政策,把姐姐的户口弄成上海的。为什么没有送他去上海,这对幼小的孝华来说一直是个谜。平时怎么看都是父母最爱他,可关键时刻怎么偏离方向呢?其实,他也不想去上海,虽然他一次也没去过,但听别人说就是楼高、人多、汽车多,牛奶糖和点心做得好吃。这个他吃过,舅舅每年会寄上两次。他最喜欢那种甜到心里的牛奶糖,他甚至因为这个都要喜欢上海了。可每次听到妈妈嘀咕那种跟外国话一样的上海话,他就怕得不行。他怕那个陌生、什么都听不懂的地方,他似乎要庆幸他们没送他去。心理暗示太多,他都分不清是不是自我安慰的缘故。姐姐去上海后,妈妈经常找时间回去,她也想留在那个大城市。虽然她每次回来都抱怨,说别人嘲笑她,说她土,说她是乡下人,说她不符合政策。骂归骂,她还是想念她的上海,有好几次对后来有点感情的丈夫苏红卫说,如果不是有了豆豆,她胡枫芸肯定会赖在上海,哪怕卖茶水、卖茶叶蛋、捡破烂儿呢。
不管老婆咋发威,大男子汉苏红卫大气不敢出,他其实一直都惹不起老婆。是他干了缺德事,把人家城里命的胡枫芸硬拖到了跟泥土打交道的农村。他欠老婆的,是他理亏。孝华三岁时,看着爸爸窝囊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他想以后自己要给爸爸光宗耀祖,给他长脸。他爸爸本来就爱他,因为他总是站在爸爸这边,没有像从小就会看眼色的丫丫英华那样,喜欢她妈妈身上的上海味儿。她就喜欢妈妈用烫红的铁钳子给她卷个头发,给衣服上弄个花边啥的。苏红卫看着爱美的女儿,想起他和胡枫芸给孩子起名字的寓意:英姿飒爽地走在中华大地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多希望女儿有光明的未来。对于孝华,他妈妈并没有表现更多的爱,她的心思在女儿身上。但他爸爸,对他可了不得地好。在关中,自古以来都重男轻女,男娃才是家族的正主,所以苏红卫想更多地培养儿子。最初他希望老婆能送儿子去上海,为此,他和胡枫芸吵过几次,老婆坚持送女儿,他拗不过她。上海是人家的地盘,他没有发言权。后来豆豆长大些,聪明、懂事、善解人意,他舍不得豆豆了,别说上海,就是美国他也不让送去。他很怕以后他把握不住,在那个陌生的上海,孝华会长着长着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儿子呀,那可是他的命根子。
胡枫芸后来有次去上海,几个月都不回来。她现在更多的心思是想法子留在上海。给苏红卫说是她在上海站稳脚跟,再接他们爷儿俩。苏红卫知道这是稳住他的话,天各一方,这话哪有个准儿。何况她在那个城市也不容易,弟弟一家都不欢迎她。虽说她娘家妈手心手背都是肉,心疼她,希望她能留在上海,可是不大的两个屋子挤着一大家子,她和女儿在老娘的屋子搭了个临时铺,吃饭喝水都要看弟媳妇的脸色。她这年龄,复习功课考大学已经不可能,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想在上海立足,她只能找份工作干。上海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方,没有了上海户口,她就像个乡下人一样四处碰壁。她一烦,就买张火车票回到渭河边的仁厚庄。可是看惯了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她再也受不了乡下的萧瑟和苍凉。以前和她一个被窝的苏红卫,她也嫌他脏,每天她都搂着儿子睡觉。即使这样她也忍受不了几天,她思念她的上海,思念那片灯红酒绿的繁华。几次来来去去,她更是打定主意留在上海。她中学的好姐妹嫁了个好丈夫,有海外关系,父母和姐姐都在美国。人家工作好,在区政府坐办公室,丈夫跟她在一个大楼上班,是人事局局长。胡枫芸厚着脸皮找她同学,好在同学还算热情,没有势利眼,给丈夫说了她的情况。她丈夫也是个热心人,立即承诺着手办英华的户口,还给她找了份临时工。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在区政府收发报纸,工资不算高,但还算清闲,最重要的是她能接触到领导。
胡枫芸虽然是有两个孩子的女人,在农村也待了近十年,但她身材苗条,漂亮又会打扮,很有些风韵。不到半年区上一个丧偶的副区长就看上了她。五十多岁的男人,也不用绕什么弯子,有一天让司机接了胡枫芸到他家。他很直截了当,说看上她了,要娶她。胡枫芸刚开始吓了一跳,特别是他没有铺垫地对她动手动脚,她狠狠地推开,摔门走了。又有了第二次。这次她半推半就,羞涩地接受了这个男人。副区长说要娶她,尽快。她没有给他说她结婚的事,只说她是知青,户口留在了陕西。副区长啥不明白,严肃地点点头,只是说让她尽快处理好乡下的事情。还给她承诺结了婚,她的户口他出面来办。胡枫芸现在是户口高于一切,她不敢耽误时间,请了假立刻坐火车赶回仁厚庄。
2
胡枫芸回到村子的时候,孝华眼睛已经出了问题。苏红卫前几天刚带他到西安儿童医院和第四医院看了,说他得了双眼黄斑变性,这病一发现就是晚期,治不好。
胡枫芸吓傻了。
其实,孝华的眼病几乎没有什么预兆。不久前,他感到眼睛不舒服,看东西模糊,有时候还会有黑影。胡枫芸那会儿在上海,孝华没敢给他爸爸说。他最近因为妈妈不回来,已经很烦了。特别是村上换了村干部,说他是造反派的人,没有提前通知就免了他村支部书记的职。在村里一贯受人尊重的他,突然成了和别人一样的普通农民,他不能接受。而他引以自豪的老婆长久地待在上海,好议论的乡亲早从私下嘀咕变成当面开他玩笑了。他脾气一天天暴躁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关心儿子。孝华上了小学,学习不用他操心,第一学期就拿了全班第一,第二学期又是第一。他想儿子将是他的希望,现在是凭本事吃饭的年代,再也不是以前的唯成分论。儿子这样学下去,肯定能考上大学。孝华上了二年级,他妈还从上海寄来了漂亮的书包和新衣服。孝华高兴坏了。他给同学显摆,还说他以后也要像姐姐一样去上海。上海老大老大,比西安城还大。伙伴们羡慕他有个上海妈妈,羡慕那个老大老大繁华的城市等着他。他总是不喜欢他们弄脏他漂亮的彩色皮球,他不让他们玩,一个人偷偷在自己家院子里拍皮球。每当他拍皮球时,他家低矮的土墙上就会爬好多小孩,直勾勾地看他,有的甚至羡慕得掉口水。还有妈妈寄来的大白兔牛奶糖,使他奠定了同学中的领导地位。不管玩什么,玩打仗、玩斗鸡、玩滚铁环,他从来都是头儿。所有的伙伴,都听他的,以他为中心。
孝华因此自信满满。直到有一天他眼睛不舒服,看啥东西好像都有些变形,不那么清楚,他还没当回事。他从小就没得过啥病,想着很快就会好的。即使左眼疼、干涩的时候,他还是没给谁说。就要期中考试了,他不愿意面对眼睛不对劲这个现实,而且再有一学期他就要上三年级了,妈妈还说等他上了三年级就带他去上海上学。他渴望那一天的到来。
可突然一天下午,他什么都看不到了。桌上他的书,地上他家装粮食的木柜、窗户、门、树、天空,什么都看不见。他爸爸不在家,他吓哭了,瘫坐在青砖铺的地上。哭了,眼泪都哭干了,依旧是一片黑,看不见。他爸爸最近迷上了打牌,常常到那个光棍六六家去打。一打就是一天,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孝华哭饿了,起身,摸索着到厨房,找到馍笼子。在他拿到馍馍的时候,一下子碰翻了笼子。馍馍咕噜噜滚了一地。他又摸索着拾地上的馍,拾到一个,用嘴吹吹灰,再放进笼子里。
等苏红卫回到家,看到儿子在炕上睡着,没有开灯。他拉亮电灯。孝华并没看他,睁着大眼盯着天花板。他叫了一声。孝华转过头,对他笑了一下。他奇怪他为啥跟不对眼光。他没有想太多,随便到厨房拿了个凉馍,夹了辣子吃了,困得顾不上刷牙,上了炕,一倒头就呼噜声大作。
孝华没有睡着,他睁着看不见东西的大眼睛,清醒地躺在爸爸身边。
第二天早上,苏红卫发现儿子很奇怪,下炕慢慢地,也不看门、不看地,摸索着走路。他忙拉住儿子。孝华声音小小地说他看不见,夜个就看不见了。他生怕吓坏爸爸。苏红卫急急地吼儿子,拍了他一巴掌,说得了这么大的病都不说一声。孝华低下头,不再说话。
急红了眼的苏红卫拿了他攒下的所有钱,简单收拾了些行李,立即带他去省城西安。西安,他没去过几次。还好,热心人很多,有人给他介绍西安看眼睛最好的医院。他们折腾了整整三天,儿童医院和第四医院都说孝华得了个难治的眼病,叫黄斑变性。病是晚期,视网膜下出现了新生血管。没有办法手术,用激光治也不行。发现得太晚了,而且他得的是急性的,这种急性一般一发现就是晚期。几个医生都这样说。他们的话像是商量过的,说的几乎一样。平静的语气透着残酷的现实。
一想到不到八岁的儿子以后要成为瞎子,他在第四医院让儿子排队等大夫点眼药时,自己偷偷躲进厕所哇哇大哭起来。再也治不好了,他娃以后咋办呀,咋给他妈交代呀。
他没敢给老婆写信,他怕她那急脾气。
没想到老婆这个时间回来,既不过节,也不过年。当她看到儿子摸索地扑向她,确定他眼睛瞎了的时候,哇哇哭着瘫倒在地上。她慢慢平静下来,没有提离婚的事,而是数自己包里的钱,立即决定再去西安给儿子看病。他们带着孝华在西安城,跑遍了所有的医院,包括部队医院,不管做啥检查,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一个答案——没治了。他们没有回仁厚庄,而是直接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她把他爷儿俩安排在家附近的旅馆,没有带他们去她娘家,她嫌丢人。她现在还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瞎子的现实。她妈妈过来看了一次,象征性地关心了一下孝华,没再对他说什么话。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外孙,她没有什么感情。她也不正眼看女婿苏红卫。苏红卫在她面前胆怯得更像个憋屈的乡下人了。她只跟自己女儿胡枫芸说话,叽里咕噜的上海话让孝华感觉很陌生,仿佛自己处在外国,浑身都不自在。他姐姐英华,静悄悄地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只是哭,但她矜持地并没有抱他。舅舅他们都没有来,他们大概早已厌烦他们全家了。
胡枫芸带着他们去了几家有名的眼科医院,医生都摇头。最后他们再次去了最权威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遗憾地说太晚了,目前根本没有办法治。
二十天,让他们全家丧失了全部的信心。花光了所有的钱,也没有地方可以看儿子的病,苏红卫没有理由待在上海,他的儿子孝华也是。
这次胡枫芸主动陪他们回到仁厚庄。苏红卫想大概儿子生病老婆动了恻隐之心吧。没想到回家的当天夜里,她就跟他提出离婚的事。他们争吵得很厉害,两个人都说了刺伤对方的狠话。胡枫芸埋怨苏红卫耽误了孝华的病,如果他关心儿子,儿子咋会耽误呢。苏红卫也不示弱,骂胡枫芸,说她到大城市光顾享受去了,不管这个家。从争吵到谩骂,步步升级。
孝华瑟缩在隔壁屋子的土坑一角,嘤嘤地哭泣发抖。他听见他们好像打起来,爸爸高大壮实的身材动起手可了得。一直以来,苏红卫在家里都是妻管严,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乡下人的他在老婆面前从来都是唯唯诺诺。婚后他第一次施展男人的威力,竟是他要失去她的时候。他不能容忍她的离开。胡枫芸哭得死去活来,伤心欲绝。她凄惨的哭声让孝华难受不安。几天几夜,一家三口都无法入睡。
一连七天无休止的吵闹,夫妻俩终于疲惫了,但谁也不让步。孝华悄悄拉了爸爸的衣服来到院子里,劝他放了妈妈。他说妈妈也不容易,她不喜欢这乡下,留住人,也留不住她的心。苏红卫没想到八岁的儿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抱住儿子,答应了他的要求。
胡枫芸离开那天,除了汽车、火车票钱,她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苏红卫父子。苏红卫没有送她,一大早去给自家的自留地浇地了。胡枫芸知道他是不想面对她,她爱怜地抚摸着孝华的头、眼睛、脸和手,哭着说以后一定会把他接到上海。她要让他在上海受教育。不管妈妈说啥,孝华都不说话。不知是什么心理,此刻的他就是不相信她说的。他固执地认为,她会一去不复返的。他不哭,也不流露什么感情,他任这个跟他有着紧密血缘的女人的感情恣意地展现。
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要学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本事。
3
棉衣换成单衣后不长时间的一天上午,孝华被父亲早早叫起,给他换了新衣服。爸爸笑着说是那个女人从上海买来的。爸爸能笑,孝华也笑了,他爸都生气半年多了,一直以来都气鼓鼓的,像个吹胀的猪尿泡。
孝华一天天明白懂得了些事情,他现在不去学校的墙角下可怜巴巴地待着了,像个等着别人施舍和怜悯的儿童。他知道他即使想学什么,再也不可能像他的同学那样了。他是没有视力的残疾人,是个瞎子,就该接受这个现实。爸爸前几天就说要带他去见师父,今天终于要去了。他很兴奋,看不见东西的眼睛都流露出笑来。
拐杖、墨镜,是孝华的必备道具。在农村哪有墨镜,那是上次在上海他妈给他买的,说睁着看不见东西的大眼睛怪吓人的。在荒凉的渭河之滨的小村庄,他的墨镜是一种时髦。戴着墨镜的他看上去神秘而有趣,谁也摸不清他的心思。这是他的好朋友说的。
孝华拉着爸爸的衣服,紧挨着他走着。爸爸不时提醒他:有个水坑,有牛粪,向右拐,向左有个大石头,等等。对面有人,往往会躲过他们走。村上人已经习惯孝华的瞎了,除了见了面还会说这可怜的娃呀,基本上没有过多的关注。
看着他们父子,几个蹲在村口吃饭的女人跟苏红卫打招呼,苏红卫简单地回应。倒是孝华大大方方地说:“婶,姨,你们好。”有个中年女人忙说:“豆豆好,要想开,哦,我娃。”等他们刚走过,有个女人尽量小声地嘀咕道:“唉,这年月,有啥都不要有病,没啥都不要没钱。屋里一个人得病,全家就都撂到沟里,翻不起身了。”
“就是,就是。你看红卫家,豆豆眼一瞎,她妈都不回来,不要这家了。红卫头发都急白了。”
苞谷糁呼噜吸进嘴里的声音后,又一个女人说:“这娃是个能豆,聪明得很,可惜了,可惜了。一辈子就这样毁了。”
声音逐渐小了,听不清她们还在说啥。从最初悲凉情绪中走出的孝华比以前开朗多了,他没有过多悲伤。现在没有什么能打击他了。眼睛瞎了,还有啥能比这严重的。他轻描淡写地用胳膊轻轻撞了下他爸,说:“爸,你真头发白了?”苏红卫用手抚摸了下他的脑袋:“白了一点,我也老了嘛。”“你哪儿老,你才三十几岁呢。”
苏红卫爱怜地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说:“不要操心我了。你这小脑子,不知道都装了些啥。唉,如果不是眼睛,可能以后都能当科学家。”
孝华嘿嘿笑着,狠劲点头:“就是。不过我现在目标变了。说不定以后你要以我为荣呢。不像现在,到处的人都可怜咱。”
“好,好。有志向。”苏红卫虽然这样夸奖,但实在是底气不足,他不知道一个瞎子能做出啥大事来。在他看来,只要娃能挣点钱养活自己就行了。在凭力气吃饭的农村,看不见啥真是寸步难行。
骊山脚下有个古老的村子,村子有个神算,姓李,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人们称呼他李神仙,也叫他神算李。李神仙总爱闭着眼,但他不是个盲人,眼睛好着呢,故意不看这乱糟糟的世界。他想看时,眼就睁开一下,但很快又闭上,好像觉得睁着眼很费事一样。他很老了,满脸沟沟坎坎的皱纹。没人知道他年龄,谁也说不清。白胡子脏兮兮地飘在下巴下,没有一根黑发的头发用褐色的麻绳绑了个发髻,在头顶上顶着。常年一身粗布黑褂子,冬天不换棉衣,夏天也不换薄的衣服。好像天热天冷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结过婚,没家人,没有娃,没有亲戚,孤家寡人一个。谁似乎都了解他,也不了解他。都知道他可能是外来户,但不知道啥年代起他开始在这胡姓的村子里。他一直住在一个没有围墙的房子里,两间大的屋子,干啥都在里面。后来是两邻修院子,他就有了个窄窄的院子,没有门,他也不修门。
听说解放前他就能掐会算,很有名气,在县城混得不错。解放了,人人都要革命了,没有人再相信算命卜卦看风水的把戏。奇怪的是李神仙在“大跃进”的时候,突然疯了,成天光着身子,在街上又唱又跳,有时候都疯到半山上那个山缝缝去了。他索性在那里住着,想回来时,他就回来,自由得没人能管。想来,谁会跟一个疯子较真。当时驻村的县上干部本来和村里先进骨干分子合计把李神仙弄成反革命,没想到他疯了,只好临时抓了个小学教师顶事。
李神仙这一疯就是二十年。那二十年他是咋活的,没有人知道。谁也顾不上关心一个疯子。反正疯子精神得很,没见他有病有灾的。直到“文革”结束,开始包产到户,他突然不疯了,去参加生产队分自留地的社员大会。他再也不脱衣服光身子乱跑了,蓬乱的白发扎了起来绾了个髻。有了地的他,每天都到他的地里干半天活,下午就到离村几百米的街上摆摊算卦。不到一年时间,他的名气就又回到了解放前。后来他嫌麻烦,不上街去了。他似乎也不需要钱,他以前挣的钱,谁要他都给,不记账,也不让人还,他只求温饱就行了。找他卜卦的人越来越多,有西安的大官开着红旗车、进口车来找他算前程;有家长领着娃娃算学业高考的;有人请他去看阴宅风水的。都说他算得准,反正他窄小的院子总有等的人。他不急不慢,按部就班地按他的习惯生活来,别人放下来的点心水果他都散给到他这里玩耍的娃娃。有些吃食,他会让娃娃们给村头那个瞎子送去。那瞎子没有亲人,陪伴他的是把一碰都要破的二胡,他的小屋子常常传出凄凉的音乐。李神仙不去他那儿,他不跟俗人交朋友,他怕麻烦。
有人想知道他为啥能掐会算,趁他下地里时偷偷进到他没有锁的屋子里。啥神秘书都没有。村里有好事的年轻人也想学他这个手艺寻思以后挣大钱。碰着这样的人,他就打马虎眼,说自己那一套是骗人的,没有啥好学,他不收徒弟。
然而不管他咋说,他的名声大得快响到北京了。经常有外地的人慕名拜访。人特别多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躲起来,一个人大晚上爬上骊山,住到道观去了。道观有上千年的历史,“文革”时遭破坏了。道士们作鸟兽散。只有那个老道士躲到骊山深处的山洞修道去了,直到前年恢复这千年道观,他才出山了。没有人知道李神仙和现在的道长的交情从何时开始,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认识而且关系不浅。所以,他一上山,就有人怀疑他和那个跟他一样年老的道长切磋技艺去了。他在山上住上一阵子,就又下山,去过那红尘滚滚烟雾腾腾的生活。在这俗世,他没有朋友,不跟人说闲话,他的话都是充满神秘的。他往往不把话说透,满是玄机的几句话,让人佩服得直点头。
这个神秘的李神仙越传越神了,苏红卫就是听村里乡里好多人说过他而打算让儿子跟他学的。但是知道李神仙的逸闻趣事越多,特别是听说他不收徒弟,对来找他、让他收孝华到门下,苏红卫就越是没有把握。虽然他给孝华说,这次带他见师父。这会不会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苏红卫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
苏红卫父子俩倒了三次汽车,几乎到黄昏才到了骊山脚下李神仙住的老村子。
在华清池旁边他们找了个便宜的旅舍,把孝华安顿在屋子里。苏红卫就到村子打听李神仙的住处。
这么大的名声,三岁的娃都知道李神仙。他就是被一群娃娃领去的。
天已麻麻黑,李神仙破旧的门框上挂了个小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一个字:歇。
一个跟孝华大小差不多的男娃对他说:“神仙睡觉了,今儿来的人多,他累了。”
“那啥时间他开门?”苏红卫不知道该用啥词问神仙的作息时间。
“你明个后晌早早来,他肯定在,而且不会睡觉。”另外一个男娃给他扮了个鬼脸。
苏红卫提着苹果和橘子罐头回到旅馆。他给孝华说没见到神仙,打算明天直接带孝华去。孝华静静地躺在床上,“哦”了一声。
之后,他们父子俩没有说一句话,各怀心事地躺着。
在陌生的木板床上,孝华像按了开关一样很快进入了梦乡。
4
苹果和橘子罐头苏红卫一直不离手,即使他坐在李神仙小院子的砖头上时。孝华紧挨着坐在他旁边。他们前面有八个人在排队,后面没有一个人。那是因为苏红卫总是把后面的人让到前面。他知道他们比别人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当着别人的面也不好开口。
李神仙的门口还是挂着木板,上面有另外一个字:算。苏红卫想这李神仙也真有意思,处处表现得这么神秘。排队的人对李神仙都很好奇,一有人出来,就忙问:“算得准不?”从里面出来的人跟商量好了一样,都说准。
孝华很安静,他仔细用耳朵辨别分析周围的情况。说也奇怪,自从没有视力以后,他耳朵变得分外地灵。他凭着说话人的语气语速停顿的地方,揣摩人的表情和心理。因为不能看,他甚至感受到了更丰富的世界,一个奇妙的声音的世界。而且他习惯了思考,习惯了想象,习惯了想自己的心事。
此刻,在这等待中,他突然想起他一去不复返的妈妈。他从来没有像爸爸那样埋怨妈妈,他甚至理解她。她想过好的、轻松的、多彩的生活,有啥不对?为啥人都得在一个尘土飞扬、贫穷的地方窝着。现在广播成天喊实现四个现代化,守着穷日子咋实现,谁也没办法。
奇怪得很,眼瞎了以后,他变了。他有了些奇怪的想法,变得好像懂得了好多东西,一下子明白了这纷杂的世界。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晚上奇怪的梦。
有条很大的白龙呼啦地穿过窗户,来到他炕上。他从没见过龙,但看到那样子、那架势,他就认为那是威武的龙。那天,他妈妈还在。他们在吵。白龙睁着铜铃一样的大眼对他的脸吐芯子。奇怪,他能清晰地看见龙,它是彩色的。一股白气进到他头里,一股黑气从他胸口冲了出去。他紧张得很,翻动身子,在咳嗽中醒来。他兴奋极了,忘记自己没有了视力,还往四处看,可是啥也看不到。用手把炕摸了遍,也没有龙的影子。但奇妙的是,他突然觉得身体一阵轻松,脑子也充满了很多奇怪的想法。
他没有给任何人说过这个梦,对他的好朋友苏明没有,对他爸爸也没有。
龙好像驻扎在他身体里,给他装进去了知识和精力。除了看不见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没有不如人的地方了。他还记得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好像有什么寓意一样。“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真奇怪,这是哪里的话,怎么会蹦在自己脑子里。蹇,这复杂的字,他都没学过,现在他会念了,可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好多好多整段整段的话、诗文在脑子里,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神龙赋予他的?他不敢给爸爸说,说了他也不信。
在李神仙窄小的院子里,跟焦急等待苏红卫的不安相比,孝华是如此安静。大概是神灵给了他某种力量吧。
前面有人对孝华好奇,问他这问他那,苏红卫只是简单地回答他们,他不愿意细说。他认为现在的人,都盼着你过得差呢。他渭河北生硬的口音引来那些人的嘲笑。他们或者讲普通话,或者说轻巧的西安话。孝华根本不说话。不说话的人让人捉摸不透,还显得神秘。有人甚至嘀咕,这娃是不是哑巴。孝华依旧不言语。
终于轮到他们了。
来的人都把鞋脱在屋外,里面高出一个台阶,起了个大台子,整个屋子里就是一个大炕。李神仙盘腿坐在暗处,隔了一个小小的矮矮的只有一个搪瓷缸子的茶几,苏红卫和儿子站在对面的麻布垫子上。
苏红卫递上罐头,李神仙看都不看,随手往地上一放。苏红卫发现地上堆满了东西,有他这样的罐头,有点心,有北方稀罕的香蕉和叫不上名字的水果。苏红卫心跳得怦怦的,结结巴巴地说着。李神仙瞟了他一眼,示意他们坐下说。
“李神仙,我,我……”苏红卫吞吞吐吐,总怕一说出,就遭拒绝,所以不敢说。
“不要叫我神仙,我就是比你活得长。话说直接些,有啥为难的。”李神仙说的是地道的西安话,轻飘飘的,真有些神仙的味道。奇怪这李神仙在骊山下,咋没有这里的口音。
苏红卫注意到李神仙一直不经意地瞟孝华,看看又闭上眼睛。他用手捋捋胡子,若有所思地摇头和点头。
“我想让我儿子跟你学。”这回苏红卫直接得没有了委婉的礼节。
李神仙揉揉眼睛,面无表情地说:“我不收徒弟。”
苏红卫赶快收起盘着的腿,直直地跪着,急切地说:“李神仙,我儿子你看到了,他是瞎子,不学点啥,以后没办法活。”
“水有水的路,花有花的道。是人都能活下去。”李神仙依旧双眼微闭,不动声色。
“我娃可聪明了,学习都是一百分。如果不是这眼,他出息大了。”
“现在娃娃都聪明,没有笨的。”
“他需要你,我来之前就给他说去见师父。”苏红卫都快急哭了,好像他自己夸下的海口必须让人兑现一样。
李神仙抬眼看了一下不做一声的孝华,表情没有变化,摇头:“那是你的事。我还是那句话,不收徒弟。”
李神仙说完,从旁边随手拿起个苹果递给孝华。孝华乖巧地说:“谢谢,师父。”
“这娃,我不是你师父。”李神仙脸上有了些表情,笑了。
“你就是我师父。”孝华好像比他爸还固执,声音虽小,但字字清楚有力量。他胳膊肘轻轻动了下他爸,小声道:“爸,你先出去。我跟师父有话说。”
苏红卫鼻子哼了一下,转身出去了。
只剩下老少两人。李神仙眼睛睁着看这个小小的盲童。他在想这个奇怪的孩子真的有些特殊。
孝华站起身,表情严肃,童声款款而道:“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李神仙眼睛瞪得溜圆,惊讶地问:“娃,你这跟谁学的?”
孝华缓缓摇头:“没有人教我。一天夜里,梦见龙飞到我炕上以后,就记得很多奇怪的话。还有呢: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孝华说得虽不快,但叽里呱啦的,没有停顿。
“停。娃呀,这是神书。真没有人教过你?”李神仙的语气里透着喜悦。
孝华还是摇头:“神仙,真没有。我都不懂啥意思。东一句西一句的,没头没脑。”
李神仙满意地捋着胡子,缓缓地说:“好,我教你。我这辈子就收你这个徒弟。”
孝华很高兴,立即给李神仙磕了三个响头。
苏红卫在外面焦急地等。不一会儿,门开了。儿子探出头,叫他进去。这回是李神仙没有铺垫,说他要收这个徒弟。苏红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神仙和儿子都不给他解释原因。李神仙说娃以后就跟着他,要求苏红卫每个月送来二十斤面,说是学费。苏红卫满口答应。李神仙还说人家孔子收弟子都让拿一捆干肉,肉就算了。说完哈哈笑起来。苏红卫也笑了,他儿子孝华大墨镜下的小脸蛋也露出了笑来。
他终于有师父了。孝华心里喜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