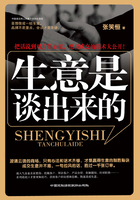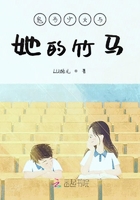1978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次招生。非常荣幸,我能出人头地。此前,我在工厂做工人。虽然考上了大学,实现了理想,可是,进入黄瓜园之后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好像除了画画技法上的那一点事情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和我的同时代的学子一样,经历了成长时期无书可读的阶段,加上我来自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之上,就更在情理之中。
开学典礼上,见到了许多仰慕已久的老师,其情形至今历历在目。但是,没有见到刘海粟院长(他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恢复院长职务)。那时候,刘老基本上都住在上海,不怎么来南京。有关刘老的事迹以及学问和艺术,绝大多数都是从我后来的导师温肇桐教授那里得知。温肇桐教授,江苏常熟人,他在到上海美专教书之前只是常熟虞山镇石梅小学的图画老师,但是,他非常刻苦,在教小学图画课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学美术教育法》的书。说是书,其实只有几十页,几千字,好像比32开还小,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值得一提。温先生寄了一本给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老。刘校长看后,大加赞赏,认为开天辟地,居然还有人研究小学美术教育法。因此,决定聘温先生任上海美专教授。话说得很清楚,私立学校薪水很低,温先生还是接受了邀请,从此离开常熟到了上海。这是他日后与刘校长建立长久友谊的基础。
因为一本书而起用小学美术老师任上海美专的教授,可以看出刘校长的知人善任和不拘一格,也可以看出上海美专当年的教育思想已经是一个开放的格局,除了技法的训练还关注到审美教育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温先生又随刘校长到了无锡的华东艺专,接着又到了南京。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为了支援西北地区的艺术教育,有关部门决定将华东艺专整体迁往西安。先期已将院藏的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石膏像等运到了西安,刘校长带头反对,温先生积极响应。结果刘校长为此被打成“右派”,而温先生等几位跟随刘校长反对迁校西安的教授也都被打成“右派”。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亲上加亲。
在开学典礼上,虽然没有见到刘院长,可是,刘院长在上海美专时期的挚友和得力助手谢海燕副院长的讲话却对我后来的艺术发展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讲话中提到关于美术史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时,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让我为之一震——怎么会是这样?谢副院长还说,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比较薄弱,全国只有屈指可数的数十人而已。他所指出的这一学科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与我们庞大的美术家队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因而当时还有这样一句调侃的话,“画画不成搞理论,理论不成搞行政”。所以,社会中对于美术理论的不重视是有目共睹的。谢副院长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因此,在我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就按照谢副院长的这一提示,不仅努力学习美术史和其他文化课程,而且还选择了美术史专业作为我今后努力进取的方向。后来,在温肇桐教授的影响下,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基本上就决定了今后转向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
1979年之后,刘院长一年会来几次学校,他的每次到来都引得全校上下奔走呼告,尤其是那些经过“文革”多年未见的老先生们,更是亲切无比。而当刘院长为师生示范作画的时候都被围得水泄不通,也是盛况空前。1980年,刘海粟院长在江苏美术馆举办个展,我在参观时被他画面中的题画诗深深吸引,后来在温肇桐先生的指导下写成了《刘海粟先生的题画艺术浅识》一文,并得到了温先生的推荐,发表在1981年的南艺学报《艺苑》之上。这是第一篇研究刘海粟院长题画的文章,也创造了南艺本科生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先例。刘院长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打听作者是谁,当他得知是本校的一位三年级的学生时,就提出要见见这位学生。当办公室的李国杰老师通知刘院长要在西康路省委招待所接见我的时候,我内心是激动不已。虽然这不是第一次见到刘院长,可是单独见面的感觉自然是亲切和自豪。刘院长言谈举止不凡,气魄很大,声音也很洪亮。他给予我的鼓励,自然也是后来我转向美术史专业的一个动因。这次接见中还谈到要成立“刘海粟研究会”的计划,亦将我吸纳为成员,可是,后来此事不知何故却不了了之。
此生虽然不能成为刘院长的嫡系学生,然而,暗中却私淑刘院长,他的水墨,他的书法,他的线条,他的气势,都是我的榜样。后来我在一段时间内专攻梅花,常常联想到刘院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画毛泽东诗意的《红梅》,枝干遒劲犹如风雪塑造,那红色的沉稳,入木三分。而热烈中的寒意出古人法度之外,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我画梅花,以刘院长为楷模,不为前人所囿,专以直杆和水墨,圈圈点点,表现梅花的清气和精神。显然,从风格上和刘院长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可是,我们以梅花为题材的创作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色,最重要的是,至今我的画长于题跋的特点,都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刘院长的题画艺术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研究他的题画诗,还研究“画之不足,题以发之”的位置安排以及与画的关系。
有了研究刘院长题画艺术的开始,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悉心收集整理明清绘画上的题画诗,编成了《明清花鸟画题画诗选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出版的第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