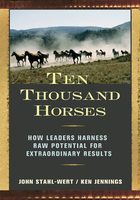时间:1949年2月初。
地点:海上。
大海一片澄澈,天空一片澄澈。
一艘舰艇在海面行进,海鸥追逐着船后被掀起的浪,在船的周围嬉闹着,不时有那么一只两只,落在船板上、舷梯上,坦然地接受游人投过来的食物。
舰艇的一端,桑梓和吉诚相拥着,面朝大海,满脸阴霾。“不知桑桑怎样了,爸妈怎样了,我心里好乱。”吉诚紧拥着桑梓:“别想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会没事的。”他轻吻着她的额头,“不要乱想,对宝宝不好。生下孩子后,我们再回去负荆请罪。”两滴泪滴落在桑梓的头发上。
成都,宽巷子,席庐。
一片凋敝的景象。大红喜字的灯笼,破烂不堪,胡乱地扔在杂物中间,那曾经灼灼的菊花,全凋零了,席庐显得那么寥落和沉寂。坐在院子里,看到满地憔悴的菊花,席母叹息:“不知诚儿在哪儿,他怎么就跟桑梓搅到一块去了。这个桑梓啊,洪泽不是喜欢她吗,还追到重庆去了。唉……”“别说了,谁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怪不得那段时间,桑梓总来找吉诚。”“吉诚自己的错,桑梓一个女孩子,还能绑架他不成。别总护着儿子,他不是东西!”“桑梓啊,她可怀着孩子呢,经不起折腾。”“是啊!”“唉,不知道桑家怎样了,该去看看的。”“看,你好意思看,见面说什么?我们两家——完了。”
暖阳高照。存仁医院某病房,洁白的墙,洁白的床。
桑桑依旧沉睡不醒,她已经躺了四个月了。怀玉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桑一鹤夫妇一下苍老了许多。桑桑的主治医师过来了,桑母急急迎上去,欲哭无泪:“大夫,我女儿是不是醒不来了?”“伯母,我没法给你说清楚。她的生命体征完全正常,她像是在逃避什么,不愿醒来。”二老听了,无言落泪。
微风中,洁白的窗幔如裙裾般摇曳。床上的桑桑,白皙的脸很安详,嘴角不时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穿好婚纱的桑桑,快步下楼来,她似乎听到了吉诚的脚步声。在楼道的拐角处,她看见了吉诚,吉诚欣喜地迎向她,她伸开双臂,向他奔去,楼梯却咔嚓一声断裂了,吉诚重重地摔了下去,他的一只手执着地向上伸着,桑桑奋力地去抓那只手,一失足,与吉诚一起跌向了黑黑的深渊。
黑暗中,两只手摸索着,终于牵在一起,在空中一起飘飞。前方有一团淡紫色的云,慢慢散开,一座童话般的宫殿出现在两人的面前。门口长长的甬道两旁是两列长着翅膀的仙女,一个胖胖的主教慈祥地迎出来,在仙女们的簇拥下,桑桑与吉诚步入辉煌灿烂的殿堂。
“桑桑小姐,你愿意嫁给吉诚先生为妻吗?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裕,生老病死,相伴一生。”“我愿意!”“吉诚先生,你愿意娶桑桑小姐为妻吗?不管她是贫穷还是富裕,生老病死,不离不弃。”吉诚眼神涣散:“我,我愿意……”吉诚不安地环顾四周,他的目光在殿堂门口停了下来。桑桑随他的眼睛望去,桑梓孤独凄楚地望着他们。忽然,桑梓张开翅膀,被天使们簇拥着,飞向了天空。“姐,姐!”桑桑急切地呼唤着,伸出手去。
怀玉赶紧上前,握住桑桑的手:“桑桑,我在这里。”桑桑流出了两行清澈的泪,怀玉用手绢轻轻给她拭去。不一会儿,桑桑恢复了平静,呼吸均匀,神态安详。见此情景,桑父桑母悲从中来。
“吉诚,你告诉我,你和桑梓怎么回事?”桑桑恳求道,“吉诚,你要告诉我,好不好?我不怪你,我说到做到,吉诚,求你了……”桑桑泪眼婆娑地看着吉诚。“桑桑,你是在做梦吧?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耳畔还是那悦耳的《婚礼进行曲》,可桑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吉诚叫醒她,在她的额前深情一吻,拥着她进入教堂。红红的玫瑰花瓣漫天飞舞,桑桑拥着吉诚,伏在他宽阔温暖的胸前,尽情地享受着这份幸福,不愿醒来。
从此,桑桑与梦同行,形影不离。她总是充满期待地遥望上帝的小屋、梦里的城堡。梦,绑架了她,或许是她绑架了梦。她不知道,梦是美好的,也是危险的;她更不知道,爱是美好的,也是危险的。
海上,艳阳。舰艇上,一对年轻的夫妇,用面包屑喂海鸥,他们甜甜地笑着。年轻的女人时不时不经意地护着自己微隆的肚子,她的丈夫有时调皮地将自己的耳朵伏在她的肚子上听,女人甜蜜地笑着,轻轻地推开他。
桑梓看着,忍俊不禁,回头看看吉诚,他也正注视着这对夫妻,只是他的表情僵硬,桑梓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中。
“我有点冷,回舱吧?”吉诚扶起桑梓回船舱,桑梓也用手护着自己微隆的肚子。那对小夫妻看见他们俩,冲他们一笑。回到舱中,桑梓要了一杯牛奶喝下,便睡了。吉诚走出来,扶着船栏,面朝大海,点起一支烟,一口一口地吐着,眼泪在眼眶里蓄得满满的,好像船一颠,就会溢出来似的。
夕阳离海面越来越近,海浪被落霞染成绯红,海鸥在跃金的浪花上飞掠,时而击打海面,时而冲向天空,这些愉快的身影,在落霞中成了一帧帧剪影,童话一般。落日终于没入了海中,海鸥无影无踪,那帧帧剪影如幻影般消失了。暮色笼罩了大海,神秘莫测。吉诚的脚下无数的烟头,他仍在凝望,面朝大海。
1947年,金秋,成都望江公园。金黄的落叶厚厚的,踩在上面簌簌作响。桑桑与吉诚十指相扣,漫步在银杏林中。他们的前面有一对银发的老人相搀而行,步态从容。桑桑深受感染:“吉诚,我们俩老了,要跟他们一样!”她将头倚在吉诚的肩上。“我们要有一群儿女,等我退役后,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住。晴天看日落日出,雨天看檐下飞瀑。清晨有鸟鸣,晚上听虫声。孩子们有的看书,有的胡闹,最小的在睡觉。”桑桑幸福地看着他,捏捏他的鼻子:“当兵的,你真浪漫!”“你呢,你的愿望是什么?”“我要在屋前开一畦玫瑰园,种上各色的玫瑰。我要养一些鸟、一条狗、一只猫。每天我会带着孩子们倚在门口,等你回来。”
他们憧憬:眼前是一片清澈的湖水,岸边有一栋木屋,周围是盛开的玫瑰,清晨的露珠在花叶上闪光。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嬉闹着,他们俩坐在木椅上,闲适自得。
海上一阵狂风,吉诚回过神来,想到刚才的情景,泪就来了。
舱内的桑梓,睡得很沉,眉头蹙在一起。
桑桑在试穿婚纱,幸福地笑着。自己站在医院的走廊,看着化验单发愣;楼梯间是吉诚痛苦的脸,自己苦痛的心。
她一转身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吉诚,她知道,吉诚不会接纳她,她十分后悔自己刚才说出的话,现在,她觉得自己像被人剥光一样,无地自容。她只想逃,逃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她后悔当初没有听洪泽的话,后悔那天没有纵身跳进嘉陵江,那样的话,一切就结束得干干净净。
就在她要奔走的一刹那,却听得一声惨叫,撕破苍穹。
桑梓翻身坐起来,满头是汗,梦魇似乎还没结束。
桑桑拽着婚纱狂奔,喊着:“让开,让我走——我恨你们!”便一头栽了下去。
桑梓一惊,彻底醒来,她趿着拖鞋,夺门而出,看到船舷边的吉诚,放声痛哭,惊愕中的吉诚和船员,将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桑梓扶回了船舱。
医生过来诊看:“桑女士,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动了胎气就危险了。你要保证自己不再这样。”桑梓抚着肚子点头,吉诚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吉诚睡下了,却睡得很不踏实,嘴里不时地发出清晰的呓语:“桑桑,对不起。”“爸妈,我错了,我给你们跪下了。”“是桑梓……”“爸,我说不清楚……”
桑梓斜靠在床上,不敢睡,她一闭眼,就能听到桑桑绝望地狂喊“让开,让我走——我恨你们”,就看到桑桑苍白的脸和瘫软得像面团一样的身体,她只要被惊醒,就会哭泣。
昏厥后的桑桑瘫软如泥,吉诚抱起她飞一般奔向汽车,桑父桑母惊恐地看着这情景:“怎么啦!怎么啦?”
桑桑被送进了急救室,医护人员忙进忙出,吉诚守在门前双手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脑袋:“我不是人,我还是人吗?怎么办?怎么办啊……”怀玉赶来了,看看他和桑梓,表情复杂。
桑梓辛酸地看着吉诚,不停地啜泣,脸上写满懊悔。忽然她眼前一黑,双腿一软,瘫了下去,怀玉大喊:“医生,医生——”大家手忙脚乱地将桑梓送进了另一间急救室。
一下子倒下两个,吉诚惊恐万分,六神无主,一切全靠怀玉照应着。给桑梓诊断的医生出来了:“没什么大事,受到了惊吓,紧张过度。她已怀孕两个多月,还好,胎儿正常。她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再刺激她,否则,胎儿不保。”吉诚目光呆滞不停地点头。
洁白的窗帘,洁白的床单,桑梓似乎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躺在病床上的,不是自己,而是桑桑。这种毫无生机的白,让人窒息,只有那吊瓶里的一点一滴,才是整个病房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
庭院积水空明,树影绰约,寒气逼人。
桑梓一抬头,两双凌厉的眼睛逼视着她,是父母,她的心像是被凌迟一般痛。他们的眼里有恨,有蔑,有怨,有痛,也有怜。他们一步步逼近她,桑梓步步后退,竟退进了桑桑的房间。桑梓很慌乱,下定决心要道出实情:“桑桑,姐跟你讲……”“不要,我不听,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桑桑泪流满面,“他上战场了?受伤了?死了?”她惊恐万分,痛哭不已。
桑梓惊呆了,原以为桑桑已经知道了一切,只是不想挑明,不想面对,原来根本不是。桑桑哪会想到世间竟有这样龌龊的事呢?她的世界是那么澄澈纯净。桑梓哭得涕泪滂沱,她无地自容,难以自处,她要认错,要忏悔,要赎罪,她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可是一片冰心的桑桑啊,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给她。她和吉诚的“垢”与“小”,一旦道出,就是对桑桑的轻侮、亵渎、玷污、戕害。
桑梓回身看看父母,他们的眼睛将她凌迟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淋。她的内心忽然生出一股怨恨:桑桑,你凭什么这样单纯。我是不耻,可我知耻了,我要从这耻海里游出来,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桑梓痛不欲生,她羞惭、耻辱,不顾一切地夺门而逃。那空寂的院子,没有门,没有窗户,只有四面的高墙,她惶恐地找寻着出逃的路,可是她动弹不得,桑梓对着黑黝黝的天空绝望地大叫:“放我出去——”
她醒了,浑身是汗,吉诚坐在床前,将她的手捂在自己宽大而有力的手掌中。
桑桑被推了出来,吉诚快步凑到跟前。桑桑如熟睡一般,神态安详。
医生对怀玉和吉诚说:“她没事啦,放心。”吉诚紧问:“她为什么没醒?”“她不愿意醒!”“为什么?”“问你自己!”洪泽用手指戳着吉诚的胸口,不再理会他。洪泽和吉诚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吉诚投考了黄埔军校,洪泽去学了西医。
桑桑被推进病房,吉诚欲跟进去,却被怀玉挡在了门外。无奈之下,吉诚回到了桑梓的病房,桑梓正在用力拍打自己的肚子:“吉诚,我们不能要这个孩子,我要打掉他。”吉诚紧紧抓住她的手:“不行,这也是一条命啊!”桑梓放声痛哭。“实在不行,那就依你吧……”吉诚躲避着桑梓的眼睛,泪眼模糊。桑梓一怔,更是痛哭不已,几近崩溃。
“拿掉孩子就能拯救现在的局面吗?就能当一切不曾发生吗?无辜的孩子是你们的救世主吗?”洪泽来了,义正词严,“吉诚,你是男人,是军人,你要负责。现在你只能对一方负责,一方一命一尸;另一方,一命三尸,你选择吧。”“一命三尸?”吉诚和桑梓惊恐地望着洪泽。“桑梓,你怀的是双胞胎。”
听到此,桑梓又喜又悲,泣不成声,吉诚却是一脸茫然和无奈,呆滞地坐着。他无法左右自己,他的内心在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决定又否定,他完全陷入了人生的两难之中,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伤害,都是悲剧。他爱桑桑,是真的,桑桑单纯娴静;他喜欢桑梓,也是真的,桑梓热情开朗;他更喜欢他的孩子,那是他的血脉,他的种。就这一天,吉诚就憔悴成了另一个人。先前那个风华正茂、英俊倜傥、幽默自信的吉诚完全失去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具枯槁、毫无生机可言的行尸走肉。
天黑下来了,吉诚久久地站在桑桑的病房外,他不敢进去,他怕桑桑一醒来就看见自己,他就那么怔怔地站着,桑桑动一下,他都会如惊弓之鸟般逃走。过一会儿,他又过来,久久地凝视着桑桑。很久很久,他才回到桑梓的病房。
病房收拾得很整洁,桑梓却没了踪影,一种不祥之感袭击了吉诚,他冲出病房大喊:“洪泽,医生,桑梓不见了!”整个医院上下出动,四处找寻桑梓。
紧邻医院的公园湖边,秋湖水平如镜,冷的月亮沉在水底。清辉中,杨柳依依。
一个落寞的身影临湖伫立,两行清泪汩汩流淌:“桑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妈妈永远陪着你们。”她慢慢地蹚进湖里,湖水没了她的膝,没了她的腰……突然一双有力的手将她拦腰抱住:“桑梓,不可以。你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夭折了吧,孩子一定不愿意。”桑梓被抱上了岸,吉诚紧紧搂住她,“桑梓,我们走,走得远远的。”“桑桑怎么办?”“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向她请罪,我们赎罪。我们有罪,可我们的孩子无罪。”“吉诚,对不起。”两人相拥着哭泣。此情此景,洪泽和医护人员悄悄退了,只剩这对苦情的人任意泪奔。
“孩子是无罪的。”吉诚的呓语将桑梓拉回现实之中,她下意识地抚摸着肚子:“孩子,你们是无罪的,你们有权出生。”舱外还是那轮冷月,望着它,桑梓的心平静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