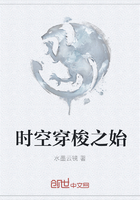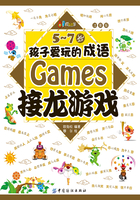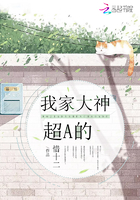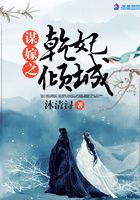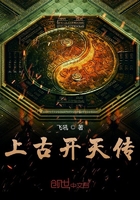从9月10号凌晨在观音坡后山第一次看见元风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郭琪告诉他这小子坠崖被救之后就失了忆,如今已被酱园街三仓货栈的老板收养了,但今天突然再见到他自己心里还是有点异样。
那天夜里这小子的眼神像头饿狼,如今从他的眼里已经看不到一星半点的邪气,看来这个“小流浪”确实因为失忆而脱胎换骨了。
也好,他心里念叨着,这世界上运气好的人就应该无忧无虑地生活,而不是直眉瞪眼地挺着或者愁眉苦脸地捱着。
……
半个小时后,元风就到了五道尖山脚下。
和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他把车停在路边的小卖部门口,买了一袋米,一桶油。他给小卖部老板发了一根烟,一眼瞅见他家后院儿地上放着一副木马背架,便向老板借了来用,把装鞋的那个大包绑在了木马上。
松铃观山门前,元风看见泉萧、泉鼓正在门口候着。
元风:“你俩怎么在这?”
泉萧和泉鼓看见元风喜出望外,一边接过元风肩扛手提的物件,一边和他说道:“风儿,你来的正好。今日寅时不周阁金铎异响,方丈便占了一卦,卯时与我和师弟说,今日巳时必有少年贵人从西南而来,着黑衣,驾木马,解我道门足下之忧,叫我们过了辰时务必在山门前等候。”
元风心想,四海还挺神,都说中了。现在刚过九点,酱园街在五道尖西南,我外套是黑色的,肩上扛的木马是山下刚借的,这包东西也是他们买的新鞋。这个很难作弊,他寅时算卦卯时相告,那时我不是没醒就是刚起床,这批货也还没送到。
元风跟在二人身后进到观内,“道长呢?”
泉萧:“方丈说卦象中可见虽是少年贵人,但此人五行里土性太重,正克我家方丈。所以,他可见你却不可迎你。你需到斋堂用一碗‘金玉粥’,之后再由我引你去见他。”
元风听见金玉粥食指大动,却没想到就是玉米稀粥里点了几片百合而已,不过一碗热粥下肚,倒也解了一路上的饥渴。
泉萧:“此时我家方丈在藏经阁。”
元风:“上次来时怎么没见到藏经阁?我看电视上少林寺的藏经阁都是单门独院的一座高楼,楼下有个大水池,十八个棍僧值守……”
泉萧:“我们这里可比不了少林寺,到了你就知道了。”
说着话两人到了西院里,这里院墙外便是一片山坡,山坡上的梯田里种满了谷物和蔬菜,一群道士正在田里忙着收玉米。
院里有个两层小楼,一楼是放农具和盛放米面蔬菜的地方,旁边有个楼梯接到二楼。他俩上了楼,元风走到门口才看见门边有个小小的牌子,写着“藏经阁”三个字。
元风仔细观察这间房,摆了许多装满书籍的原木书架,书架都是八九层向上一直顶到天花板,实际藏书量可不小。屋里虽然陈设简单,但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人点了檀香,气氛温和淡雅,倒是适合读经的心境。
最里边朝山坡玉米地的那面墙上开了一扇大窗。此刻,四海正在靠窗的一张大案台上写着毛笔字。
四海:“元风小友,有一个月没见了吧?”
元风:“嗯,一个多月了,这段时间你没下过山吗,国庆节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去镇上?”
四海:“我们出家人躲的就是清闲,再说了,山下的人忙着过节,山上的人在忙着秋收呢?”
元风:“也是,最近和老唐进山,也收了不少玉米和地瓜。”
元风走到四海身边,见四海用篆体写了四个字“一念无明”。
元风:“篆体我是认识的,这四个字我也认识,可一念无明排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四海放下了笔,说道:“这四个字是从佛经上来的。”
元风不解,问道:“修道之人干嘛研究佛经?”
四海:“有何不可呢?大道唯真,至理共通。修道之人理应修天下道,而非一门之道。”
元风:“道长,‘无明’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四海:“无明作为佛经中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公元二世纪安世高所译的《相应阿含》的经篇之中,后世自公元五世纪求那跋陀罗又将这些经篇的合集译作《杂阿含经》,并流传至今。这些经文主要记录了佛祖在世时对弟子所说的重要教理,是佛教禅修的经典。据《杂阿含经》记载,摩诃拘希罗问舍利弗:‘所谓无明,云何是无明,谁有此无明?’舍利弗答道:‘无明者谓不知,不知者是无明。’后世解释无明又阐述为‘不知意识心之虚幻’。”
元风:“听不明白。”
四海:“是贫道的过失,倒和你吊起书袋来了。”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四海转而正色道:“无明就是烦恼,就是普通人心中的‘苦’。比如说有些人回顾曾经犯下的过错,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那么想,为什么那么做,这是无明。再比如有些人要做一些选择,但思虑之时却不知要怎么想,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无明。所以修禅之人会认为无明是‘不能见到世间实相的自我猜疑,也是我们执取和贪嗔的根源’,才会生出妄想、痴心、执著的念头。”
四海:“所以大乘佛法把无明分成两个部分:一念无明,无始无明。如果因为一时的欲念而产生的‘愚痴’是一念无明的话,那没有开端和起始的‘愚痴’就是无始无明。”
元风:“道长您也有无明之时吗?”
四海抚掌大笑,“问得好,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道法虽广不度无缘之人。”
他带元风来到茶桌前坐下,在桌边的水盆里洗净双手后便开始沏茶,“我有无明之时,你有无明之时,众生皆有无明之时。佛家说无明不是说跨过了它就能显出如何的本领或者功德,其真正的用心是告诉所有人这是存在于世间的永恒,同你的思考、决定、功业、一生的行为都联系在一起,或者因为经验,或者在于偏见,或者困于无知,或者陷于执念,就生出口无明、身无明与心无明来,循环往复,不可抑止,或多或少,不生不灭。”
元风:“那无明之时到底要怎么做?”
四海:“圣弃智、仁弃义、巧弃利;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心斋天地,坐忘江湖;清虚清净致虚极,随心所欲合于道。”
元风一句没听懂,继续问道:“那烦恼终究是逃不开的,是吗?”
四海没有回答他,从桌上拿了一只透明水杯放在元风面前,拎着水壶倒了大半杯开水,然后从茶叶罐里捻出一片毛峰,放在了杯子里。
四海做完这些,在书架边脱了道袍换了长褂,“元风小友,今日招待不周,切莫见怪。赶上农忙,我们忙完了都在地里吃些干粮,贫道就不留你用斋了。请你替我谢谢唐居士。对了,出门时泉萧有东西给你,是我那荆州练内功的朋友托我转交给你的。我不懂他的玄机,希望你能懂。”
四海说完这些,扬长而去,只留下元风一个人还坐在藏经阁里。元风看着身边的那个茶杯,那只茶叶已经泡发了,翠绿翠绿的叶尖立在水中,既不上也不下。
元风心想,这四海和电视上的牛鼻子老道一样,就喜欢打哑谜,这回自己彻底无明了,根本不知道四海干嘛来这么一手。
他是想说我就像这个悬在茶杯里的茶叶一样是一个无明之人吗?这么说倒也没错,自己没有记忆,也看不清未来。
四海是不是在嘲笑自己是个“杯具”里的小人物呢?可能性不大,四海道长应该还不会尖刻到这种程度,倒是自己多心了。
……
元风从松铃观里出来时,泉萧果然送了他一件东西,用牛皮纸包着,放在塑料袋里。
元风下了四道尖之后,看周围无人便立刻拆了包装,见里面包着一套四本的线装古书,书名叫做《妙谛玄轴》。他看这黄巴巴的纸张和手工线装的工艺就感觉这是个很牛B的东西,说不定和《九阴真经》或者《九阳真经》有的一拼,只要不是《葵花宝典》就行。
他下了山没有直接回三仓货栈,开着三轮去了潘家园。
……
此刻他就在猩猩的房间里,二人对坐着,都趴在桌上紧紧盯着桌面上那杯泡着一根茶叶的白开水。
这是四海给元风出的题,他又原样给猩猩演了一遍。
“这是禅机啊!”猩猩感叹了一句。
元风望着他,一般这种时候,猩猩后边都有长篇大论的。
猩猩:“对于修行的人来说,茶与禅本是一味。出家之人是最早饮茶的,洞庭碧螺春、武夷岩茶、大理感通茶,天台山罗汉供、杭州香林茶、九华山高山云雾最初都是产于寺院,然后由雅士高人带至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