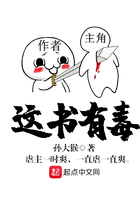(1)
第21天。
醉酒的感觉无比幸福,除了第二天以外。
梦境跟现实有很大不同,不难分辨,只是需要时间以及你在哪。当你梦着你很难分的清现在是不是醒着,当你醒着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一样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醒着。
但就头痛欲裂浑身无力来讲,马可知道自己醒了,知道自己昨晚喝多了。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第一次感受断片儿,挺奇妙的,但也很慌张。马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回到床上,从味道上判断自己可以给这个陌生的房间造成了极大的化学伤害。
他站起身,突然感到一阵恶心,然后眼前发黑。他强忍着站了一会儿,感觉自己还行。他朝房门走去,终于摸到了门把手,拧开,一个人从门的另一面进来跟马可撞在一起。
“马可先生,很显然,你醒了?”那人抓住了他的肩膀,他才没再次倒下去。
他认出眼前的是夏迎春。
“呃……啊……”一口酸液吐在了小夏身上。马可一边咳着一边说:“对不起!我没忍住。”
“闻起来像是——”小夏说,“盐酸、糖蛋白、胃蛋白酶、黏液……”
“什么?”
“我是说,我得过一次胃炎。水、脂类、蛋白质、电解质和多肽激素,PH值1.4……”
“他说你的胃受伤严重。”俞一雯走过来,仍穿着前一天的大牡丹连衣裙,鲜艳亮丽。马可想起了昨天的事。“这是哪?”他问。“黑水公司董事长钟明的别墅,小雪的家。昨晚你把保罗给的地址交给了大排档的老板。”一雯说。
“对,那个老板——他有些奇怪。”马可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似乎没有。
“你真该好好谢谢人家。”一雯说,“还有钟雪。不过她现在不在。你还能走路么?”
“还行。”
“那我去跟小雪逛街了,让小夏送你回去吧。”
马可被送回了旅馆房间。他感觉自己更难受了,除非是躺下,其他姿势都让自己觉得像是死过一次似的,比回溯更糟糕。
“小夏,你去休息吧,我自己能行。”
夏迎春点点头:“那你自己注意些,有事打我房间电话。俞医生说你这情况至少躺一天。”他指了指床头柜上,“保温壶里是粥,休息一会把它喝下去,再努力的睡一下。也是俞医生交代的。”夏迎春向房门走去。
“小夏!”
夏迎春回身。“啊?”
“手表的事——很抱歉。阿亮跑了,我找不到他。”
“没关系的,我知道你尽力了。”夏迎春出门回了房间。
马可浑身无力。喝了粥,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然后摸到了脖子上的项链,他用手揉搓着,渐渐的,他睡着了。
(2)
再次醒来已经是晚饭时间。
这次送饭的是小卢,还是喝粥。送走小卢,马可靠在床头,打开电视,胡乱的按着遥控器。
猛然间,他想起了那颗种子。
他窜下床,那件西服脏透了,还没来得及送洗,谢天谢地。种子还在布包里。他拿着那颗种子发了会儿呆。然后他找了个杯子,接了点儿水,把种子扔在水杯里。水杯立刻被映成了猩红色,他盯着水杯,十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好像不是这么种的’,他这么想着,重新把种子捞出来。
他看看种子,又看看那杯水。他把水杯拿起来一饮而尽。然后躺回到床上,闭上眼睛。等他再睁开眼睛,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床头是空着的水杯,种子还在自己手心。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马可把种子放在自己的舌头上,轻轻的舔了舔。接着,他把它放在嘴里含着。——没什么味道——
马可用牙齿轻轻的咬了咬。咔,种子被咬碎了。
‘好苦!’
但是他没吐。吐了就全完了。他赶紧又倒了杯水,喝了下去。然后再来一杯。
‘完了!’他想,‘唯一线索现在在他肚子里。不久还将被自己消化。’
马可试着走了走,没感觉有什么异样。他看了看窗外。
‘晓风残月,今宵酒醒何处?’他对着月亮傻笑了两声,又念了几句“一了百了。”
他伸了个懒腰,觉得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他洗了把脸,然后发现自己长出了胡子。他在洗漱包里找到了剃须刀和剃须泡,刮了胡子,最后穿上一套运动装,把那个空布包揣在怀里,下楼去了。
他在旅店周围闲逛,晚上的空气不错。转到一雯的窗下,抬头看了看,灯还是黑的。他围着旅馆转了大概有十四五圈,脑子里不再像前几天那样乱糟糟没有头绪,而是清澈透明。他走累了但精神很好。在停车场边他看到自己的新车。很普通的大众车,经济实用。他插手在口袋里摸了摸。‘出门的时候竟然带上了车钥匙!’
他打开车门坐在里面。收音机里交通广播、音乐广播、新闻——,马可不停的换台。他觉得有些无聊,然后他转动车钥匙,发动机转动起来。接着,他在马路上漫无目的的开车,逛着逛着逛出了城区,逛着逛着逛上了公路。然后,他沿着向北的方向一直开了下去。
(3)
郊外公路上车很少。
但马可还是尽量开的慢些。虽然路灯还算明亮,但极远处仍然是黑洞洞的。
两个多小时后。终于看到了那片果园。
马可没有开进往别墅去的小路,也没有停车。他又向前开了1公里,才停在路边,熄火下车。他在后备箱里翻了翻,只到一只尾部带有安全锥的手电筒,一边是手电,一边是金属锥。掂量了一下,分量不小。试了试,还有电。
他沿着公路往回走了大约400多米,一矮身钻进了果园。因为担心被人发现,他没敢打开手电,而是借着果树枝叶透过来的一点点月光,摸着黑往果林深处走。他在心里算计着,这个方向,是能够到达洪运奎的别墅的。就算有人守在这,也应该守在小路上,不会在果林里。
马可走出了20多分钟,蹲下来观察下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微风滑过枝叶的沙沙声。速度太慢了。他站起身辨别了一下方向,决定冒一冒险。他开始往偏南的方向走。这样能尽早找到通往别墅的小路。如果能离小路近一些,就可以借着路灯前进,这样再走30分钟也就到了。
走了没多远,突然听到前面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哗啦啦——哗啦啦——’
马可再次蹲下,瞪大了眼睛四下里找。可见的范围都是果树。但这声音绝不是风声。‘是老鼠?’他俯身接着往前走,走的很慢。
声音越来越大。那表示越来越近,而且那东西听起来个头不小。他绝不甘心就这么回去,抽出手电把安全锥的尖头朝外举到自己耳侧。
前面有一个建筑,一人多高。看起来像是个施肥罐。马可绕过它,渐渐的看清了它后面的东西。
他突然僵住,定在原地,像一座雕塑。
马可终于看到是什么东西在响动。那是一条黑色的狗,在一颗果树下正在用前爪在土里挖坑。没命的挖。
马可脑中闪过保罗说过的一句话。‘这里有一只疯狗,已经咬了几个人了,我们还没抓住它,很危险的。’
马可轻轻的往后退。他屏住呼吸,绕回到施肥罐后面。他停下来稳了稳心神。转身继续悄悄的潜行,他感觉浑身紧绷着,头又开始晕起来。
他走着走着身后‘哗啦啦’的声音消失了。马可扭回头,可见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他加快了脚步。方向,方向。最近的开阔地应该是那条小路。然后马可干脆跑了起来,刚跑了十几步,后面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喘着粗气。粗气在身后追着他。马可脚下拼命的跑,后面的声音却紧追不舍。马可扭回头一看,黑影已经来到面前。就是那条狗,黑色皮毛被月光照的发亮。
马可拼尽全力跑下去,可后面喘气的声音却越来越近。他再回头的时候,竟是四目相对。黑狗流着口水。黑狗跳起来扑向马可,马可腿一软蹲坐在地上,黑狗扑了个空。还没等马可站起来,黑狗已经发起了第二次进攻。
“啊!”
马可的左肩膀被黑狗咬住。剧痛让马可下意识的用力挣扎。可怎么挣也挣不开。马可用手肘抵住疯狗,用力一扯,左肩上的一块肉已经被狗咬下来。马可忍着疼,站起来就跑。没几步,感觉小腿上又被咬了。他用力一甩没甩开,反而被拖倒在地上。他回手抡起手电,用安全锥的一侧用力向黑狗的脑袋砸过去,不停的砸。黑狗挨了几下,吃不住疼放开了马可。
马可拖着伤腿再次逃跑。黑狗就跟在他身侧,像是在寻找好的角度和偷袭的机会。
马可借着果树几次躲过黑狗的扑击,现在已经分不清方向。他跑着跑着,依稀见到前面有一闪一闪的光亮,等跑到近前已经能看清是几个手电在往自己这边照射。
“救命!”马可声嘶力竭的喊着。
“什么人?”几个手电朝马可喊着。
马可冲出果林迎面跟一个保安撞了个满怀,身边另外两个保安围过来把马可按在地上。马可喘着粗气:“狗——疯狗!”三个人立刻放开马可,黑狗同时也冲出了果林,霎时间就有一名保安被被咬住小臂扑倒在地。马可站起来忍着疼往大路上跑。身后人喊狗叫乱成一团。
马可一口气跑出了小路,上了大路,他完全忘记了疼痛,奔了有将近两公里,一直跑回到自己的汽车。开门、上车、锁车,这会儿才顾上喘口气,不停的喘,口腔、气管和喉咙已经被呼气吸气搜刮的干燥疼痛。还没等他把气喘匀,远处的岔路口开出来两辆车,朝自己的方向飞驰而来。
马可掏出钥匙打着了汽车。他踩住离合挂上倒挡,一边看着对面来车一边系上安全带。两个车子停到近前,下来五个保安朝自己围过来。等围到近前,马可猛的踩油门。车子倒出去一大截,然后咆哮着冲开了包围圈,一路向南飞驰。
马可开的飞快,好像那条疯狗还在他身后似的。肩膀和小腿开始疼了起来,痛的他浑身发抖。渐渐的他感觉自己的视线有点模糊,伤痛加上刚才的狂奔还有失血太多。马可越来越晕,车子在公路上摇摇摆摆。他进入一段弯道,前面出现一辆卡车,他急忙转左,却在另一条车道上撞上了一个三角架。马可猛打方向盘。车子突然失控,飞了出去,紧接着车身翻滚了几次,冲出了路肩。
(4)
车轮朝上。
马可大头朝下挂在车厢里。他用力睁开眼睛,可眼皮不怎么听话。伸手摸安全带的卡扣,可怎么也摸不到。马可悬在那里,身体动不了,脖子上的项链垂在自己脸上,上面坠着的戒指就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朦朦胧胧间,他看见一辆车停在公路边,一个人从车上走下来,嘴里叼着一根烟,走起路来像是个老人,可样子又没那么老。
那人走到近前,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马可颈下的动脉。
“我还以为你自己就把自己终结了。”
那人往马可的脸上吐了个烟圈,然后在马可的眼前掸了掸烟灰。
“我的头——好痛。”马可说。
“我知道,我知道。马上就好。”他说着从后腰某处抽出一把匕首,“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昨天多谢你,我过的很开心。虽然那个狐狸精拿走了我所有的钱,不过正巧我没什么钱。”
比起那把小刀,马可更担心自己的头。那种要裂开的感觉,还不如给自己来一刀。
“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人说,“他们说你是杀不死的。”
马可觉得他认错人了,他想申辩,可喉咙好像被什么卡住了,什么都说不出。
“可是我不相信,”那人说,“二十多年了,我想我总得试试。也许能成呢?”
那人说着,刀子往前递,可刀刃在马可的脖子前面停住了。
那人一手擎着刀子,另一只手捂着胸口。“好热——”他皱着眉,跪在地上。铛琅一声,刀子脱手。“好烫——”那人躺在地上双手揉搓着胸口,身体不停的扭动。
马可的头昏昏沉沉,可他更惊异于眼前的景象。那个人脖子肿了起来,胸口到喉咙处像是有个大功率的灯泡烨烨放光。那人撕扯着胸口的衣服,急的满地打滚,他的脸和手也跟着红了起来,微微的泛光。马可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那人的喉咙里开始冒出滚滚的黑烟。
“你总是没记性,”另一个声音冷冷的说,“我说过,我会烧死你,从里面。你想体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么?谢必安?”
一个灰蒙蒙的东西走到马可旁边,他蹲下来查看马可的情况。他的肚子又大又肥,脸色很难看,灰蒙蒙的,头发特别的少,但却卷曲着上升着。
马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胖子。“张友人?我的头——好痛。”
“忍耐一下,”张友人说,“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至于为什么头痛——这我可说不清。”
“求你了,停下来!”谢必安嘶叫着,扭动着,满脸通红,嘴里还在冒烟。
张友人转身摸了摸谢必安的口袋,掏出手机,拨了120。电话接通,他告诉对方车祸的位置后,朝谢必安挥了挥手。谢必安渐渐的冷静下来,喘着粗气。
“我真该把你烧成焦炭,”张友人说,“你干嘛就是不肯放过他?”
“不肯放过他的不是我。”谢必安从地上爬起来,瘫坐在地上。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再热也不再烫,只是摔了一跤。“他凌驾于时间和死亡之上,”谢必安说,“他在跟宇宙的规则作对,除了神明没人有资格获得任何意义上的不朽。是诸神不能原谅他如此狂妄的——”他想了想,“——狂妄的身体。”
“得了吧,”张友人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你口中的所谓诸神,都是不入流的小朋友?听我的,回家吧,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实在不行,去钟离权那消遣消遣。”
“你肯放我走?”
“我说过会烧死你,但那是在你谋杀了我的朋友之后。是对你的威慑。”
“可我还会找上他的。”
“我也会一直跟着他。”
谢必安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匕首,依旧插在腰间,他可不想下次拧不开酒瓶盖的时候找不到它。他对马可说:“总有一天我会完成任务,你的意识会跟着我走,去你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会回家,睡上几天。”
说完谢必安回到自己的车上把车开走了。
马可感觉自己的头好了些,不怎么痛了,但却越来越晕。他在有限的视线范围寻找着张友人,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张友人已经不见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看到救援车和救护车相继到了,在人们撬开车门前,他就昏过去了。
马可做了一场梦,他梦到旅馆,梦到K的别墅。接着是一个小镇,然后是一间实验室和一座荒山。最后他梦到一个峡谷,到处都是猩红色的植物,像是生的牛排,或是一整块新鲜的肝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