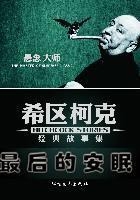将近十点的时候,巨大的理疗机器才推到了茹风的床边。护士在调机器的时候,他转过头去看了看隔壁床的女人,她已经舒坦的睡着了,但这次没有打鼾。病房里大多数人都睡着了,总之还是要归咎于旁边这个呻吟的女人,就是她不断的呻吟和鼾声才让许多人在病时欣赏不了蓝天,而只能披星戴月的辗转,虽然打鼾的不止她一个,可是谁让她在茹风的旁边呢?茹风是个睡眠非常浅的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因为睡觉而误事、或者一次性上几个闹钟这样的事,他总是在闹钟响第一声的时候拿起来把它关掉,然后很快的爬起来。
冰凉的导片贴在他的太阳穴上,爪子抓住它的头皮,机器发出嗡嗡嗡准备的声音,然后是有节奏的滴滴声,大约只在茹风的耳边响了几声,他便什么也不知道的睡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感觉到有人把机器撤走,但是他睁不开眼睛,太空旷了,周围的一切,他陷入了一种没有梦、没有思想的睡眠中。
再醒过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黑了,值班台的护士也换成了昨晚的那个,她用一支带羽毛的笔,在本子上沙沙沙的记录着什么,仿佛用不着思考一般的,不间断的写着。
他和女人之间的那扇帘子又重新被拉上了,女人一点声响也没有,仿佛不在那里,周围的一切都安静极了,他想动一动自己的腿,但是没有用,他和腿的关联好像被某种东西取消了,也好像腿不在那里。
他想抬一抬手,发现也是一样,手的关联也和他的思想完全取消了。
“护士。”
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发出声音,只看见小护士还是纹丝不动的在本子上沙沙写着。
“护士。”
他又叫了一声,他仿佛失聪了,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他透过未拉严的窗帘借一丝月光,直到太阳升起来。
“我想上厕所护士。”小护士拉开他与女人之间的隔帘时,他对护士说。
“上吧。”
“可能要麻烦你一下。”他扫了一眼吊瓶。
“你直接上就是了,插了尿管的。”
“我想上个大的。”
“直接上就是了。”
“可是?”
“你只是想而已,你上不出来的,不信你试试。”
他其实丝毫不想上厕所,只是不确定的事情越积越多,他感到害怕,或者他想确定自己的腿还在不在,仅此而已。
女人的床位变成了一张空地,床被推走了,‘难怪没有声音’他想,这一幕让他有了一丝放松,但随即又焦虑起来。
过了一会儿,女人被几个人推了进来,她还是一个劲的呻吟着,也不知道是哪里疼,她为什么总是这样,整个病房只有她一个人呻吟,是其他人坚强吗?不,只是真的不疼而已,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至少茹风是这样。
“您哪里不舒服吗?”
“受老罪了哎哟。”
“您昨天去哪儿了呀,一晚上没回来。”
“做手术去了。”
“那见到你的孩子了吗?”
“哪有什么孩子哟,这可是外国。”
“外国?”
“你看哪有个中国字的,俺虽然不识字吧,看个形状还是会看的。这些小姑娘都有出息哟,都跑到外国来打工了,将来俺儿子也能有这样的出息,他学习可好了……”
这病房里,从护士到病人全是中国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女人口里的‘外国’,茹风越想越觉得奇怪,又接着问:“大姐,你怎么到这来的啊,你知道吗?”
“那我不知道,哎哟……”她仓促的答应了一句,又呻吟起来。
“这的医药费看起来不便宜。”茹风故意说。
“我家是种田的,哪交得起这个钱。”女人一下子急了。
“您来多久了?”
“十天半个月都不止,护士护士!”这会儿女人已经顾不上和茹风闲聊了。
这回不是昨天的494。
“姑娘,这你们收多少钱一天呀?”
“这我不清楚。怎么了你?”护士的口吻充满了不耐烦。
“我们那个新农合可以用不?”
“你别瞎操心了,你家人会解决的。”
“哎哟,要命了!我们家是想不出办法的呀。您就告诉我,新农合可以用不?还要自己交多少钱?我得的是什么病?这里是哪里哟……”女人一股脑问起来,越说越激动。
茹风心里平添了一份内疚,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不该再给她这个女人添这些烦恼,她虽然很吵,但是真的很可怜,看得出内心也十分淳朴良善,至少她一定是个好母亲。
伴随着女人的吆喝,病房里也开始有了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声音变得越发大了“对啊,我们什么病?怎么都不知道!”“对啊!今天得给我说清楚。”这些人虽然声音大,可还是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茹风又试着动了动腿,还是没有用。
护士连忙跑到大病房中间去镇压,这会儿应该是中午,茹风下意识的看了一眼鈡,果然12:30,刁钻的护士一瞬间显得很单薄,她拼命镇压着病人的高呼,又跑到值班台去打电话。
这时,隔壁床的女人一把扯下了左手上的针,下了床,但肩膀上的导管是和一个机器联通着的,她险些被绊倒,她把身子往回靠了靠,一只手推着机器,双脚一瘸一拐的朝门口走去。
“大姐!当心啊。”茹风焦虑的疾呼。
“我就是到收费处问问!不急。”女人说。
小护士挂上电话急匆匆的迎着女人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