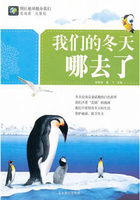午后的天空阴得很厚,仿佛正盖着被子在呼呼大睡。这巨大的被子不仅朝上盖着天空,而且也向下捂住了地面,这样,盛夏的炎热就只得无情地欺负地球上的生物了。作为万物中高级的统治者--人类,这时候,都在盼望着清凉雨水的到来。而处于高级人类中的弱势群体--民工,也正在工棚里,等待着到底需不需要上工的号令,由此看来,这号令似乎就来自于天空。
民工们的心是矛盾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喜欢下雨的天气。一方面,雨天可以让他们疲倦紧张的身体得到休息,得到放松;但另一方面,当他们休息时,活就得放下,那将会是时间的消耗,是没有工资的消耗。
不过,相对他们来说,气候就简单的多了。云层似乎还在不停地加厚,但什么东西都会有无法承载的时候。终于,云层的厚度到极限了,它不会作任何思考,载不动就卸呗--雨,痛快地投向了大地的怀抱并热烈地亲吻。
“嘿,休息吧,等雨停了再说。”王进明对大伙嚷嚷道,他刚刚坐起便像少了重心的不倒翁似的躺下了,两对“眼皮夫妇”又亲密地抱在了一起。
虽说,工棚现在还属于午休的时间,但里面一点都不安静,甚至可以说相当的吵:不仅有那些睡觉时特有的响动。而且,有几个人仿佛天生的不知道累,在这万物都犯困的时候,他们却在“叽叽喳喳”地侃大山。这些人当然就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了。
“啊呀,你们不知道,当你第一次下井时,你会相当害怕……”高桓正在将自己的打工经历同好朋友分享,当他知道雨水强迫他们休息时,他便讲得更有精神了。而拿着好奇心吸取新鲜事的周毅和周家庆,却一动不动,好像并没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他两还处在刚才的炎热中盯着高桓一起流着汗。
“当你被慢慢地往井下送时,周围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黑了,你就像是被慢慢地送到了地狱。那种感觉,唉……再当你最后到了井下时,先不说那种从来没有过的黑暗怎样,就那特殊呛鼻的味就能叫你换不过气来,我的天……”高桓还想滔滔不绝一会,但门口有情况了。
“嗒嗒嗒”是雨中急促的跑步声,“啪”,一个湿……,不,“落汤人”站在了门口,天唉,你就不能找地方避避雨吗?
“我的个乖乖,这球雨还挺大,妈的。”迎雨跑回来的人正是杜有志,他又在骂天。
“在头灯的光线里,你可以看到那和水一起流下来的煤溜子,听,你的脚下还有老鼠叫唤的声音……”
“来、来、来,大伙都醒一醒,有事和大家说说,都起来啦!别睡了!”杜有志说,过了一会儿,他已经把头发擦干净了,但睡觉的人们仍然睡着。“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塌方……”讲故事的人依旧讲着。
杜有志见客气地说没效果,他发火了,他脱下鞋使劲地敲着床梁说:“都他妈给我起来!你,别说啦!一群鳖孙。”
“怎么了?”
“谁啊?”
“什么声音?出什么事了?”
……
他的话凑效了,民工们一排溜一骨碌像部队的紧急集合一样坐了起来:一个个瘪瘪的肚子在快速地起伏着;一副副迷然的表情在搜寻着出了什么事;一双双含着浑浊眼泪的眼睛最后都一齐冲向了杜有志。
“杜叔,怎么了?能不能正常点啊?”周毅恼恨他搅了一局精彩的讲述。
“就是,老杜,以后请你别闹这么大动静,唉!”又有人说。
“呵,都教训起我来了,妈的。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有病,淋着这么大的雨,我跑回来?都教训起我来了。”杜有志不服气地说了这么几句,倒也不显得太生气。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王进明说。
外面的雨还在“噼哩啪啦”地下着,屋内已经慢慢的“安静”了,当然也一定很自然的存在着民工们应该有的声音,但这不会影响杜有志给他们开会。
“大伙听我说,是这么个事情,咱们工程队原本只是包了这个建筑的基础和主体,这不,这些活马上就干完了。我寻思吧,这年头,找个活也不容易。我就和冯建业商量,是不是将剩余的装修什么的也揽给咱们,他说可以给上头说说。他和上头去说,我就来和大家伙说,你们也都是老工人了,什么活咱干不了,嘿嘿。不过,我还得征求你们各位的同意,如果不想继续干呢,就先打个招呼,过几天签合同、领工资啥的,就不乱了。好,不想继续干的我登记一下。”
“还有,你们别太小心了,人家公司虽说也拖咱们工钱,可人家迟早都会如数给了咱们的。”杜有志的话说完了,他等待着是否有人会选择去找新的工作。然而,好像是他最后的几句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好多个似乎想要退出的人却又坐下了,最后,只有十几个人选择了离开大家。
能有这样的事,对周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不但觉得目前的工作十分适合他,既体现价值又能挣了钱;而且觉得目前所相处的人们也都十分适合他,既有传授本领的师父又有同甘共苦的兄弟朋友。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工地干活,他可以每天晚上与他喜爱的女孩独自相处一段时间,因此,不用怎么考虑,他便死心塌地的留下了。
接近黄昏的时候,雨撒完了它最后的一滴。继而,天空也就放晴了,是被洗过的那种清澈的晴。老地方的晚霞也出来了,它红艳艳地笑着,在高兴的告诉人们:明天将是一个大晴天。
周毅又该去约会了,他顾不得欣赏漂亮的晚霞,也无暇去顾及其他民工对天气的评价。他只管在畅然的心情中,顺着那条梦一般的小路,去看到她的脸,去牵住她的手。
灰蓝的天空投射出昏暗的境象,昏暗带来了柔和清淡的路灯光,在路灯光的伴随下,周毅和陈文歆手拉手漫步在闲人汇集的街上。
街道改不了它特有的底层风貌,就像周毅改不了他对陈文歆的喜爱。此时,也许有人不解了,为何这样看似毫不相干的两者会被一起提及呢?因为这两者都共同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它们保持的时间具有相同性,可能长久存在,更有可能,现在的状态只是一颗划过的命运流星,或许在哪个没有征兆的普通时间里,它们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面是一个写着“美美神剪”的理发店,牌子上的红绿彩灯正在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看到这个,周毅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而陈文歆也由不得己地仰视着周毅的头发,已成鸟窝了。然后,他们的眼神撞到一起,便会意地笑了。
理发店的门永远向他们打开,理发店的老板娘也会永远与他们笑脸相迎。然而,年轻的女理发师却似乎是一副不会软下来的面容,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老板娘的命令。
“欢迎,欢迎,理发吧,快里边请,嘿嘿。”老板娘没有下达命令。
“你们哪位理发?”理发师依然没得到命令。
“哦,好,好,坐这里吧,媚儿,拿你的绝活给这位帅哥好好露一手。”
“呃?什么?媚儿?!好熟悉的名字,是在……”周毅的脑袋又开始回忆往事了,似乎他的记忆力真的不太好,当他自我感觉已“翻江倒海”般的搅动脑汁很长时间时,才在突然之中意识到“理发店”、“发廊”之间微妙的关系。
“啊,发廊、媚儿、虎……”他想起来了。
“你叫媚儿吗?”周毅问,他看不到女理发师的脸,只看到自己眼前那垂下的头发。“嗯,是啊,他们都是这么叫我的,嘻嘻。”
“那,那你认识王双虎吗?”周毅又问。
“不认识,嘻嘻。”女理发师娴熟认真地操作着手里的头发,仿佛是故意为了应付“嘻嘻”的声音才扬了扬嘴角,而后的一瞬便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的表情又变为硬硬的了。
在他们这短短的交谈中,坐在旁边的陈文歆敏感地看看周毅,又看看媚儿,眼神中充满了“愤怒”的醋味。她仔细研究了一下镜子中忙碌着的媚儿的脸,发现这女孩的眼睛有些特别:那里面的一对眼珠子似乎不怎么灵动。还有,她的脖子是像电脑摄像头的脖子,弯弯的,呆呆的,在没有外力的时候,可能“永远”不会变形,像个机器人。不过,她的样子倒还算清秀,尤其那满头秀发--时尚飘逸。
“哦,原来你不认识啊。”周毅正在被摆弄着。
“你们可真奇怪……”老板娘说话了,“前些时,就有个自称王双虎的人,见了我们的媚儿好像眼都直了,非得说他认识我们的媚儿,这不是笑话吗。我们的媚儿我从小带到大,基本就没出过门,我把我的本领全部传给我们的媚儿,她学得很努力,也很认真。唉,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脑袋却有些毛病……”
老板娘停止了说话,陈文歆眼中的“醋味”也消失了。周毅闭上了眼睛,任由细碎的头发在“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中,像雪花一样无声地飘落到雪白的围布上。
“嘻嘻,好了。”媚儿说。
头发剪短了,也剪漂亮了,周毅想看一看此刻头发的效果,却只看见媚儿那浅浅的笑容正在慢慢升华。
从理发店出来,周毅的脑袋感到了无比的清爽,这样的感觉他已好久没有尝到了。
陈文歆津津有味地看着周毅,心里十分佩服媚儿的手艺,将自己的心上人整理地既精神而且更加帅气了,她很高兴,很自豪。而周毅却在思考着一个解不开的问题:难道世界上真有两个人,他(她)们拥有相同的名字,相同的长相,以及相似的职业吗?……可能、也许、或者,真的有吧。他在意识里这样回答了自己。
旧的工作一做完,新的工作也就接踵而至了。
崭新的楼房矗立而起,像一个刚落地的婴儿:脚手架的撤离,是他脱离胎盘后的独立;斑驳的墙体,是他未经雕琢的娇嫩躯体;空荡的楼壳,是他还未开发的智力。
难以忍受的酷暑,难以改变的苦累。楼房最后的工程开始了,工人们在仔仔细细地将这个刚出世的婴儿朝漂亮的方向打扮。周毅和周家庆面对这样的工程,似乎又无称心的活可干了,他们没办法,只得再次被分派到基层的岗位上,从而回归了他们原先的力工行业。
看着一个个在外墙上忙碌的身影,杜有志依旧行使着他监督的职责。民工们很卖力,只要材料备齐,他们的世界里也许没有开小差一说。不过,也不尽然,这不,在杜有志谨慎地巡视中,几个民工却“悠闲”地围着圈抽起了烟。
“唉,那几个鳖孙,干什么呢?”杜有志呐喊道,并走了过去。
他的话太有震慑力了,话音一落,那几个人仿佛猛然想起了,现在是工作时间,不该这么大胆地消遣,便快速的悻悻然操起工具,继续起了他们的活。
当杜有志走过去时,他看到,刚才那几个人所围的沙土上画了些条条框框,他不用细看便已猜测了个七八分:这几个小子肯定有鬼。
“呵呵,鳖孙……”杜有志轻轻笑了笑。
然而,这边的事刚摆平,不一会儿,那边又吵吵着热闹起来了,而且聚集的人还不少。“妈的,这伙鳖孙看来是要真的造反还是咋的。”杜有志皱起眉,自言自语道,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便朝热闹的人们跑去,可他这一抹,却将手里的灰画到了脸上,但他丝毫没觉。
“你他妈有种就再说一遍!”
“你……本来就是嘛……有病!”
看来是有人打架了。不过,这嘈杂中那带点嘶哑的声音,使杜有志不能分辨出是什么人在为看热闹的人上演“龙虎斗”。
他走近了,也在人缝之间看清楚了表演者,原来是周毅和来自河北的李顺子搅到了一起。
“呵呵,乖乖,好啊!好好打,你两好好打,你们好好看,呃,延误了工期,上面扣你们工钱时别他妈找老子,啊!”杜有志出现了,一些人听到话音,开始看他,好像他一个人的吼叫比过了两个人的表演,看他的人竟然笑了,而且也不再观看打架,虽然这时的打架已不止是两人了。
“你们笑什么笑,快去干活!”
“哈哈!老杜,你太够意思了。他们唱武戏,你还在这儿唱文戏,哈哈,还把脸谱给画上了。”有人说。
“哈哈!呵呵……”看着杜有志的人笑得更有节奏了。
“鳖孙,别管老子唱什么戏,你们几个狗日的赶紧干活,小心工钱我扣你们。”杜有志颤抖着手指说。还别说,这话挺有用。说完后,那几个人很快便归向正业了。而还有那么几个武戏迷,可能并不在乎工钱被扣,还在认真地欣赏着单挑是如何发展成群殴的,虽然,杜有志已经高喊两遍了。
“我操!”杜有志没办法了,他冲进“打斗场”,朝每个“勇士”的屁股使劲踢了一脚。但可笑的是,被踢的人依然站得很稳,虽然他们还在施展着武艺;而踢人的杜有志在完成了这项壮举时,却摇摇晃晃地快要站不住了,好像是他在有意炫耀自己的醉拳。不过,虽然杜有志已显苍老,但毕竟还是个男人,他的一脚还是让几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愤怒地看着他。
“呃,你……你们继续打啊,怎……怎么不打了?啊!”用尽了坚强的意志,最后才站稳的杜有志像一只打累的野兽,弯着腰怒斥着,虽然他才一共只踢了四脚。这四脚分别是周毅、周家庆、李顺子和他的一个同乡。
几秒钟内,四个人只怔怔地看着杜有志,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但围观的人却多数夹起工具离开了,因为工长的“神兵天降”使得那两句关于工钱的话有些滞后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
“杜叔,是这家伙先骂我的……”周毅最先发觉他们被工长抓住了,但认出是工长的他,脸上却仿佛有了笑影。
“杜工长……我,我,是他先打我的。”李顺子说,他第二个认出了杜有志,也许是他的眼睛有些肿的缘故,认人的本领才落后了周毅。
“工长,嘿嘿,我们不敢了,饶了我们吧。”
“是啊,我们不打了。”两个帮忙打架或是帮忙挨打的人说。
“荒唐,简直荒唐,都十八九、二十的人了,还打架,你们他妈鳖孙们还要不要脸了,告诉你们,这个月的工资每人扣五百,这是上头的规定。”杜有志那粘着泥土的脸好像是增加了他说话的气势,因为四个人都显出很害怕的样子。
“什么,这就扣五百啊?”周毅惊道。
“对,就是这么个规定。我也不问你们打架的原因,不管谁对谁错,在我面前都是错,工钱都得叩你们,谁要是不服,卷铺盖走他狗日的。”杜有志宛若一个手握大权的人物,很是有气派。
“知道吗?你们这几个鳖孙已经严重……”
“哈哈哈……”周毅控制不住笑了,因为,他觉得杜有志此时的脸酷像一种什么动物,对,斑马,但他不是黑白杠,而是灰黄杠。
周毅的笑一打开,其他三个人便似乎被提醒了,看着杜有志的脸,他们也笑了。
“哈哈……呵呵……”
杜有志给工地带来了笑的资本。
是什么创造了似曾相识;
是什么带给了我们陌生的熟悉;
也许只有经历才是真理;
只有奋然向前才会拥有自己的历史;
但现实却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定义;
因为,茫茫浩瀚才是永恒的生命之地。
时间始终是一天一天地过去,日升和日落是它的标志。当我们天真无邪的时候,天上的太阳似乎永远那么耀眼,日子也永远那么漫长,因为我们渴望着长大。然而,当幼时的愿望实现了,我们长大了。此时,拥有成长经历的我们,又开始感叹时光飞逝的无情。我们忙于各种事情,无暇享受时间应有的乐趣,所以,我们又常常怀念儿时的那种无忧无虑,尽管那时的岁月我们只是处于“无奈”的等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