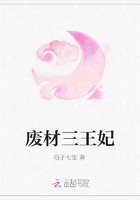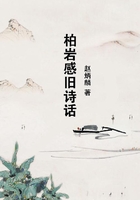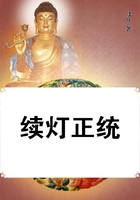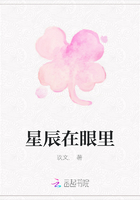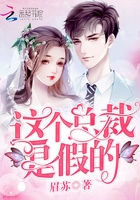无论是文化立场、诗还是生命,哑默的悲剧都在于,他已将时态错置,却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他用古典的过去时态,西方的将来时态,对应了两不顾的现在进行时态:1957年和1966年的现在进行时态。一把资产阶级的小提琴,一片隐士的辋川,一本花花草草的《芥子园画谱》,被强行塞进了锣鼓喧天的工农兵的现场。哑默也带着他的眼睛、耳朵、心脏、英语和贵族般的倨傲,或者说,带着他所理解的过去和将来步入了这个现场。气度不凡,坎壈已生。很快,他就发现,孤立如此轻易地配合了被孤立。由昏暗、可疑到不正确,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解放牌卡车开过来,拉走了他家藏的图书、唱片、字画、古玩和细软,他的任务,就是帮大人誊写检查书、交代书、自白书、供状或交心报告。这个被抛入洪流的年轻人,如同落英,他还能剩下些什么?“重负、修途和长夜”。是的,他还剩下了笔,或者说,还剩下了诗和文学的宿命。最早的那批作品,《海鸥》《鸽子》《晨鸡》和《启明星》,都有个隐喻,都有双望眼,似乎接上了三四十年代的苦难抒情和希望抒情。至于《彗星》,则似乎只有苦难抒情,那种不祥感,虽未成谶,却压低了此后的希望抒情。从1976年到1986年,诗人完成了两部长诗——《飘散的土地》和《湮灭》,前者可以称为“民族情感史诗”,后者则可以称为“个人精神史诗”。从这两部史诗来看,希望抒情的味儿已越来越淡,淡到几乎没有,苦难抒情就益发有了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把个人悲剧,抬升,再抬升,以至成为引发共鸣的时代悲剧。既然能够做到此点,那么,旧式的言语,老派的修辞,又岂容他人指疵?比哑默小七岁的诗人——北岛——早年曾提醒前者,说他缺乏“更深沉更内在的力量”。此言自是不无道理,但是,哑默限于——也可说陷于——西南的群山,限于边陲,限于野鸭塘的农村小学校,虽然也曾读到若干“灰皮书”和“黄皮书”,却并没有隔空猎获某种尖新的“现代性”。哑默只能不断往后退,退到三四十年代,退到艾青、沈从文、林语堂甚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虽说不断往后退,《湮灭》在文体上仍有前瞻性的实验:他自己称为“非模式文学”;到了今天,或许可以称为“跨文类写作”。说到野鸭塘,以及那所小学校,也曾给诗人带来世外温暖和“乡野的礼物”。南有野鸭塘,北有白洋淀,这两个源头性的沙龙,已然成为文化史上的传说。话说远了。且看这个坎壈而忿怒的诗人,“不肯低头事鸾鹤”,却用写作见证了内在的细软和'藜,也见证了历史的心跳——即便是身处“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其十数卷作品,却没有像样的发表和出版。1979年早春,油印的《哑默诗选》发布于西单民主墙——这是个事件;1987年早春,《飘散的土地》最后十一行发表于《诗刊》——这也是个事件。真是雪中之雪,道在山林。“应该有不朽的作品安慰这个世界”,哑默或未写出他心中的不朽的作品,但他的诗与文学,或可与他的情志的芬芳,共同来安慰这个曾经如此苦难的世界。
同类推荐
理直话自爽(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从喧嚣中缓缓走来,如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收拾了一路趣闻,满载着一眼美景,静静地与你分享。靠近它,你会忘记白日里琐碎的工作,沉溺于片刻的宁谧。靠近它,你也会忘却烦恼,还心灵一片晴朗。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散文(2017年第5期)
《散文》创刊于1980年1月,是我国第一家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创刊之初,便确立了思想上追求高格调,艺术上追求高水准的办刊宗旨,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得《散文》成为一份高雅纯净,独具品位的刊物,推出了包括贾平凹、赵丽宏、詹克明、李汉荣等在内的大批优秀散文作家及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社会的认可。从创刊至今,《散文》一直以它独特的魅力力证着自己的存在,坚持呈现当代中国巅峰笔意,鼓励作者表达发现,呈现了一种罕见的沉思的品质和悲悯情怀,是当代文学界尤其是散文界极具分量的文学读本,在读者、作者、文学评论者心中地位崇高,影响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