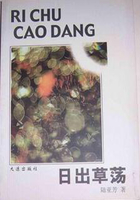好些年了,女儿小灯从南京回来,郁良都会上火车站去接。看到女儿拖着拉杆箱,穿着露膝盖露肩膀的衣服,款款地从站里走出来,郁良的心里就会有一阵惊喜,一阵怅惘。他照例会快步上前,喊了女儿,从她手里夺过拉杆箱。小灯呢,脸上平平淡淡,嘟着嘴说:“叫你不要来接的嘛,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郁良一愣,挤出笑来说:“是想不来的,想想还是来了。反正今天没有事。”说着右手从背后拿出来,变戏法似的,变出一袋枇杷,有时是一袋杨梅,“都是时新水果,你喜欢吃的。”
女儿的房间一直是空的,平时老两口一星期打扫两次,从来不住人。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就是在厅里搭钢丝床,也不能住小灯的房间,她晓得了要生气的。女儿进了自己房间,就会把房门关上,不晓得她在里边悉悉索索忙什么。郁良和她讲话,往往是门里一句,门外一句。
阳光落进天井里,天井里就像注满了橘黄色的水,门一开,这水就溢进屋里来,屋里红木家具便泛出深沉的光泽。不远处有一个古迹园,除了节假日,平时这里都是安静的郁郁葱葱着。郁良已经习惯小灯任性的表现了,他心里对她怀着很深的歉疚。简直不敢回忆,回忆是锋利坚硬的石片,在肚子里一打滚,五脏六腑都要割碎,流出殷红的血。小灯二十七岁时,她决意离开这座温馨、舒适的城市,离开一直陪伴她的父母,到异地去谋生。她略显扁平的脸上渗出了一层层汗珠,细密的牙齿咬住了薄薄的嘴唇,出血了。她的妈妈再三盘问,才得知,处了两年的男朋友提出分手了。男朋友高个子,梳着三分头,还会讲些俏皮话,已经来家里好多次了。女儿无法承受这打击,无法再看见她和他无数次逛过的马路、商店、公园、电影院……
“这混蛋!”郁良发出愤懑的吼叫,似乎比小灯还要撕心裂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知道,还要问我吗?”小灯眼里透出阴冷的光,像一把寒剑直抵他的内心。接着,她冷笑了,“你真是不知道?”
他低下头去,看到了自己的胸脯,又看了进去,仿佛里面有一个黑洞,洞里有模糊而生硬的内容。他跌坐在藤椅上。
她不要郁良送,也不要母亲送。一个人拉着拉杆箱去了火车站。
五年过去了,小灯在南京过得怎么样,郁良不清楚,他只能从女儿电话里的声音来分辨。如果小灯的声音是流畅而轻松的,那就是过得不坏。如果声音烦躁不安,那一定是遇上了不顺心的事情。这时郁良一边听,一边不停地告诫自己,要耐心。他要当一个大容量的垃圾筒,让她尽情地倾倒。然而,女儿从来不谈自己的终身大事,郁良还能忍,但做妈妈的不行,小灯回来,她总在她耳边唠叨。小灯回答得也干脆,“你要是再逼,我会让你们终生痛苦的!”吓得她妈妈脸色发白,从此不敢开口。
然而,最近却有了意外。女儿在手机上说到了房子,她说现在房价涨得太快了,她考虑在南京的新区按揭买套房子。听起来像是随口说说的,却像在郁良心里划下一道深深的印痕。
“对,对,太对了,小灯,你就应该在南京买套房,属于自己的房子!不,不,爸爸妈妈的房子,那一间永远是你的,谁来都不让住。可是,你应该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在南京买,对的!就在你谋生的地方买。”
郁良在电话里、手机上不停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他心里暖暖的,有一股热浪在滚动,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慈爱的、敢担当的老父亲。
“爸爸老了,除了喝点好茶,没什么消费了。我工资不低,以前还攒了一些钱,可以支援你!”
晚上睡到床上,妻子用脚踢他的小腿,说,“小灯怎么会突然想买房子,奇怪呀,会不会有男朋友了?”郁良心里一亮,“是啊,完全有这个可能,以前女儿从来不提房子,而现在居然说想按揭了,这个变化太大了!看来她想筑一个温馨的窝了?”
他又去了火车站。当小灯从车站里走出来时,他发现她和以前不一样了,步子轻快了,脸也变得生动了。郁良去过果园,此时小灯的脸就像挂在树枝上的新鲜的红扑扑的苹果。
他们上了公共汽车,坐定了。郁良忍不住了,大着胆问:“小灯,跟老爸说实话,当然你可以不和我说,不过,你还是应该和老爸说。是不是有了?”
小灯脸上起了红晕,半嗔半喜拍他一下,“爸,你说什么呀!”
郁良懂了。爱情真能改变人!不由心里感慨。不过,找到的真是爱情吗?他还不敢肯定。
妻子已经在家烧了一桌美食。郁良温了一壶女儿红,倒进三个杯子里。他高高举起杯子,小灯也举起杯子,和他重重地碰一下,酒晃出来,溢到了手背上。郁良的记忆中,女儿好久没有这么爽快了。
一壶酒只剩一个底了,小灯的故事就露出端倪了。那个男友不是她一个公司的,却是在同一座大厦里。那段时间真是奇怪,他们每天都会在电梯里至少遇上一次,半年后才有正式的交往。没想到在不少地方,两人都有相近的看法。他们的交往开始还期期艾艾,后来就像燃上药引子一样快速。
妻子用手背抹着眼睛,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么大一块心病就这么除了?她始终不敢相信,眼神还有点迷茫。
郁良闷头喝了一大口,趁着酒力问:“那个,那个……他知道了?”他说得有点艰难。
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问,怕女儿生气,可这是避不开的呀。小灯不作声了,一会,说,“给他看了。”
这句话虽然平静,在郁良的耳朵里却像撞响了铜钟,一时他老泪纵横,都是他作的孽,给幼年的小灯留下致命的伤痕,也在自己心里留下了永恒的伤口。所有的后果都是女儿在默默地屈辱地承受。他想不流泪,但做不到。
小灯从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递过来。妻子也说:“小灯找到了,我们应该高兴才是。”
他接了纸,抹去泪水,大口地呼吸着,“我不应该……”
小灯说:“他也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他明天赶回来。”
天蒙蒙亮,妻子就起床了,她睡不着了。她梦里都在动脑筋,怎么烧出一桌富有苏南特色的好小菜来。郁良是工业大学的教授,明年就要退休了,课时不算多,下午他上完课,匆匆赶回来了。
等待和关禁闭一样难熬,当时针指向五点,大门响了。等小灯把男朋友领进屋了,郁良才含笑站起来,他须有应有的稳重。老实说,他一瞬间有些失望,来人长得偏矮,似乎还没有小灯高,肤色发黑,五官也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和以前那个比,外貌差了不少。这是小灯新的男友吗?女儿按揭买房就是为了和他,郁良的思想像旋风中的几片落叶。
“爸爸!”小灯发现他愣神了,扯了一下他的袖管。
他忙回过神来,招呼男青年,“请坐,请坐。喝茶。”他把一盅铁观音茶送到他面前,手有点哆嗦。
此刻的小灯显得大方主动,她说,她的男朋友姓姜,单名叫姜弘。郁良“哦哦”地应着,心里接着想,就是他“看过”小灯了?心里有点不惬意,一时又静下来。
小灯说:“爸,您怎么不说话?”回过头对姜弘说:“我爸的口才可好了,上课时口若悬河,学生就喜欢听他讲课。”
郁良知道自己不对了,强打起精神,热情地和姜弘说长说短,顿时空气活泛起来了。
妻子很快摆出一桌菜了,她的任务就是让未来的女婿吃好。她不停地替小姜夹菜,糖醋排骨、响油鳝糊、龙丝卷、香酥鸭,他碗里始终是冒尖的。她一边夹,一边嘴里说:“多吃点,多吃点,最好不剩。你们嘛,将来两个人,菜不要烧得太多。”姜弘说:“烧得多没有关系。”妻子说:“我们小灯是从来不吃隔夜菜的,一点都不吃。”姜弘笑了:“我知道。”妻子说:“那谁吃?”他说:“我吃。”一点都不含糊。小灯脸上就有得意的神色。
郁良有些感动,看来他是真的对小灯好。
就这样,毛脚女婿算上过门了。事已如此,没什么可以计较的了。郁良私下和女儿谈过了,家里有积蓄,房子的首付款由父母出,按揭主要由他们还。不过,郁良停了停说,“如果需要,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援。”小灯眼睛红了,爸爸妈妈,你们对我太好了。
接下来,该亲家见面了。姜弘的母亲早些年就过世了,就他父亲一个人了。小灯说:“姜弘说了,他爸身体不好,不一定要见的。你们以后见面好了。”
郁良说:“不行,这个仪式是一定要有。”
这是大事,不能在家里请,他去订了饭店,是市里一流的大鸿运饭店。听说老姜高血压,经常头晕,郁良想起有朋友送过他天麻、灵芝之类,都没有吃,从柜子里找了出来,给老姜带去。
姜弘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只不过后者更老一点,胖一点。给人印象深的,就是在脸中央,坐着一个毛孔粗大的发红的蒜头鼻子。郁良忍不住想,将来姜弘老了,鼻子是不是也会发红呢?说到穿着,老姜也是不伦不类,郁良是一个讲究衣着的人,可是你看他穿的,外面一件深色的半高领,里面却是一件灰色衬衫,头颈这里乱七八糟。郁良心里直嘀咕。
郁良带了礼物,而对方是空着手来,这倒也算了。
一时上菜了。郁良请对方动筷,老姜也不客气,闷了头吃。小灯是个乖巧人,见双方没有多少话说,就夸起姜弘来,说他十分钻研,来公司不过三年,已经是一个部门的头了。姜弘给表扬得不好意思了,转手把花献了出去,“都是爸爸教育的。”郁良就接口:“姜还是老的辣。”老姜也不谦虚,一边专心对付碟子里的大虾,一边说:“当然嘛。”
郁良心里就笑,这倒是个好为人师的主。
话题有所转移,小灯说:“网上有段视频,是两个著名学者的发言,公开向市领导提意见,批评拆迁方式粗暴,破坏了古建筑和古文化,还要把我们屋后的老城墙拆了。”
老姜的脸已经被酒涨红了,他抓了餐巾擦油腻腻的嘴巴,扔出一句话,“这两个人我知道,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
郁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什么,怎么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什么意思?他想忍,却没有忍住,“我们现在拆迁就是做过头了,不管什么古建筑,也不管你老百姓怎么想,统统抛在脑后。这两个学者我都认识,我们是朋友,我想他们是出于真心,怎么是翘尾巴呢?”
“哼!”老姜从酒糟鼻子里喷出一股气,“这两个人是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吗?快五十年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我对他们知根知底,当年整得还不够!”
郁良浑身燥热起来,像有一头黄蜂绕着他的脑袋嗡嗡飞。当年整得还不够。这话太邪乎了,当年多少人妻离子散,上吊、投湖,还不够?怎么样才叫够呢?
郁良的眼里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雾状样的东西,那片雾变幻着,变出人的形状来,就是那两个学者,一个是历史系的,一个建筑系的,他听他们说过,以前被整得很苦。
那片雾继续变幻着,变出了另一个人,郁良细看,就是自己的父亲,当年吴东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常戴一顶鸭舌帽,后来天天斗他,帽子早不见了,露出头发稀疏的脑瓜,胸前挂一块小黑板一样大的牌子。郁良老听他念叨一句话,“有辱斯文,有辱斯文……”一天夜里,他投了孔雀湖。郁良胸中生出一股气,急剧地扩大,把心脏压得变形。他的身子前俯,胸膛抵在桌沿上,“你太过分了,知识分子还整得不够?怎么可以这样说……”
老姜也不示弱,两排大牙咬碎一块酱肘,吞进肚里,说,“如果整够了,整怕了,今天他们还敢趾高气扬?”
郁良想,我说了,这两个学者是我敬重的朋友,而且,他应该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他却一个劲说整得不够!什么意思,是有意挑衅?还是无法控制真实的内心?郁良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什么,肯定是激动了,筷子从手中跳出来,掉下了地,葡萄酒把面前的白桌面染红了一块。
老姜也动怒了,放下筷子,抬高了声音,摆出不示弱的样子。
妻子着急了,在台下扯他的衣角,“怎么可以这样?”
小灯说:“你们二老犯什么病了?今天是亲家见面,不是让你们吵架来的。”姜弘也说:“是我引起的,都是我不对。爸爸,别说了,求你了……”
酒宴不欢而散。郁良走出包间时发现,礼物安然在桌上,没有送出去。
夜深了,郁良躺到床上,又坐起来,心里一股气结成了块垒,无法消除。女儿房间的门紧闭着,还亮着一盏小灯。郁良竖了耳朵听,似有嘤嘤的抽泣声,时断时续,仿佛是夜风中的细雨,寒流中的落红,梦呓中的独语,徐徐向着不可名状的前方流去……
妻子说:“睡吧,睡吧,明天再说了。”
第二天,他去了一个地方。昨天酒席上,他得知了老姜原来在的工厂,郁良恰好有个朋友也在那里待过。费了点周折,他找到了那个朋友,得到了准确的信息,老姜曾经是工宣队的骨干。
回来的路上,郁良始终在紧张地思索。小灯是要和这个人的儿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床上啊!从遗传基因的角度看,他会给姜弘植入什么呢,偏见、固执、冥顽不化?他不能不担心。亲家是什么,是比兄弟、邻里、朋友都重要的角色,而现在,他却选择了这么个蒜头鼻子。他养老只能靠小灯,那将来势必要和这个蒜头鼻子为伍,见了面就乌眼鸡似的斗。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另一个女儿可以作替补。他实在不能接受。
郁良的眼光移出了紫砂茶壶,移到了女儿腰际、前胸,却着了慌似的跳开,仿佛误入了他的伤心地。他满怀慈爱看着小灯,抓了她的左手,放进自己的掌心。她却愤愤地拿开。他心里便叹一声。他小心地选择字眼,尽量婉转地说出心中的意思。
他发现女儿眼里透出一种陌生的冰冷光亮,她的神色在急剧地变化,如同天气在顷刻之间进入深秋,踏在寒冬的门槛上了。他知道这对女儿的伤害有多大,却是不能不做的选择。他说:“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找过姜弘,和他明说了,我们两家不合适,这个关系只能中断。”
小灯的身子索索抖着,脸像雪一样苍白,“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你太自私了!”
“不是,不是的。”他极力辩解,“他的父亲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还说那时候还整得不够,这是什么混账话啊!”
“我是嫁给他,不是嫁给他的老爸!”
“你没有说错,亲爱的女儿,可是,你要进他家的门,我只有你一个女儿,我找的是亲家,不是冤家……你能说他的儿子没有他的遗传基因?还有,你的爷爷,他是一身正气的知识分子啊。”
郁良觉得自己铮铮有理,然而在小灯面前,每条理由都变得软弱无力。
“爸爸,你忘了?我胸前的伤疤!它还留在那里。”
她的声音如同一条带电的鞭子,抽得他身子和灵魂一起蜷缩起来。
啊,久远了,那是小灯三岁时候。那时他们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只有一个房间,还不带卫生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要给小灯洗澡了,郁良就在屋中央放下一个大木盆,妻子烧了水,他端来一大锅开水,倒进木盆。小灯已经脱了外衣,只穿着内衣,在盆旁的高椅子上玩耍。郁良就要去兑冷水,忽然电话响了,他心里本来有事,他班上的一个同学上体育课忽然昏倒,他护送去了医院,说要检查观察,待了一个小时,他关照了护理的同学才离开,会不会又有情况?
郁良奔过去接电话,还好,医生说问题不大。他刚松一口气,却听到身后迸出一声惊人魂魄的哭叫,他回头,小灯掉进盆里了!他疯了一般奔过去,从开水中捞起了小灯,又抱紧女儿,疯一般冲出门,妻子跟在后面跑,长发披散,他冲进了医院。
小灯是迎面扑进盆中的,胸脯大面积烫伤。从此,丑陋的伤痕一直跟随着小灯,她长大了,伤疤似乎也随之扩大。这是女儿的隐秘之伤,也是他永远自责的心灵之痛。那个留三分头的男友,就是看见了伤疤而离去的啊。
郁良顿时手脚冰冷,有一种说不出话的窒息。
小灯和姜弘失去联系了,微信拉黑了,手机也停了。小灯找到他家去。老姜眼里闪出恶毒的光亮,说,“我早对儿子说了,跟了你不会有好果子吃。应验了吧!”
小灯找到南京去了。公司的人对她说,“姜弘已经辞职。”她吃惊得合不上嘴。又赶到他住的地方,房东对她说,“已经退租,不住了。”小灯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商店、广场、文化中心、电影院,他们以前去过的地方,她都去了。她张着两手,眼睛光光的,像一个白日梦游的人。蓦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跑上去,从后边勒住那人的腰。那人回头,哎,认错人了。
半夜了,小灯忽然在床上号啕大哭,像是荒野上母狼的嚎叫,久久不停息。房东对她说,“我的房客都要吓跑了。如果你还这样,只能请你走。”
小灯变得疯疯癫癫,不能上班了。公司打电话给郁良,他和妻子赶了去,把女儿接了回来。火车上,他心痛地看着女儿,两个月前,她还是一个新鲜红润的苹果,现在却成了一个风干的失了颜色的果子。
他不住地想:是我毁了女儿的幸福吗?可是,我总不能不顾自己晚年的安宁吧。又想起父亲的惨状,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愿意呀。我错了吗?我作了什么孽啊?他不停地在心中替自己辩护,仿佛在一个几近干涸的井中打水。
有了父母的悉心照顾,小灯的状态似有好转。她忽然不说话了,有时一整天都没有一句话,关紧了房门,不知在屋里干什么。
他和妻子就在房门外坐着,两双眼睛对视,目光重重地落下。我该怎么办,他在心里挣扎。妻子伸过手来,放在他手背上,轻轻抚摸。
一天,他在天井里枯坐,闭上眼,阳光酥酥地照他身上。忽然听到声响,他睁了眼,看见小灯从屋里探出头,跑到大门边,开了门,姜弘出现了。两人抱在一起,说了几句话,小灯又跑回房间,再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姜弘接了,两人快步朝门外走。
郁良想站起来,手脚却麻了,动弹不得,要说话,却没有声音。两个人出门了,郁良挣扎了几下,忽然能动了,很快就到了门外。有一辆出租车,两个年轻人正在上车,车里还有一个人,似是老姜的脑壳。车门关了,车子开了。
郁良急了,他忙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追前面那辆车。咬住了,路上满是人和车,红灯绿灯,急停急驰,真有美国大片的味道。眨眼到了火车站,两人下车了,郁良跟了上去。他们发现他了,手拉着手,快步跑起来。郁良划动两条老腿,呼呼喘气。
两个人的手断开了,寻找着,又拉到了一起。他们跑上天桥,不跑了,手牵着手,走向栏杆。郁良有不祥的预感,高声喊起来。小灯听见了,朝他这里看,他看清女儿的眼里有无尽的哀怨和怜悯。小灯掉过头,和姜弘一起,跨过栏杆,从天桥上跳下来。在灰蒙蒙的空中,他们的手还连着,像一对绿颜色的卡通人。
他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叫,醒了,他还坐在天井里。是一枕黄粱梦。他听见了自己发出的声音,额上渗出冰凉的汗水。
妻子过来说:“你怎么啦,叫得好吓人。”
房间门开了,小灯的脑袋伸出来了,径直走,开了大门出去了。郁良让妻子拉了他一把,才从藤椅上站起。走到门口,他扶着门框看,小灯撒开腿,沿着马路向前跑去,嘴里发出含糊的欢快的声音。在路另一端的树下,站着一个不高的男人,就是姜弘。他先是不动,后来也跑了几步,两人遇上了,愣了下,抱在一起。
郁良使劲揉眼睛,这不是梦。
一个晴天,郁良和妻子到火车站来了,他们是来送小灯、姜弘去南京的。这次带的行李不少,郁良拖了一只拉杆箱,还拎一只包,进了火车站,全部交给了姜弘。
郁良拉住小灯,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递给她,说,“这是爸爸妈妈为你们准备的,收好了,给你们买房子付首付。”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小灯眼睛湿了,“你们对我太好了。”
郁良的眼睛也湿了,“我欠你太多了……”
小灯拽住他手臂摇,“爸爸,你不能这么说,不能……”
郁良点点头,“我不说。”女儿的气色好多了,沮丧、憔悴都没有了,又像一个挂在枝头的红润的苹果。他看姜弘也顺眼了,可能看习惯了。
他又从包里摸出东西,是没有送出去的药,交给了姜弘,让他有机会带给他的老爸,让昔日的工宣队骨干把脑病治好。姜弘接了说:“我替我爸谢谢您。”
郁良冷冷一笑,心里说,我不会再看见他了,除非他换一副脑子,但可能性是零。
他们上车了,列车走了。郁良没有马上离去,两条铁轨在他眼前无尽地延伸,把小灯送向远方。他知道女儿是去南京,又似乎不知道她去哪里,仿佛去一个无可名状的地方。他心里突然疼得厉害,流泪了,一时老泪纵横。他弯下腰,捂住了胸口。妻子紧张了,“你怎么啦,你不舒服吗?”他大口地呼吸,用手背重重地把泪抹去,说,“我应该高兴,你说是吗,应该高兴。”
站台上的人都走了,一辆列车开进来,没有停,快速通过。这里视野开阔,四周是原野和青黛色的山岭,景色苍茫。又一辆列车通过,又一辆列车开出。耳边是呼啸的风声,云在天上翻滚,一群褐色的鸟从野地里飞起,发出掀动铁皮似的鸣叫。恍恍然,他看见了父亲,他赤头跣足在地下走,嘴里喃喃自语,“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他又一次流泪了。
一缕阳光从云层中穿出来,直直地投射在面前,光柱中翻卷着万万千千的尘埃,如无数匹野马在扬鬃奔腾,他定神看,仿佛随之一起翻滚、升腾。
2017年6月8日写于南京老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