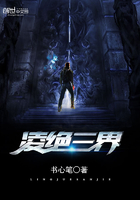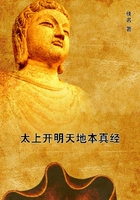“呵!”亓野嘲讽一笑,以两手指聚力,从已经有些缺口的剑身使力,残缺的一段顿时掉落,捏住那断掉的一段,亓野暗暗使力,那断剑立刻以极快的速度飞向远处的林太守,携着万钧之势,从发顶略过,将其发冠削落,掉下一片片的黑发。
“可惜了。”亓野叹一口气,仰头望天,将另一段断剑扔在地上,大有一副束手就擒之态。
“杀了他,给我杀了他!”
死士得了命令,捏着短刀就重新扑上来,一把短刀从侧面切过来,亓野避闪不及,被刺中右胸口,早前的暗伤一起发作,一口鲜红的血顿时从喉头涌出,一阵腥甜。
见亓野重伤,那林太守立时的夺过一个死士的短刀,一脚踹开挡在亓野身前的无期,短刀就要重重的落下……
意料中的血溅当场的画面并未出现。
“狗官!”一个粗犷的汉子及时的将人连同短刀踢飞出去,“殿下!”
亓野半眯着眼睛,将面前的人认了个清楚,乃是镇南王身边的第一猛将魏钊。
这魏钊素有“飞虎将军”的名望,为人最是骁勇。
“王爷还在后面,随后就到,担心殿下安危,这才嘱臣前一步来。”似是清楚亓野心中的疑惑,魏钊解释道,“微臣来迟,还请殿下责罚!”
亓野摆摆手,眼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只吩咐一句:“小心,都是死士!”
魏钊是个武将,没有朝堂上文官们的弯弯绕绕,一向只将皇明放在心上,此刻听闻这林太守居然敢豢养死士,一双虎目睁得硕大,随即怒斥道:“直娘贼!好你个林肴!”
骂完,更是挥舞着手中的大刀,一把扒开身前的一个死士,恨不能上前将人的首级给带下来。
林肴应是未曾料到这种情况,此刻见着魏钊到来,又听闻镇南王随即便道,早已变了脸色,两股战战,心中恨骂杨子甫先一步离开。
心中虽是惧怕,嘴上却依旧不曾让人:“哼!我当是谁,不过一个莽夫!何足惧?!”
眼下实在是个两难的境地,但不论成败,他已是退无可退,想明白这一层,林肴一脚揣想身旁的侍卫:“还愣着干嘛?还不给我放箭?杀!杀了他们就没事儿了!”
“大胆林肴!谋害皇子,还不束手就擒?”一阵洪亮的声量从院子外传来,接着便是一阵井然有序的迈步声,亓野松了一口气。
镇南大将军的人一到,立刻围满了院子,原本漆黑的夜,此刻被照的恍若白日。
“完了,完了,完了……”见到镇南王的大军,林肴是彻底凉了心,恍惚着,也听不见左右的声音,嘴里只不断的念叨着。
“将林肴及其手下羁押,若有反抗者,就地格杀!”镇南王下了命令,浩浩荡荡的大军立刻开始行动,这都是些在战场上杀敌的军士,身上带着杀伐的煞气,林肴的侍卫虽有训练,却终日养在深宅里,自是不可与之相比,只单单见了这阵势,立时的溃不成军,乖乖的被俘虏带走。
“殿下!”镇南王一眼看见重伤的亓野二人,将人带走,传唤大夫。
……
亓野是昏迷了一日醒来的,又因着受了重伤,回京的路上一直在马车上休息。
因着是镇南王回京,镇南王又是素有守疆卫土的“战神”名号在外,更有苏陵太守林肴被押解,街道周边浩浩荡荡的围满了观望的群众。
一则是为了瞻仰镇南王的圣容,二则却是为了八卦林肴及满门下狱的真相。
“哎,我听说啊,这林肴胆大妄为,竟然谋杀皇子!”
人群中显然有些小道消息灵敏的好事之人,缩在角落里扬声唤了一句,顿时乌压压的聚拢了大批观众。
“不知是哪一位皇子啊?”发问的是一位士子扮相的人,像他们这般要入仕的,自然是要清楚一些朝政大事和动向。因此,周遭倒是见怪不怪,反而兴致冲冲的盯着人群中间的好事之人。
“这……这,这可是机密!机密!”毕竟是普通群众,便是有些渠道,哪能清楚的和到了现场似的,原本就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说出的话,此刻被这么的一问,立时的窘迫起来。
“嘁!”围观的也不都是傻子,见此,纷纷作鸟兽散。
“我倒是听说这林肴之子林弋桢还在逃,方才我进城时见着官差正在张贴皇榜通缉他呢!”有一客商扮相的人插话。
“可不是嘛,这谋害皇子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便是逃了又如何,终究是躲不过的。”有人接了话茬儿,接着又道:“想不到这林弋桢竟也不是酒囊饭袋,照说他爹犯下如此罪行,他居然没被吓得尿裤子,倒还能不声不响的逃走!”
人群中又是一阵议论纷纷。
远处的南北街角各蜷缩着一人,一个是笑的明媚不知事的女子,莹白的小手握成拳,手心处紧紧地攥着一枚水滴状的玉坠,另一只手伸出食指来,满心欢喜的戳着摆弄;另一边,是个带着斗笠黑纱遮面的男子打扮的人,望着镇南王身后的马车盯的出神,眼中是疯狂的刻毒颜色,手握成拳垂在身侧,片刻后上了一辆马车离开。
……
这几日的朝堂之上可谓是风起云涌,各党派之间的利益角逐立时的争锋相对起来。
眼下,镇南王平北疆而归,自是功不可没,与之相随的是六皇子亓野。
人人都知道皇上最是喜爱六皇子,可是这喜爱从来就不单纯,怎么说呢,皇家却不稀罕的就是所谓情分。相同的,镇南王虽是当今圣上的同胞兄弟,但皇家向来无情,自古便有功高震主,此次又是大功勋,局势怕是……
而另一边,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猜到,林肴突然地发难不会简单,皇储之争历来龌龊不堪,只是,林肴藏的深,平日里很难看出动向,那么……是哪一位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