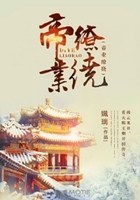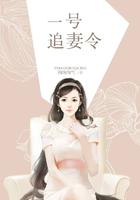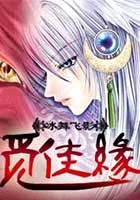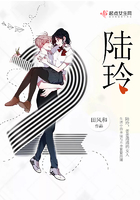程学理是北宋理学的主要奠基者程颢、程颐一门的嫡传后代,出生于集“程朱理学”之大成者朱熹的故里古徽州婺源,也是深得朱熹学术精髓的鸿学之士。据说他出生时,天上闪着万道霞光,一道彩虹横跨南北,山野到处奇花怒放,数日不谢,百鸟齐鸣,群兽飞奔。年轻时他就熟读古书,声名远扬,他十六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长得清秀,风流倜傥,被乡里学子称为“旷世神童、天才少年、朱熹转世”。
他少年得志,一举成名,源于他十六岁就完成了一篇广被流传的惊世奇文《九子评说》,他把自古以来的读书人分成九子,即孝子、学子、赤子、君子、游子、浪子、竖子、孽子、戏子。他最推崇的是“上三子”,他认为自古以来读书人能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孝子,这种孝就是中华文明的灵魂和精髓,这种孝分小孝和大孝,小孝是孝父母、孝师长、孝家族,大孝孝的是民族、国家、天下。天下指的是什么?天下指的就是我们认识的天地宇宙,万物生灵。其次就是学子,真正的学子不是为功名利禄、科举状元、出人头地而读书的,而是为天下苍生读书、探索天地宇宙的真理、天下人排忧解惑而读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其次的是赤子,读书人最起码要对国家民族保持一种拳拳赤子之心,要能以纯洁、真诚、善良、自然的心态,去追求真理、探索世界,光明坦白,勇往直前。他在文章中还说,如果读书人达不到“上三子”的标准,最低也要守住“中三子”的底线,做一个有学问、有修养、有道德的正人君子;即使漂泊终生,身不由己,也要做一个不忘故土、心怀祖国、落叶归根的游子;即使误入歧途,终生流浪,也要做一个重情重义、敢做敢当、勇于回头金不换的浪子。他在文章中特别批驳了被视为读书人耻辱的“下三子”,首先是竖子,指那些不学无术、盲目自大、沽名钓誉的读书人,比他们更可恶的是那些出身高贵的纨绔子弟,他们皮囊空空,无所事事,从小养尊处优,却要附庸风雅,故作高深,他们是亵渎圣贤的假读书人,其实他们从出生到离世,都是一群不可为伍的祸害,除了糟蹋粮食败坏社会风气,毫无作为。但是自古以来,穷不长根,富不长苗,富贵不过三代,多少帝王将相都是风吹雨打去,何况这些跳梁一时的孽子,所以他们可恶但不可恨。真正可恶又可恨的是那些满脸仁义道德,写得一手道德文章,一生把读书当演戏的文人墨客,他们是历史上最大的戏子。他们常常高登大雅之堂,高谈阔论,代表国家民族人民,私下却专干肮脏污浊的勾当。他们阳奉阴违,言行不一,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灵魂早已比他们的躯体提前消亡。自古以来的贪官污吏、卖国大盗、文痞奸臣无不是从这些读书人演变而来的,他们就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人,他们是读书人的大敌大耻大害,却又千代不绝,万年相传。
程学理的《九子评说》一经问世,立即众说纷纭,震动整个皖南学界,被誉为“旷世奇文”,也得罪了一些达官贵人。但那时的程学理年少气盛,从不把那些老朽、功名官位放在眼里。
在他考取举人那年,县府官衙牵来红头大马要他骑上游街,他却说:“有我老母亲在世,我哪能享受这等荣耀?没有母亲的辛苦,哪有我的今生?”
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先磕头焚香,禀告先祖,然后把他老母亲抱上马背,把那大红花给他老母亲戴上,最后把鞋子脱下挂在胸前,赤足牵着马,在一片锣鼓喜乐中,带着他老母亲一起去游街,顿时轰动全县,无数人挤满了大路两旁,一时传为美谈。
有衙吏告到知府,说他违背朝廷规矩,但知府大人却对他颇称赞,说程学理少不更事,孝心可嘉,并要将爱女相许。但被程学理断然拒绝,他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母亲早已给我定下娃娃亲,母命断不可违。”
他母亲给他定下的这门娃娃亲还是在他周岁时,他得了天花,生命垂危。他母亲请来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这小鬼的命已不属阳间,能否把他的命拉回来,就需有个命硬的人把他拉回来。”
他母亲吓得面色全无,忙问如何解救。那算命先生点拨道:“马上给他寻一门娃娃亲,找一个命硬的女娃把他拉住。”
他母亲立即按照算命先生算定的生辰八字四处寻找,先找了几家人家都不答应,后来好不容易在几十里外的山里找到一家,愿救程学理一命,那家悄悄地收了丰厚的彩礼,但有个要求,就是一定要保密,不得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他的命救不回来,就当什么事都没有过。所以这门娃娃亲只有他母亲知道。如果他不认这门亲,也没人会说什么,但在他母亲心里,他的命就是那个大他一岁,命很硬的女娃救回来的。
程学理知道这门娃娃亲后,就一直铭记在心上。在考中举人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娶亲,他和母亲商定,重又请了个媒婆,严格遵循皖南山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明媒正娶,并严格遵循说媒、行聘、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房、回门这九道程序,从头一道道做起。
程学理做的每一道程序都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后来成为大家传颂的表率,成了一些人效仿的榜样。他说:“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不依,那都是几百上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都有很深刻的道理在里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忘了老祖宗的规矩,那就是忘本,那就是不孝。但是对于老祖宗的规矩,也不能刻意死板,也要活学活用,不断改进才对。”
程学理做的第一件事说媒,就没有请媒婆,而是自己亲自找上门去,自己给自己说媒。他对岳父一家人说:“说亲这等大事,何须媒人中间周旋,我自己的事只有我自己最能说清,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何须外人从中搅和,来回传话,多生枝节。我们这门亲事,我母亲从小就定了,我奉母命成婚,义不容辞,望岳父大人成全。”
他岳父一家人见到举人女婿,喜从天降,哪里还有多话,连声说道:“一切都由贤婿做主,所有的规矩都由贤婿自定。”
程学理说道:“多谢岳父大人体谅,该讲的规矩一样不少,我只求能简便一些罢了。”
到了行聘之日,程学理独自一人牵着家里唯一的那头毛驴来到岳父家下聘礼。他岳父感激不已地说:“贤婿为了十几年前的那段没成文的婚约,放弃知府贵婿不做,放弃那份荣华富贵,我哪能还收你的聘礼?你们母子二人从小孤苦伶仃,只有这一头毛驴相依为命,你快快拉回去吧。”
程学理说道:“小婿虽家境贫寒,但该讲的规矩不能不讲,我知道你从小把女儿养大,含辛茹苦,耗费了多少心血。再重的聘礼也不能弥补你们的付出。我现在只有用这头毛驴来表达我的心意,但我会用一生来慢慢报答你们的。”
程学理的举动早已使岳父一家大为感动,接下来的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房,一切都是照程学理的安排行事。程学理并没有因为岳父一家的厚爱而有任何怠慢,都是由他亲自按规定程序严格完成。
他虽数次亲自去岳父家商谈亲事,但他都严格遵守着女方家的最后一道底线,从没提出过要见女方一面的要求,而且一天来回一百多里,不管有多辛苦,就是遇到刮风下雨,山洪暴发,他也都是来去匆匆,即使岳父全家出面挽留,他也从没在岳父家留宿过夜,按照规矩在没成亲前是不能求见女方的,更不能在女方家留宿,那都被视为对女方的不尊重。
直到拜堂闹洞房后,他揭开新娘的红头盖,他才第一次看到新娘春秀的脸,她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算难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山里理家过日子的女人。他没感到惊喜也没有感到失望,他唯一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她和他娘一样,也是一双小脚。他良久地捏着那双藏在绣花鞋里的小脚,只说了一句:“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双小脚,以后谁也不许裹小脚了。”
新娘春秀听到他的第一句就是这,以为他是嫌弃自己,吓得小声抽泣起来。他忙安慰着:“这不是你的责任,是我们这里的封建陋习太深厚了,要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慢慢改掉。”
春秀受宠若惊地说:“先生是文曲星下凡,我是个不识一字的山里女娃,哪能配得上先生你啊!我只求能一辈子给你做一个丫鬟,给你烧茶递水、洗衣做饭,伺候你一辈子。”
程学理说:“此话差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无论我将来有无前途,你都是我的糟糠之妻,金山银山可丢去,糟糠之妻万不可丢啊。你不识字又有何妨,女子无才就是德呀,你只需给我在家生儿育女,照顾老人足矣。”
新娘春秀这才定下心来说:“先生放心,将来不管你远走何方,出去多少年,家中有我,一切都不用你牵挂。”
程学理说:“女人就是家,有了你,我就有了家,就有了一辈子的牵挂。好男儿志在四方,报效国家,不管我将云游何方,我都是皖南山区的儿子,是这一片山水养育了我,我的根都深扎在这里。我如果是天上的风筝,你就是牵住我的那根线。我们皖南女子要的是德,不是才貌啊。我是读书人,一定会牢记圣贤的教诲,为人师表,做人表率。”
新娘春秀感激得泪流满面地说:“我前世积了什么德呀,我家祖先积了什么德呀,让我这辈子能嫁给先生你呀。”
三天后,他陪新娘春秀回门时,岳父一家已把他视作神明。他岳父说:“你虽是我女婿,却比我儿子还亲,人家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家不信这个,以后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你只管放心去京赶考,去奔前程,家里的事都交给我们。”他这才发现岳父家原是个殷实人家,有好几座茶山。
婚后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春秀特别勤劳能干,特别孝顺,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把他和全家人都照顾得周到服帖。他开始感到这门亲事是多么的正确,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有老天注定,给他安排了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媳妇。家有贤妻,万事不愁,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学业和前途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