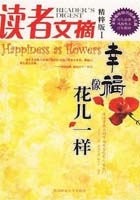“姑娘,下雨了,可来店中歇歇。”
“也好。”淅淅沥沥雨声将她的声音包裹在湿漉漉的水雾里,让人不是很能听清楚。
恍惚间她笑了笑,踏着地面上坑坑洼洼中的积水走进店中来,她在店前干草垫上刮去靴底水渍,用清朗的嗓音说道,“一盏热茶。”
约莫是有月余了,她日日都来这里,就在路口前的石桥上,或坐或立,日日夜夜,往复如此。
“姑娘可是在等什么人?”
“是啊,他让我在这等他,可我稀里糊涂也不知到什么地,好不容易找到这儿。”
“姑娘会不会寻错了地方。”
“那不会,你家后头那李府的钱庄不是被土匪烧了吗?那定不会认错的。”
店家应承着笑了笑,毕竟这钱庄大火烧起来,竟然没有波及自己的小茶楼半分,正是烧了高香阿弥陀佛了。
“近来天气湿凉,姑娘,这盏五花茶,你慢些饮了吧。”
“谢了。”
“姑娘等的是什么人?”
“苏牧。”她抬起茶盏,轻抿了一口,尚觉得有些烫,便又放回桌上,继续说道,“我并不知他是何人?”
店家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也罢,即是他不再来,我也不必再等,且行我事,就当萍水相逢一场。”
说这话的人,的确是从那天起,没再来过。
楼外还是细雨蒙蒙,一盏茶落,她付了钱,回身就钻进了雨雾里。
“姑娘。”
她应声回过头来。
“姑娘可留下姓名,待到那位公子来了……”
“司空凌。”未待店家话语落定,她便回答道。
言罢,她站在雨里,回头隔着朦胧雨丝看着一半淹没在烟雨之中的楼阁,须臾,她又道,“你呢?怎么称呼?”
店家一面拾起门梁前一把雨伞,一面应道,“钟年。”
钟年正想抬头将雨伞递出去,恍然间,那人早已远去,消失在了茫茫雨雾中。
苏牧,想必这江湖中的人,对这个名,已是早有耳闻。兰亭尊师陈昱门下最为得意的弟子,据说是十六岁就已自创剑法,以一己之力放翻了一众师兄弟乃至师尊长老,多少闻其名而去挑战的人,皆数败了下来。就连当年诸雪武会第一人九峰楼岳嵩都曾败给了他。自然他也是这一届诸雪武会兰亭会选出参加武会的弟子之一。
仰慕他的女子,又怎只其一个。
钟年看着屋外雨中匆匆行人,来来往往,像是一场场无聊透顶的戏剧,每天都一如往是地轮番上演着,从来都不会疲倦,也从来都不会厌倦。
茶楼里人们每天一如往常的资谈,说书先生每天说着一如往常的故事,戏楼里戏子每天唱着一如往常的曲儿……
至于后来她再见到的司空凌,是在滨州官府的刑场上,所行之事那更是惊世骇俗——杀了程家庄满门,独放走了几个奴仆。至于是何缘由,并不知晓。
程家人是当地大户,向来行善,开仓济粮,接济了不少穷苦百姓,却在一夜之间血流成河,令人唏嘘。
而犯下这罪行之人,当是令人发指,千刀万剐难解其恨。
滨州官府判以斩刑。
而此刻刑台上那人,只是不以为然地勾起嘴角一笑,似乎是对死亡、对刑台下的芸芸众生、对身后油头粉面的官僚使出了最大的嘲讽。
可就在那番嘲讽笑容之下,一瞬耳边呼呼作响,破空一道黑影闪过,接下来的戏码便是,死囚斩刑当场逃离,众目睽睽之下说了一句“我还不想死。”随后逃之夭夭。
只留当街围观叫骂的群众和坐得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面面相觑。
至于司空凌怎么逃走的,钟年也是实在没有看出来,她也就跟风瞎凑热闹,对于这些人来说,兴许那茶楼里说书人讲得绘声绘色的故事还没有当街斩首这种血淋淋的场面吸引人,甚至还有抱着四五岁小孩来的。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有些虽不明发生了什么事,然仍是跟着别人破口大骂着。
钟年也见过几次此番场面,她自认自己并不是什么好人,当然也没有高高在上批评同类人的资本。
三人成虎,人云亦云。
次日,茶楼外出现了一个人,素净衣衫,身长屹立,在混杂纷乱的人群中显得此人极其突兀,甚至是与俗世格格不入。
他手中拿着一张不知何时飘落下的当街贴出的公示,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兴趣还是其他什么缘由,他愣是盯着那张告示看了许久,最后波澜不惊地将其折叠整齐,塞进了自己布囊里。
这个人钟年之前是见过的,正是钱庄出事那几日,倒是经常见他在这条街上晃悠,想是在寻什么人。
“姑娘。”
钟年回了回神,这才见那人已经走进茶楼来,正欲与她说什么。
他恭手一礼,“敢问……”语出二字,他又微微顿住了,似乎是感觉这番有些唐突,然再思虑重新整理语言。
“司空凌?”钟年见他如此,觉得颇有些意思,便直接说道。
至于最近能贴出的公告,无非就是对司空凌的通缉令罢了,毕竟一个死囚出逃本就不是什么小事,那些官府的差兵几日来可算是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抓到司空凌就大卸八块,如此,也难解心中不快。
那人微微抬眸,却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任何神情。
看来传闻中泽仁处善修身律己的苏牧,还是个不言苟笑的公子。
又或许是她自己问得太过直接。
“她来过。”他淡淡说道,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情绪,不过他倒是肯定司空凌来过这里。
“杀人偿命,不过如此。”钟年一面朝他笑了笑,一面盯着旁边店小二手指飞速拨打着的算盘珠子,“世人皆有好生之能,正如告示上所说,她逃走了。”
他也没说什么,再微礼表谢,便转身走了。
近来天气多雨,白日些放晴几个时辰,方到入夜时分,又下起了雨,洋洋洒洒。微雨拍打着屋瓦的声音,同桌前湿气朦胧而微醺的灯火零落不定。
街道前石桥对面楼中隐约传来戏娘悠悠婉转的歌声。
春秋亭外窥啼影,
朱楼阁上忆断肠,
休恋逝水别余恨,
早悟兰因自思量,
韶华无言人生遇,
残生复安德馨香。
随着那哀婉的歌调,也不由自主地用木筷敲起了桌前的陶瓷茶盏。
“这对面楼唱戏的小娘子是不是换人了,这声音怎么听着比往常清丽些,倒没有这么悲怨了。”店小二一边收拾着桌椅,一边回头朝此时正无聊把玩着茶具的钟年说道。
“自然是要换人的,再清丽优美的花儿,都会日渐衰落的。”钟年懒懒散散回他道。
“唉,也是,枚娘也老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平常人们爱听的曲儿,枚娘唱得好,十分感情她唱出了十二分,人们却又不爱听了。”
“是啊,枚娘唱得好,可人们却不再爱听她唱的曲儿了,终归还是会有新的姑娘来代替她的。”
“也不知枚娘走了没?不若他日请她来店中喝盏茶,了示送别。”
“走了,昨日便走了。我昨日见她走时,她什么也没带,空落落的一个人,就连那套她最爱穿的红色戏服都只能留下,说到底,她在戏楼里这么些年了,却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说到这,钟年再次看向屋外,亭台楼阁被笼罩在茫茫细雨间,水雾中隔岸昏黄的烛火,四下晕染开来,偶尔被微风吹得摇摆不定。
店小二也不再说什么,闷头继续收拾起东西。
枚娘来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雨季,细雨朦胧的河对岸,一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姑娘,淡墨笔绘梅花点缀的油纸伞下,是她日渐模糊的莞尔一笑。
那时钟年还小,父亲正拉她走进茶楼店中,无意回头间,她看见了枚娘,只是一瞬的目光触碰,她却清晰地记得当时这番画面,恍如哪个文人才子精心布局的水墨画一般。
偶尔她也会去对面戏楼里听曲儿,枚娘见她来,都会送她一盒甜点。枚娘自以为小孩子都爱吃甜的东西,可钟年却不喜欢甜食,但她还是欣然接受了枚娘的好意。
枚娘还喜欢红色,她说红色喜庆,穿上红色的衣裙,整个人都被映衬得容光焕发了。
“钟掌柜……”钟年敲着桌上茶盏正是一阵出神,却听店小二小心翼翼地唤她道。
钟年听言抬头,示意店小二有什么事继续说。
“方才,来了两个客人……”店小二迟疑了一下,又道,“就是那个泼皮无赖黑梵,还带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人……”
钟年听言皱了皱眉头,这黑梵就是个财迷,老做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坑蒙拐骗偷,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人老是喜欢来找她麻烦。
钟年捋了捋袖子,朝着店小二指的方向走去。
“哟哟哟,掌柜的。”那黑梵一见她来,连声应道。
“有话快说,小心我把你再轰出去!”钟年瞧着他没好气地说道。
“钟掌柜别这么大火气,”说时,黑梵笑了笑,从袖中抽出一卷墨迹斑斑的字布,然后扬手展开,“怎么样?你若能提供给我她的去处,上面的赏金,咋们五五分成。”
钟年一睹那布示,俨然是司空凌的通缉令,她更加没好气地笑了一声,“得了吧,我钟年又不是什么神仙,我哪知道她在哪?”
“掌柜的耳听八方,掌管着示罗这么多年,能有查不到的人吗?”
这家伙倒是什么都知道啊。
示罗也号称“江湖小灵通”,掌管四方社会情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当然也给有需要的人卖情报,至于示罗的确为世人所知,而他们头上的老大,没几个是知道的,就像她这样,表面仅仅是一个茶馆老板娘。
“行啊,我看我手下这些示罗,倒还不如你的消息灵通啊。”钟年忍着一股想把这家伙轰出去的冲动,又是不爽又是讽刺地说道。
“别啊,钟掌柜……”
“没完没了啊你,你倒说说,你怎么把这家伙擒来?”钟年一手指着告示上的画像,有些不耐烦的打断他道。
黑梵笑了笑,一手拽过身旁那个目光呆滞的少年,“这不有个现成的人质嘛。”
这么一说,钟年才注意到黑梵身边还有另一个人,看着也就十五六岁的模样,五官端正清秀,不过有些消瘦,也不免平凡,让人印象不会很深也不会多去注意的一个人。
既然是人质,那定是与逃犯有关的什么人了。
少年就这般目光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
“你给他下蛊了?”钟年问道。
“是啊。”黑梵笑着答道。
“你怎么就认为这逃犯会为了他,”钟年说时指了指少年,“来换自己呢?除非,他对于逃犯来说很重要?”
“她会的。”黑梵肯定道。
“哦?”钟年瞧了黑梵一眼,一副愿闻其详的模样。
“这个逃犯非常自信,所以就算再进牢中一次,她也认为自己有能力再逃出来。即便他不那么重要,出于自大狂妄,逃犯还是会来的。况且……”黑梵一面说着,一面拍了拍少年的肩膀,续而说道,“这不是唯一的筹码,能解开他身上的蛊毒的人,也只有老夫我了。”
钟年眯了眯眼,嘴角含笑,看似是饶有兴趣,却又未言。
“至于她司空凌之后怎么逃出牢狱,那便是官府自己的事情了,老夫我就只负责抓人,拿到该有的赏金,岂不美哉。”
钟年听言笑着轻哼一声,说道:“北街流云客栈,暂歇此地的一位公子,叫苏牧,你跟着他,便能找到司空凌。”
黑梵一听有些疑惑,莫不是这苏牧是要跟自己抢生意的人。
“至于其他,那就是你的事情了。”钟年说着用手点了点桌子,完全无视他的疑惑,还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行了吧,小店也要打烊了。”
话说司空凌已经把滨州绕了几个圈,兜兜转转,还是找不到这路该怎么走。除了到处躲着官兵,有时候她也在想,或许阿爹能看见她的通缉令,会不会寻她而来呢。不过思来想去也有些后悔,若是她没有跟着那个陌生人出来,阿爹会不会已经回家了,此番她也不知道回去的路,他会不会来找她。
近日也真的是晦气得很,不过是迷路之间,循着一丝诡异的血腥味误入程家庄,到时已是人死魂去了,死状那可谓惨不忍睹。之后便是一波人冲进来不由分说地把不明状况的她给绑走了,直接给她定了个死罪。
要是她真的死了,不知道老天会不会给她来场六月飞雪。
现在的官家断案,都这么含糊不清的吗?
司空凌这番想着,这便见到前方树影下似有屋瓦,走近一些,方是一屋破庙,细雨划过庙外繁密的树叶,滴滴答答地敲打着山庙残破的青瓦,也不知是废弃了多少年的山庙,据阿爹的话来说,这些废弃的小庙,多半是用来供山神的,罔尘山的那个山寺里,应该也是一个小山神。只不过人们都喜欢拜些大神仙,久而久之,这些小庙里,香火便越来越不旺盛了。
不过,小庙的确是破旧了些,但还是个极佳的落脚之处。
司空凌找了个相对干燥的地方安顿下来,方觉得肚子好生饿,却又无奈屋外淅淅沥沥个不停的雨,山地里湿,也不好找什么吃的,便将就着屋内烛台的干木板枕着睡觉,以便忽略那饿得咕咕乱叫的肚子。
可又是辗转难眠,都不知是入夜几分了,雨还在下,寂静的夜色中显得夜雨的杂乱声很大,甚是让人有几分烦躁不安。
她尽量换了个让自己舒服些的姿势,在渐渐趋于朦胧的雨声中,恍然又回到了罔尘山下的那个山寺里,阿爹坐在院前,看着某个地方出神,而她就靠在神像下的烛台前睡觉,在梦里,她用阿爹给她做的桃木剑,斩杀了无数大妖怪。
有时候,她也会梦见广袤无垠的草原,大风拂过芒草沙啦啦的响着,远远可以听见马铃的声音,幽幽荡在低垂的蓝天白云下的旷野上,那般动听,骑马而来的是一个姑娘,她穿着圆领衫的骑服,脸上的笑容,同天空中洒下来的阳光一样明媚,她远远叫着自己凌儿,而每每这个时候,那个姑娘,就会蓦然变得模糊,整个画面如潮水般往后退去,只到最后,画面终于定格了,司空凌看见姑娘胸前蔓延在她骑服上的血色,还有她身后的天,慢慢晕染开的腥红,一把剑插入她的心腔,她颓然从马上跌落下来。
而那把剑,流光白影,被一人漠然收回剑鞘之中,只是一瞬刹那,刺眼的血色之下,那一袭同样令人觉得刺目的白衣,和那把白芒之剑,来人在昏然的光色下看不清的脸,却在她的梦中轮番出现。
大风吹着,仍然是芒草沙啦啦地响着,其间传来远远的马铃幽幽的声音,荡漾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阿爹摸着她的头,沉默了好久,才说,“凌儿,我们回家吧,回家吧。”
日光西下,阿爹背着她,她爬着阿爹的肩头,浅浅的睡着。
阿爹近来几日都不说话,也不理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把砚台里的墨打泼了,他就生气了,所以一直都不搭理她。又兴许是罔尘山的雨季快到了,他忙着去捣鼓屋顶,没有时间听她叽叽咕咕的。终归还是回到阿爹的身边好,回到罔尘好,回到家好……没有凡世的纷纷攘攘,没有走到哪都觉得一样的街道,没有到处搜捕她的官兵。
她坐在院中,偷偷喝着阿爹泡好的茶,阳光穿过树叶间隙,打到地上的斑斑点点。还有院外依然顽强挂在枝头上零星的桃红,终于抵不过风吹雨打,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