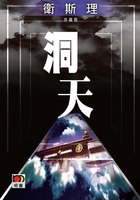他们下山来到山洞口,一道光线从挂在洞口的毯子边缘透出来。那两只背包在树脚边,上面盖着帆布,罗伯特·乔丹跪下,摸到盖在背包上的帆布又潮又硬。黑暗中,他在帆布下一只背包的外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只有皮套的扁酒瓶,把它插在他的衣袋里。背包由串在背包口上的金属扣眼里的长柄挂锁锁住,他打开锁,解开系在每只背包口上的拉绳,把两手伸进去摸索,核实一下里面的东西。他在一只背包的深处摸到那一包包捆好的炸药,那是裹在睡袋里的,然后他系上这背包上的绳子,推上了锁,两手伸进另一只背包,摸到那只轮廓分明的放旧引爆器的木盒,装雷管的雪茄烟盒,每个圆柱形小雷管外面都由它的两根铜线团团绕住(这一切都精心包装好,就像他小时候包装收集到的野鸟蛋那样)。他还摸到从手提机枪枪身上卸下的包在他皮茄克里的枪托、装在大背包一只内口袋里的两盘子弹和五个子弹夹,以及另一只内口袋里的几小卷铜丝和一大卷绝缘细电线。他在藏电线的内口袋里摸到了老虎钳和两把在炸药包一端钻洞用的木头锥子,接着从最后一只内口袋里掏出一大盒他从戈尔兹的司令部弄来的俄国烟卷,扎紧背包口,插上挂锁,扣上背包盖,再用帆布盖上这两只背包。安塞尔莫这时已上前进入山洞。
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想跟他进去,接着再一想,就揭去那两只背包上的帆布,一手提一只,勉强地提着向洞口走去。他放下一只背包,撩开毯子,然后低下头,抓住皮背带,两手各提一只,走进山洞。
山洞里暖洋洋,烟雾缭绕。沿洞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支插在瓶子里的牛脂烛,桌边坐着巴勃罗、三个他不认识的人和那吉卜赛人拉斐尔。烛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背后的洞壁上,安塞尔莫还站在桌子右边他刚才进来时的地方。巴勃罗的老婆正弯身站在山洞一角生炭火的炉灶边。那姑娘跪在她身旁,在一只铁锅里搅拌。她从锅里提起木汤匙,望着罗伯特·乔丹站在洞口,他借炉火的光亮看到那妇人在拉风箱,看到姑娘的脸和她的一条手臂,还看到汤汁正从汤匙中滴下来,在滴入铁锅。
“你提着什么?”巴勃罗问。
“我的东西,”罗伯特·乔丹说着,在桌子对面山洞比较开阔的地方放下背包,两只背包隔开一小段距离。
“放在外面不好吗?”巴勃罗问。
“黑暗里人可能被它们绊倒,”罗伯特·乔丹说着,走到桌边,把那盒烟卷放在桌上。
“我不喜欢把炸药放在这儿山洞里,”巴勃罗说。
“离炉火远着呢,”罗伯特·乔丹说。“来几支烟吧。”他用拇指指甲划开盒盖上印有一艘彩色大兵舰图形的纸盒一边的封口,把纸盒推向巴勃罗。
安塞尔莫给他端来一只蒙着生皮的凳子,他就在桌边坐下。巴勃罗望着他,好像又有话要说,结果却伸手去拿烟卷。
罗伯特·乔丹把烟卷推向其他人。此刻他并不望着他们。但他觉察到一人拿了烟卷,两人没有拿。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勃罗身上。
“情况怎么样,吉卜赛人?”他对拉斐尔说。
“好,”吉卜赛人说。罗伯特·乔丹看得出,他进来时他们已在谈论他。连吉卜赛人也局促不安。
“她会让你再吃一回吗?”罗伯特·乔丹问吉卜赛人。
“会的。干吗不?”吉卜赛人说。这时的情况和他们下午友好地一起又说又笑大不相同了。
巴勃罗的老婆没说什么,只顾把炭火扇旺。
“有个叫奥古斯丁的说,他在山上被厌倦感搞得要死了,”罗伯特·乔丹说。
“死不了的,”巴勃罗说。“让他死一会儿好了。”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双手搁在桌上,倾身向前,向桌边的人笼统地问。
“剩下不多了,”巴勃罗阴郁地说。罗伯特·乔丹决定不如观察一下另外三人的神情,设法判断自己的处境。
“既然这样,让我喝杯水吧。你,”他对姑娘大声说。“给我来杯水。”
姑娘望望那妇人,妇人没说什么,只当没听到。她随即向盛有水的锅子走去,满满舀了一杯。她把水端到桌前,放在他面前。罗伯特·乔丹朝她笑笑。同时,他收缩腹肌,在凳子上微微向左转,这一来,腰带上的手枪滑到更顺手的地方。他一手向下伸向后裤袋,巴勃罗注视着他。他知道大家也都在注视着他,但他只注视着巴勃罗。他从后裤袋里一手抽出那只有皮套的扁酒瓶,旋开瓶盖,然后举起杯子,喝掉了半杯水,再把瓶里的酒十分缓慢地倒进杯子。
“这东西劲头太大,你受不了,不然我给你一些,”他对姑娘说,又对她笑笑。“剩下不多了,不然我请你喝一些,”他对巴勃罗说。
“我不喜欢大茴香酒,”巴勃罗说。
一股呛人的气味飘过桌面,他闻到这里头有一种气味是他熟悉的。
“好,”罗伯特·乔丹说,“因为只剩很少一点儿了。”
“那是什么酒?”吉卜赛人问。
“药酒,”罗伯特·乔丹说。“想尝尝吗?”
“喝了管什么用?”
“什么都管用,”罗伯特·乔丹说。“什么病都管治。你如果有什么病,它准能治。”
“让我尝尝,”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把杯子向他推去。这时酒掺了水成为乳黄色,他希望吉卜赛人至多喝一口。剩下只有很少一点儿了,而这样一杯东西,可以代替晚报,代替往日在咖啡馆里的所有夜晚,代替每年会在这一月开花的所有栗树,代替郊外林阴路上的策马缓行,代替书店,代替报亭,代替美术陈列馆,代替蒙特苏里公园,代替布法罗运动场,代替夏蒙高地,代替保险信托公司和巴黎旧城岛,代替古老的福约特旅馆,还可以代替傍晚读书休憩;代替他享受过而已遗忘的一切[1]。当他品尝这乳浊、苦涩、使舌头麻木、使头脑发热、使肚子暖和、使思想起变化的神奇液体时,所有这一切都重现在他眼前了。
吉卜赛人做出一副苦相,交还杯子。“这东西有大茴香味,但像苦胆一样苦,”他说。“宁可害病也不愿喝这种药酒。”
“那是苦艾,”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这种酒,在这种真正的艾酒里,掺有苦艾。据说能把你的脑子烂掉,但我不相信。它只会使思想起变化。你该很慢地把水掺在里面,每次滴几滴。但我把它倒在水里。”
“你在说什么?”巴勃罗觉得受到了嘲弄,气愤地说。
“说明这药酒呗,”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并露齿笑笑。“我是在马德里买的。这是最后一瓶,已经喝了有三个星期了。”他喝了一大口,觉得它顺着舌头泻下,使舌头微感麻木。他望着巴勃罗,又露齿笑笑。
“情况怎么样?”他问。
巴勃罗不回答,罗伯特·乔丹仔细打量着桌边的另外三人。一个长着一张大扁脸,像只塞拉诺火腿似的扁平而带褐色,加上曾被打扁而鼻梁破裂的鼻子和嘴角斜叼着细长的俄国烟卷,使那张脸显得越发扁平了。这人留着灰色短发和一片灰色胡子茬,身穿寻常的黑色罩衣,齐脖子扣住纽扣。罗伯特·乔丹望着他的时候,他低头望着桌子,可是目光镇定,两眼一眨不眨。另外两个显然是兄弟。他们长得很像,身子都矮胖结实,黑头发直长到前额中部,加上黑眼睛和棕褐色皮肤。一个前额上有条刀疤,在左眼上方,他望着他们的时候,他们镇定地也望着他。一个看来有二十六或二十八岁光景,另一个可能大两岁。
“你在看什么?”兄弟中那个有刀疤的问。
“你,”罗伯特·乔丹说。
“见到有什么稀奇的地方?”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来支烟?”
“干吗不?”这位兄弟说。他刚才一支也没有拿。“这烟跟那一个的一样。炸火车的那个。”
“炸火车你在?”
“炸火车我们都在,”那人冷静地说。“只有老头子不在。”
“这才是我们现在该干的,”巴勃罗说。“再炸一列火车。”
“我们可以干这个,”罗伯特·乔丹说。“等炸桥以后。”
他能看到巴勃罗的老婆这时在炉边转过身来,正在听。他一提到桥这个字,大家都不作声了。
“等炸桥以后,”他故意重说一遍,咂了口艾酒。我还是挑明的好,他想。这问题反正要谈到。
“我不赞成炸桥,”巴勃罗说,低头望着桌子。“我也好,我手下也好,都不赞成。”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他望着安塞尔莫,举起杯子。“那我们就单干,老伙计,”他说着笑了笑。
“不要这个胆小鬼,”安塞尔莫说。
“你说什么?”巴勃罗对老头儿说。
“不是说给你听的。我没跟你说话,”安塞尔莫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这时隔着桌子望望站在炉火边的巴勃罗的老婆。她还没开过口,也没露过声色。但她这时对姑娘说了些他没法听到的话,姑娘就从炉边站起,沿着洞壁悄悄走去,揭开挂在洞口的毯子,走出去了。我看现在要摊牌了,罗伯特·乔丹想。我相信是这样。我不希望情况变成这样,但实际上看来就会这样。
“那我们来炸桥,不用你帮助,”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说。
“不行,”巴勃罗说,但罗伯特·乔丹注意到他脸上在出汗。“你不能在这儿炸桥。”
“是吗?”
“你不能炸桥,”巴勃罗费劲地说。
“那你说呢?”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的老婆说,她正站在炉边,一动不动,显得身形庞大。她转身对着他们,说,“我赞成炸桥。”她的脸被炉火照亮着,脸色绯红,这时在炉火的光照下,显得热情、黝黑而漂亮,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你认为怎么样?”巴勃罗对她说,转过头来时,罗伯特·乔丹看到他脸上被人出卖的神色和前额上的汗。
“我赞成炸桥,不赞成你,”巴勃罗的老婆说。“没别的啦。”
“我也赞成炸桥,”扁脸、断鼻梁的那个说,在桌上揿灭了烟蒂。
“我看那桥算不上什么,”两兄弟中的一个说。“我拥护巴勃罗太太。”
“我也是,”另一个兄弟说。
“我也是,”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巴勃罗,同时把垂在身边的右手越来越往下伸,以便万一需要时有所准备,几乎希望事态会这样发展(觉得那也许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解决办法,然而又不愿意损害已有的良好进展,因为他知道,一家人、一族人、一帮人在争吵中会很快地一致团结起来反对外来人,然而他又想,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用这只手所能干的事也许最简单、最好,并且像外科手术那样,最干脆),他还看到巴勃罗的老婆站在那里,并注意到她在众人表示效忠时脸上露出了自豪、坚强而健康的红晕。
“我拥护共和国,”巴勃罗的老婆乐呵呵地说。“这桥就等于共和国。我们以后有时间另作计划。”
“你啊,”巴勃罗怨恨地说。“你这个种牛脑袋、婊子心肠的东西。你以为炸了这桥还会有‘以后’?你考虑到会发生的事吗?”
“准会发生的事,”巴勃罗的老婆说。“准会发生的事总会发生。”
“这事情我们捞不到好处,事后还会像野兽一样被人搜捕,你觉得无所谓?干的时候死掉也无所谓?”
“无所谓,”巴勃罗的老婆说。“别来吓唬我,胆小鬼。”
“胆小鬼,”巴勃罗怨恨地说。“你把人家当作胆小鬼,因为人家有战术观念。因为人家能事先看到干蠢事的后果。知道什么叫蠢不是胆小。”
“知道什么叫胆小也不是蠢,”安塞尔莫忍不住讲了这一句警句。
“你要找死?”巴勃罗对他厉声说。罗伯特·乔丹觉得这话问得多么不讲究辞令。
“不。”
“那就留神你的嘴巴。你对自己不懂的事话太多。难道你没看出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他简直叫人可怜地说。“只我一人看出这件事有多严重?”
我认为是这样,罗伯特·乔丹想。老巴勃罗,老伙计啊,我认为是这样。还有我。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出来了,那妇人从我手上也看出了,但她还没有明白过来。目前她还没有明白过来。
“我当头儿难道是吃干饭的?”巴勃罗问。“我说话心中有数。你们这帮人哪里知道。这老头儿在胡扯。他这老头儿只会给外国佬当通讯员、做向导。这外国佬到这儿来干的事对外国佬们有好处。为了他的好处,我们得送命。我关心大家的好处和安全。”
“安全,”巴勃罗的老婆说。“没有安全这档子事。如今到这儿来求安全的人太多,弄得引起了大危险。如今为了求安全,你把什么都丢了。”
她这时站在桌边,一手拿着一把大汤匙。
“有安全,”巴勃罗说。“在危险中知道怎么见机行事,就有安全。像斗牛士一样,知道自己在干着什么,不冒险,就安全。”
“在他被牛角挑伤以前吧,”妇人怨恨地说。“我听到过多少次啦,斗牛士被牛挑伤前也是这个调门。多少次我听菲尼托说,这全靠学问,牛决不会挑伤人,倒是人自己撞到牛角上去的。他们挨牛角前总是这样说大话。结果是我们到病房去看他们。”这时,她学着在病床边探病的样子,“‘喂,老手,喂,’”她声音洪亮地说。接着,她模仿受了重伤的斗牛士的衰弱的声音说,“‘你好,朋友。怎么啦,比拉尔?’”“‘怎么搞的,菲尼托,好孩子,你怎么碰上了这倒霉事儿?’”她用她那洪亮的声音说。接着声音衰弱而尖细地说,“‘没什么,太太。比拉尔,没什么。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我好好儿宰了它,你知道。谁也不会干得更好。那时候,完全照着我的意思把它干了,它也死定了,腿儿摇摇晃晃的,支不住自己的身子,眼看就要栽倒,我从它身边走开,模样挺神气,挺帅,但它把这牛角从我背后捅进我屁股爿中间,从我肝脏中戳了出来。’”她不再学斗牛士那简直像女人的声音,大笑起来,又声音洪亮地说话了。“你和你的安全!我和天下收入最少的三名斗牛士混了九年,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什么叫安全吗?跟我说什么都行,可别说安全。你啊。我当初把指望全放在你身上,现在可落得怎样的下场!打了一年仗,你就变懒了,成了酒鬼、胆小鬼。”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话,”巴勃罗说。“尤其是当着大家的面,当着陌生人的面。”
“我就是要这样说话,”巴勃罗的老婆接着说下去。“你听到没有?你还以为这儿是你作主?”
“是啊,”巴勃罗说。“这儿我作主。”
“开什么玩笑,”妇人说。“这儿我作主!你们大伙儿听到了没有?这儿除了我没别人作主。你要愿意就待着,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可不准拼命死喝。你要愿意,有你一份干的。可这儿我作主。”
“我要把你和这外国佬一起毙了,”巴勃罗阴沉沉地说。
“试试看,”妇人说。“看看会怎么样。”
“给我来杯水,”罗伯特·乔丹说,眼睛仍然盯着这个脸色阴沉而脑袋笨重的汉子和那个自豪而自信地站着的妇人,她握着那把大汤匙,威风凛凛地仿佛它是根指挥棒。
“玛丽亚,”巴勃罗的老婆叫着,等姑娘进了洞口就说,“给这位同志端水。”
罗伯特·乔丹伸手去掏他那扁酒瓶,在他掏出来时,一边掏,一边松开枪套里的手枪,把它在腰带上挪到大腿根。他在杯里又斟上了艾酒,拿起姑娘给他端来的那杯水,开始把水滴入杯子,每次滴几滴。姑娘挨在他身边站着,注视着他。
“外面去,”巴勃罗的老婆对她说,用汤匙做了个手势。
“外面冷,”姑娘说,脸颊紧挨着罗伯特·乔丹的脸颊,注视着杯里正在发生的情形,那烈酒正在里面变得混浊。
“也许吧,”巴勃罗的老婆说。“但里面太热。”她接着亲切地说,“要不了多久的。”
姑娘摇摇头,就走出去。
我看他就要按捺不住了,罗伯特·乔丹管自想。他一手握着杯子,一手这时正毫不掩饰地搁在手枪上。他已经打开保险栓,摸摸上面的小方格几乎已磨得滑溜溜的枪柄,摸摸发凉的圆形扳机护圈,像遇到了老朋友似的。巴勃罗不再望着他,只望着那妇人。她接着说,“听我说,酒鬼。你明白这儿是谁作主吗?”
“我作主。”
“不。听着。把你那毛茸茸的耳朵里的耳屎掏掉。好好听着。我作主。”
巴勃罗望着她,从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他意味深长地望着她,然后望着桌子对面的罗伯特·乔丹。他深思地望了他很久,接着又回头望着那妇人。
“行。你作主,”他说。“你要他作主也行呀。你们两个可以见鬼去了。”他正眼望着那妇人的脸,既没有被她镇住,似乎也没受她多大的影响。“可能我是懒了,而且喝得太多。你可以把我当胆小鬼,但这一点你错了。我可不傻。”他顿住了一会儿。“你可以作主,还喜欢作主。那好,你既是作主的,又是女人家,就该给我们搞些吃的了。”
“玛丽亚,”巴勃罗的老婆喊着。姑娘从挂在洞口的毯子边探进头来。“快进来侍候吃晚饭。”
姑娘进了洞,走到对面炉边的矮桌前,捡起几只搪瓷大碗,端到饭桌上。
“有葡萄酒,够大家喝的,”巴勃罗的老婆对罗伯特·乔丹说。“别理会那酒鬼说的。喝完了这些酒,可以再拿些来。喝了你在喝的那怪东西吧,来杯葡萄酒。”
罗伯特·乔丹一口干了最后一点艾酒,这样猛喝一大口,觉得身子里产生一股暖和、滋润、冒出浓烈气味而产生化学反应的细细热流。他递过杯子去要葡萄酒。姑娘给他舀得满满的,笑了笑。
“呃,你看过桥了?”吉卜赛人问。其他人,刚才改变效忠对象后还没有开过口的,现在都凑向前来听。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这件事不难干。要我讲给你们听听?”
“好,伙计。挺感兴趣。”
罗伯特·乔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给他们看草图。
“瞧这桥画得多像,”那个扁脸汉子,名叫普里米蒂伏的,说。“像真的一样。”
罗伯特·乔丹用铅笔尖指着,讲解桥该怎样炸,要那样安放炸药包的理由。
“多简单啊,”两兄弟中脸上有刀疤的那个说,他名叫安德烈斯。“但是你怎样引爆炸药包呢?”
罗伯特·乔丹又作了解释,他给他们讲解着,发觉姑娘在一边望着,手臂搁在他肩上了。巴勃罗的老婆也注视着。只有巴勃罗不感兴趣,独自坐着,喝着从大缸里重新舀满的那杯酒,这大缸里的酒是玛丽亚从挂在山洞进口左侧的皮酒袋里倒出来的。
“这种事你干过很多?”姑娘悄声问罗伯特·乔丹。
“对。”
“我们可以看炸桥吗?”
“可以。干吗不?”
“你准会看到,”巴勃罗在桌子那头说。“我相信你准会看到。”
“闭嘴,”巴勃罗的老婆对他说,突然想起了下午在手掌上看到的预兆,猛的冒出一股无名怒火。“闭嘴,胆小鬼。闭嘴,不祥鸟。闭嘴,杀人凶手。”
“好吧,”巴勃罗说。“我闭嘴。现在作主的是你,美景一幕幕,你瞧下去得了。但是别忘了,我可不傻。”
巴勃罗的老婆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变成了忧伤,变成了所有的希望和前途都受到了挫折的感觉。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感觉,她一生中一直知道是什么事使她产生这种感觉的。现在这种感觉突然产生了,她把它置之脑后,免得影响自己,免得既影响自己,也影响共和国,于是她说,“我们现在来吃吧。把锅里的菜盛在碗里,玛丽亚。”
注释:
[1]从上文“代替晚报……”起,是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在回忆前几年在巴黎时爱做的事和爱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