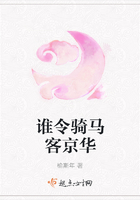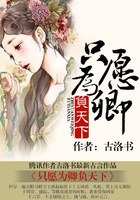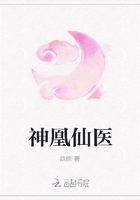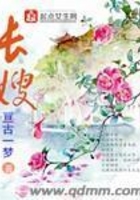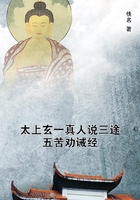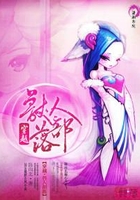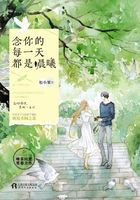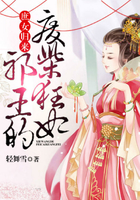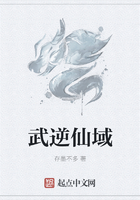题记:《皇朝历记》载:太和十六年,越君大婚,迎召国公主为后,邀皇朝储君观礼。一时四境封国之王亲贵胄、名门世家,皆往东行,以赴盛世锦绣之宴。
*******
琅国位于淇水之源,淇水东流,过天子疆域,环东越国都,终入汪洋。
琅国公子夜兰,为避国中争储之乱,欲往东越寻求庇护,便是乘了一叶扁舟依淇水下行,荡漾东去,自以为一路悠然惬意、用不得一月光景便可抵达东境。
偏人生境遇并非总是春光明媚,更多是乍暖还寒。
一路的追兵伏杀,几乎已杀尽他身边所有侍卫仆从。
此间泛舟江上,虽有江心波光滟滟,两岸桃花灼灼,又恰逢春风乍暖,拂动粉叶翩然,若云霞蒸腾,缠绵于新翠浅碧之间,只是这一派东境春盛、繁华之景,对于立在舟头的夜兰而言,却是龙潭深渊,地府之门!
自此处入东越国尚有水程百里,而这百里之内,谁人又知埋伏了多少凶险。
肃立在他身后的几名甲衣侍卫,或是持戟,或是提剑,护持于船舷两侧。那玄色甲衣印着斑斑血迹,铮铮剑锋犹有亡魂在泣,将士们个个面色凝重,戒备非常。他们都是夜兰离宫时其母妃赠予他的铠甲护卫,原本有五百之众,而今却只剩寥寥数人,且大都是伤兵残将,若再遇伏杀只怕根本无力抵挡。
就如同夜兰公子这孤弱身姿,实难抵挡江风料峭。他撑立船头,极力翘首远望,惟见一江春色寂寥,不见半片人影往来。也不知越国长公主可有接到自己的求救信函,是否会派人到边城来迎?若有迎宾之仪,则凶险可避;若无人来迎……夜兰满心凄惶,摇头叹息——此去或将葬身淇水!
自古储君之争,非胜即死。史书读了那许多,自以为早已见惯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事,可临到己身,依旧痛心疾首!如何自己毕恭毕敬、谦逊礼让,声声王兄、念念相亲却仍逃不过今日劫数。
我纵无意相争,奈何世人猜忌!——公子夜兰长声谓叹。只是不知此回设伏杀之局是长兄太子还是二哥夜玄?
父王年迈多疾,已难顾及国政之患、边关之乱,又哪有心力再顾他死活。此番依母妃所言,借越王大婚之盛事,避难于东越,不知是否良策?
想来与越国长公主也不过一面之缘,而别过三载,她可记得自己?纵然万幸记得,凭她长公主之尊,东越新君之妹,皇朝东宫之友,又如何会顾念西琅小国一个不入流的庶出公子?更别说要她以冒犯西琅太子之嫌对自己施己以援手了!
而东越中兴,俨然已是四境最盛之国,这两年间天下世家名流莫不攀附。那位长公主更是权掌三军,辅政朝堂,想来平日里必是贵客盈门,华盖满庭。此季又值越王婚典之期,一城防务皆赖她担当,各国贵族尽由她应酬,碌碌无暇,又如何会念及一个小小的夜兰?
夜兰越想越心灰意冷,越想越焦灼无望,凄然长叹,触目所及尽是落花葬泥沼。艳阳正高,却凭白欺得一身寒意。
身后侍卫不忍见他忧心惶惶,好心劝慰,“公子不是已经递信给东越长公主了吗?长公主必会派人来迎。公子安心便是。”侍卫们也都自知,仅凭余下的寥寥数人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再一回伏杀。
夜兰依旧愁眉百结,“也不知那书函是否呈到长公主案前?即便呈至她案前,她若未见也是枉然;纵然见了,她若不应亦是无用;纵然应了,若救兵迟来亦是死局!错一分,误一刻,于吾等而言皆是呜呼哀哉!入东越之前当先过鬼门关啊!”
侍卫们又都言说越国长公主素有侠义之名、多有仗义之举,却也都被夜兰摇头否决,“她纵是厚义仁德,可如今适逢越王大婚,越都宾客云集,她执掌一城安防,又怎有闲暇顾及我等。”
侍卫们便不再应言,深知自家公子素来心思忧患,从来都是山穷水尽,看不见柳暗花明。
撑舟去,宛如一支孤木寂寂于春水之上,随波东去,艳阳随行,两岸杀机暗伏,随处都可能是葬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