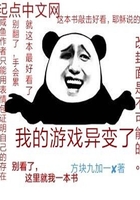淇水上游河畔,芳草萋萋间,有一布衣书生,正盘膝就席,执竿于岸上,垂钓于江心。可知这样时节正是春江水暖垂钓鲜美之时。
不远岸处,一叶扁舟驻泊柳下,一位书童懒坐舟头,抱膝垂首大有春困之容。
风过江心,江波漾起一片鳞光。书生凝目而思,所感虽是江风徐徐,所思却非江下河豚,及至身旁几时多坐了一人也未觉察。直待蓦然回首,惊见一白衣少女,正端然危坐于身侧,举目江心。
书生大为讶异,见这女子亦是凝神若思,秋水无波,倒似生就坐在那里一般。一时唯恐多言扰她清静,忙收目敛意,时而远望春水粼粼,时而又忍不得顾看身畔风流。
几许侧目间,窥得那女子目若秋水清明,眉似新月初画,一点樱唇吟浅笑一盏,一抹乌发似悬瀑垂肩。
书生惊赞之余,也不敢造次多看,忙又收回目光望向遥遥碧波,只不多时,又实忍不得回头再窥。方才那一瞥惊艳,如春燕凌波,搅起他心湖片片涟漪。
再去看那女子,竟生得如此灼采华然,眉间别有英气,眸色蔚然清朗,音容安若似这和煦春风,顾盼神飞又如春波潋滟。观她衣饰,不过一袭白衣素净,寻常的春绸素锦,即非村女郊婢之薄装,又非富家贵族之重仪,而其危坐端然自是别有雍容闲适。
此等人物如何会流落荒郊野外?书生心底轻笑——莫不是花神仙子?这等奇事竟被我程潜之遇上!
他不由悄悄转目四周,见得春风烂漫里,几只莺啼鹭鸣,几片蝶飞蜂动,除却舟头困睡的书童再无一个人影。这白衣女子莫非集香草而生,御清风而来?几曾行遍了天下,今日倒遇上了奇事!
书生程潜之着实为之感叹一番。少女许是闻他骚动又兼流目切切,忽地凝眸顾看,悄问一声,“可有斩获?”
其声泠泠,有清泉之妙,倒使程潜之羞开拙口,惟有回手一指身后竹篓。少女张目望去,见有数条肥美锦鳞,不由激赞一声,“好极!”
程潜之当她是赞自己垂钓之技,憨然一笑,正于腹中筹措谦让之辞,不想女子又问,“可有鼎?”
程潜之诧异,怔怔点头,才晓她方才激赞竟是为要沸鼎煮鱼。
“淇水金鲈鲜美,可令小童拾薪燃鼎,你我煮鱼颂春可好?”女子言辞洒落,丝毫无闺阁秀女的矜羞之态。若说是江湖儿女,她端然危坐自有威仪;若说是世家之女,又慨然洒落毫不拘礼。
程潜之一时琢磨不透,惟怔怔陪笑,恍恍答曰,“但凭姑娘所好!”
随即呼船头困坐的小童,令其铺席于浅草处,置鼎注水,又令其往林间捡拾枯木,燃水待沸。
“君钓淇水鱼,我尝鼎中鲜。先生不怪我冒昧争食?”少女围鼎而坐,朗笑问到。
程潜之笑笑,“玉树琼花,风明月朗,岂非尽归天子。你我天子之民,当共享之。”
少女笑意愈朗,随口应来,“滩台慕熔,程门伏白,此四时风境,皆天恩矣。惟鼎中鱼,当谢先生之恩。”
程潜之不觉一惊,瞠目看住面前女子,料定其来路不凡。
他方才所言本为卖弄,一言“玉树琼花”代指天子之家玉室,再言“风明月朗”是指皇朝四方守境之国,即南召(风)氏、北溟(明)昔族,东越(月)蔚族,与西琅(朗)夜氏,此乃四境封疆王族,他以八字之言说尽天下帝王,不想竟被她听破。
而女子回说的“滩台慕熔,程门伏白”,正是代指当今四大家族。澹台(滩台)以富甲天下,慕容(慕熔)以医行天下,琢湖程门以智师天下,伏白一族以累世之贵誉天下。如此四家,确实如这四时风景,皆天恩演化矣!
程潜之望着面前女子一时怔怔不知所措,世上可有这等灵通的花神仙子,还能议凡间政务,数人世繁华?终忍不得直言相询,“请教姑娘尊姓芳名?”
女子笑笑,眉眼明悦,一时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