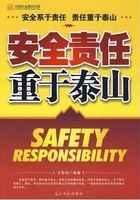程潜之蹙眉,全然猜不透她意欲何为,只是话已至此,已然不吐不快,索性坦言,“《政考》有载:‘储君之立,以嫡子先,举贤推其长矣’。公子玄非贤非长,更非嫡出,只不过这些年戍守边关,略有战功罢了!最多以上将军封之,辅君之良臣尔,何敢妄议储君?”
青琉频频点头,颇有“甚合我意”之态,“那二者相较呢?若必择其一,先生以为谁更胜任。”
程潜之颔首默笑,想她还真是穷追不舍,这回倒也爽利答她,“非二者之一,则玄胜,兰弱。”
青琉此回倒也不服,质问,“《政考》亦载,‘仁治天下,惠民矣’。先生何以推武抑文?”
“可知文非仁也!武亦非不仁。仁者兼爱,兼爱者文可熏之,武可护之,何来以文武论仁德?”
女子娥眉微蹙,既有质疑之意,又有愤慨之态,小声嘀咕一句,“若是以武诛手足呢?”
程潜之听不甚清,只疑惑望之,“在下可有言辞不妥处?”
“先生有治世辅政之才,竟为鲜鲈所误!”
一言说得程潜之开怀大笑,“蒙姑娘谬赞!实不敢当。”又试探着问,“姑娘所约之人莫非是公子夜兰?”他明知此问太过冒昧,偏又心下好奇这样女子肯为何人犯罪涉险。
“鱼儿!鱼儿!快起杆!”女子忽然跃身到程潜之身前,一把抓住竹竿,用力收线。
程潜之也连忙起身,一同使力,不消片时就扯起一条锦鱼飞跃上岸。
少女欢笑不止,眉眼璨比桃花,跃身抓住锦鳞,“先生果然有垂钓江山之才!还不拿酒来!”
程潜之见她慨然洒落,心下且赞且叹,倒也忘了方才疑问,于是唤童子,令其接去锦鳞,并竹篓中所有一起拿去河边洗了。自己则折身往船上去,不时抱回一坛陈酿,归席入坐,“琢湖青芝,可适姑娘品味?”
有意亦或无意,他竟露了身世。琢湖青芝乃程门特有,故可称是酒中名流,天下雅客谁不想品上一盏!然独独于她,也不过赞了声——“好极!”便自去摆盏捧坛,先倾一满盏,举手饮尽,又赞一声,“天下佳酿唯青芝矣!”
程潜之看得惊讶不已,也算游历非浅,却从未见过女子这般豪饮!想是她将门出身,故存磊落之风罢。又想青门另一遗孤,据闻被越国长公主养在深宫,却不知又是怎样风范?
女子三杯酒喝尽,书童才洗净了鱼肠回来,一时添入鼎中,三人围席,坐等鼎沸。
女子又说笑道,“我见先生轻舟瘦童,布衣木盏,莫不是只以垂钓锦鳞为生,清贫至此?“
程潜之闻言大笑,几日来风餐露宿之苦顷刻散尽。“在下不才,可也略通书典,设了几家学堂,教人识字知礼,倒也有些肉米入囊。”
“这样便好!这样便好……”女子应着,倒似真的忧他衣食而闻过此言又宽心许多,“先生大才!若然辅政君王则国之礼乐无忧矣!”
此是她第三回赞他治世之才。程潜之暗忖:莫非她有意为越王招揽人才?可是世人皆知:程门原本就是皇朝辅政首臣,天家御用之师,只为当年直谏得罪天子,被逐出帝都,如今才不得不退居郊野,结庐授业。而程老宗主于子孙亦有训诫:吾当世之年,程子不得入仕参政!故而四境王室也无人敢逆老宗主之意,强求程门子弟入朝为官。
“少主?少主!姑娘问话呢……”童子轻推,唤醒了程潜之的神游向外,忙向青琉赔礼,“姑娘见谅,潜之一时神游,委实失礼……”
有意亦或无意,再次透了身世。凭他诗礼世家,与她将门候府,可谓相当乎?天下名流谁不知“琢湖醅青芝,程门师天下”。她既然出言即论四大世族,当知“潜之”二字非俗流也!
可那女子似乎当真无意于此,只凑向鼎炉,嗅那鲜香,蹙眉说道,“鱼汤虽鲜,却仍有几分腥未去,不若往水边割些荠菜香草调味如何?”
程潜之哭笑不得,想堂堂程门少主之名竟不及一碗鱼羹诱人,闻言即呼小童,却被青琉拦住,“倒也不烦你这瘦弱童子,不若我唤人来,与我们割一撮荠采菜可好?”
程潜之诧异,唤何人来割采荠菜?莫非是与她相约之人?不是夜兰?又是谁人?
一时见女子自身后取出一支蓝玉洞箫,起身往河岸边去了——“此处春水汤汤,又有江风徐徐,与先生吟一曲《御风行》如何?”
程潜之怔怔,不知这女子还藏有多少惊人事!
《御风行》乃是旧年间皇朝太子凌霄君赠予东越长公主的践行曲,后被东宫乐师红葉姑娘带出宫廷,流传世间,但闻知者众,会吟着寡,眼前这青门女子向谁人习得这首萧曲?难道是她家主人——东越蔚璃?
青青浅草间,茵茵绿水旁,女子白衣胜雪临风而动,一曲箫音经风而起,泠泠若天籁之音。
程潜之低头喟叹:可怜‘潜之’之名,天下谁人不识,偏如汝卿卿,相逢亦是陌路,不醉盛名醉青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