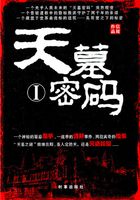『织梦花飞散的那晚,神将噩梦赐给整个大漠』
汝南不只是座小城,也是她的名字。那年清明烟雨霏霏,雨雾朦胧江面,窸窣打扰了平静的水流,落了一片乱麻。娘子的油纸伞擦过发出新芽的柳条,牵下零零落落的水滴;衣裙擦过圆石,那清雅的甜香就被留在空气里。
汝南汝南,欣羡江南。她阿娘是姑苏人,说起话来柔柔糯糯,软成棉花。本是书香门第的女儿,来时也是兰心蕙质。
阿娘怀上汝南那年,已经数年不曾回过姑苏,听说是随情郎私奔出来又遭了遗弃、无处可去才同意嫁与如今的郎君。其中多少真情,只有这一双人自己知道,她总是对着烟雨出神,到死还念着「回家」两字。
汝南阿娘终究是没能回去,身躯烧成了灰、收在坛里,漂浮如萍的一生终于称埃落定。
「员外,小姐来请您用膳」
汝南便跟在阿嬷身后,许多次瞧见她爹对着瓷坛出神。
她知晓里边安放了个什么人,从前问过:阿娘想回姑苏,为何爹爹不带她回去呢?
汝员外苍老了很多,两汪眼都陷进框里,多有几分沧桑落寞。「你娘不愿回去」他的眼中泛起浅淡的血丝,说起亡妻的时候,总是这份神情。
又过了几年,汝南落落大方,担得起‘姑娘’两字。她决议要去江南看看,也偷偷带上了她的阿娘。
汝南真正踏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姑苏下了此年第一场雨。蒙蒙雨丝将山河**织成锦绣,在姑娘的发间绕成一串沧珠。她匆忙卷过披风盖在瓷坛上,在青石巷里寻一处避雨的地方。
这遮雨地儿不过一道窄窄的屋檐,汝南贴着白墙站直,才叫雨丝错过了裙摆。她的后脑便也靠在窗边,眼眸映进青灰的天空。初春难免清冷,汝南被凉风吹得一颤,忍不住想拢好她的披风。
她垂眼瞧瞧怀里的物什,一时觉得忙不过来。适时一柄小伞侧过她的头顶,身前笼来道高挑阴影。汝南愣着眨眨眼,些许浅金卷发飘进她的视野。
她抬眼看去,却是一陌生的西域人,眉眼深邃、棱角分明、面容俊秀。这是汝南与那苏第一回见面。
那苏带着和善的笑容,一腔中原汉话说得流畅舒服。他压低了身段,降下俊俏的面容与汝南凑得很近。
「姑苏雨凉,姑娘介意与我共执一伞吗」
雨势大了些,淅淅沥沥,在凉风里倾斜轨迹,淋湿姑娘一片裙角。他瞧着温吞吞的姑娘悄然红了耳尖,正无措地又将头低下。
「多……多谢」
那苏想送她回家,却听说她从北边儿来认亲,口气止不住讶异:「姑娘从外地来的?从祁江上坐船?哪家没良心的赚这黑心钱?」
「咦?」汝南顿了脚步,疑惑地望向那苏,「难道祁江怎样了?」
「不是祁江,是姑苏城」那苏沉思顷刻,从衣襟后提出一块项链来:「这里已经不是从前的姑苏了」
汝南盯着他指上捻起的金质神像,不知为何,心跳极快。
那苏说,他八岁来的姑苏,如今十七年,再也未回去大漠。八翼光明神是他的信仰,他秉承着神的旨意来到中原。
他回忆故乡的时候,语气带着朦胧遥远的神往,好似神殿垂下的婆娑金纱,在光明与风中冥冥撩动。
「远远地瞧一眼故乡,也不可以吗?」汝南轻声问道。她想起阿娘,淡薄的江南女子躺在靠窗的摇椅上,厚重的绒毯衬得她更加病弱,那逐渐失焦的眼总是对着窗外寒江。
那苏说:「见了更是痛苦」
他望见姑娘过分美丽的眼睛,水光粼粼,胜过多少雪月。
「姑娘说的‘杨家’,姑苏城倒是有一桩。只是数年前就落难了,一众都供在祠堂里」那苏有些怜惜地看看她怀里的坛子,大抵猜到了其中是些什么,便又补充,「我领你去」
「落难?」汝南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无一幸免?」
那苏叹气,抬起纸伞露出一边天色。雨快停了,太阳却无有任何出没的意愿。汝南始觉失态,垂首敛目,称了声「抱歉」。
那苏轻笑着摇摇头,探手将姑娘落下的一缕青丝夹回耳后。她飞快地眨眨眼,而后撇开泛红的面颊。
「你看,从江畔走到现在,除了你我,一人也无」他扫过两边门窗紧闭的房屋,这样的静谧是死寂,恍如世界只抛下两人。
姑苏城的人们每逢落雨,便只躲在屋内不再出声,大好的江南盛景,此刻死气沉沉。残雨窸窸窣窣地落在青石板上,润进细缝里,新长几弯潮湿的青苔。苦涩的滋味沉淀下来,混合在更加古怪的气味里。
女儿家的绣花鞋有意无意地避开生长在石缝中的杂草青苔,些许雨丝融化在鞋面上,映进内里,凉了脚丫。
「是此地风俗吗?先生却不顾忌」
那苏眼色微暗,很快又明亮起来。「我是西域人,自然不顾忌」他却一刻不止地盯着汝南,捕捉着每个细微的表情。
好心的那苏将姑娘带来祠堂,忽地止步玄门之外。他的脸色昭示这厮正酝酿着什么心思,开口时又欲言又止。
汝南以为自己的请求拖延了他太久,歉意说:「多谢先生带路,劳烦先生了」接下来,她自己来就好。让阿娘与亲人们重聚,再上三炷香、磕三个响头。
那苏挠挠柔软的金发,看起来有些苦闷。在汝南疑惑的注视下,他解开项链挂上她的脖颈。姑娘肌肤似被烟雪浸泡,白皙细腻。他的指尖无心滑过,便触电似的缩回。
「姑苏不是从前的姑苏,早些离开吧」
汝南怔怔地望着他离去,不由地握住胸前的神像,神像上带着些许残温。一柄油纸伞正搁在她的身边,静悄悄的。
祠堂鲜有人来,蛛网从荒杂野草攀上青瓦檐角,笨重的玄门推开细小的缝,便簌簌落下许多粉尘来。汝南呛了几声,迟疑地打量一圈。
说不出的怪异。
她尽可能避开一花一木,进入正厅,烟尘已不知铺了几层,满眼灰蒙。露出木色的玄漆桌台从东连到西,两百零四座木牌乱无章法地陈列,有的已经磕坏,有的连题字都无。
汝南腾出手来,将仄歪横倒的牌一一扶起摆正,一面寻找着杨家众人的位置。估摸一刻半钟,姑娘心静下来,披了黑纶布的桌下忽然伸出只手来,瞬时抓红了她一截玉腕。
姑娘心惊肉跳,险些惊呼出声:是人是鬼?!
她从铁手中挣脱开来,向后摔去。这一摔也带出了藏在桌子底下的人,蓬头垢面、满身污浊,好似百年不曾洗浴过;举止疯癫、口中嗤笑,赫然是个病人。那乞丐一条腿坏了,大腿之下的裤筒空荡荡地飘风。
他张牙舞爪地围着汝南转圈,欢喜叫道:「文娘文娘,来抓我,来抓我」
汝南更加愕然。那「文娘」可是死去阿娘的闺名,这位先生是什么来历?
她阿爹断断续续提起,杨家官宦家族、书香门第,看重三从四德、天理纲常。亲密的闺字,哪里是普通人可唤得?这莫不是哪位幸存的舅舅,或者……
疯子见她不言不语,受了冷待,当下委屈起来,翻起一卷袖子嗷嗷直哭,豆大的泪珠子啪嗒啪嗒打碎在她的裙上。
他遂又拉住她的袖口,哭道:「文娘文娘,别不要我,我这就娶你回家」
汝南神光闪烁,认得他内袖的绣工。阿爹最爱的几件衣裳,都是这个针脚。阿爹发呆时,总是喃喃说:阿文啊,给三郎绣个竹叶吧……
阿爹等不来阿娘的竹叶璎珞,这份心意早给了他人。
汝南知他是谁,看这竹叶花纹,也知两人情分。这自有古怪,她认清他身后那些个木牌,胡乱写的正是杨家众人的名目。
一名轻易抛弃爱人的男子,为何要穿着爱人绣过的衣裳不肯脱换,为何要回到爱人的故土守着家族的神位,为何疯癫之后心心念念还是爱人的名字……
谁也不曾真正割舍谁,那为何不得不相互放弃?
汝南始觉胸口奇闷,似是身处黄梅雨季。
疯子盯着她胸口的物什,忽然惊恐地大叫起来:「你回来做什么!你也吃人吗!」
「先生,请冷静些」汝南按住他胡乱挥舞的手爪,这个动作毫无安抚的效果。疯子只更加惊惧癫狂,手脚并用地要离开她:「滚!滚!!」
汝南听出端倪,心石也沉进深渊里,落水的声音‘咚’得巨响,砸得人头昏眼花。
吃人,吃什么人?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