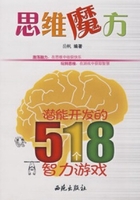那位在碧波沧海中遥望着星河夜幕的姑娘,叫做寒雨。
云彻头一回见到她的时候,海面上弥漫着浅淡的氤氲水汽。她美丽的衣绡像是与云烟连接在一起,在她梳理蜿过礁石、垂入水中的雪发时,飘散出水红雾气。
空气中涣散出清透的味道,不同于海风的鲜咸,却更似海的滋味。
月光柔和,他远远地观视着那位姑娘,却无比清晰的感知到她的情绪,凄哀、幽怨,也婉转。
他不知自己如何知晓她眼角精亮的鳞片是柔软的,他不曾见过她哭泣,却能肯定她落下的泪是纯净无比的珍珠。他知背对着她容颜是怎样清丽脱尘,而迷白的眼眸早已失去了视觉:
她是值得同情、让他心痛的姑娘。
他伫立在岸边,听着沧浪拍击礁石、打出千雪破碎的声音,脚下踩着绵软白细的沙子,浪花漫过他的鞋靴、再恋恋不舍地退去,仿佛是心上人不愿放开又不得不放开双手时,那股子酸楚的缱绻。
他们相隔甚远,可云彻以为,她距离自己很近。
「清岚……」
这是她对他的称呼,千回百转,万分哀苦。
他再次不以为然地纠正:「我不是清岚,我叫云彻。」
她沉默了许久,倔强而温柔地说:「你是清岚,你是……」
一粒珍珠落在礁石上,滚进海里。
※
妙雪圣女与幼莉圣使不见了,连多年追随她们的教众也不知她们的去向。
洛殊忧心忡忡地说:恐怕是去了布图多遗迹。
去哪里做什么——她的策师微笑着拂过鬓间的桃花,那盏泪痣盛起灼灼光华,而后和善地解释,或者说也是猜测:
「萨陀与多利亚冲突不过一日,天鹅坪便已在布图多看护。地理位置看来,不论冲突多大,都不会威胁到天鹅坪。听出疑点了吗?」
洛殊很快接过她的话:「正常的传播速度,天鹅坪绝不可能那么快收到信息并做出反应;而萨陀甚至戈林部落,为何针对平凡的多利亚——有什么在吸引他们采取动作?」
加明乐呵呵地挑好葡萄,嘎吱嘎吱地连皮带肉一起嚼。清甜的汁水从她的嘴角流下,这厮豪爽地擦擦袖子,笑嘻嘻地也加入讨论。
「应该是祭坛那枚‘鱼梁石’吧,从前游历大漠,师长对它也很有兴趣——只可惜撬不下来。洛殊,你可以再说的明白一点,比如天鹅坪不远千里去蹲破石头的原因是,它自己的那一块,在六年前失踪了。」
自己的不见了,就去抢别人的?这算什么道理。况且这石头是有什么能耐,连最繁华的天鹅坪都眼红?
温文抓抓参差不齐的短发,狐疑道:「知道得不少啊,汝南告诉你的?」
加明懒懒地躺在躺椅上,没正经地撅起蹄子蹬空气,沾了葡萄汁的手往果盘里摸索了一圈,挖出个梨来。
「算是吧,」她那亮晶晶的眼睛映着穹顶斑斓的壁画,静了会儿,又转过头问道:「你们就不好奇为什么师长对块石头感兴趣?」
端庄矜重的策师浅浅微笑,眉间没的快要生出桃花儿来。她随即讲述的,是一个有些浮夸的神话。
万年之前,诸神末日,天地双沉,山峰刺碎苍穹。创世神以身重分九洲,取九洲精野魂息凝练为九石,补残缺天际,止人间大灾。
天阙补全,遗下神石一座,神顾忌阴阳失衡,将神石投入玄海。适时蛟龙出海,击碎神石、一分为三,散落九洲各处。
加明抖完了腿,露出认真的表情:「故事不错,但蛟龙、玄海都与大漠相隔甚远——诶,去旅行我专业的,选我选我。」末了又忍不住自己破功大笑。
策师掩唇狭目,眼角含着神秘悠远的意味。大约是回应加明的玩笑,她耐心地对她说:「汝南圣女曾派遣加明圣女远行中原,若真要追究鱼梁石的缘故,行程里定然少不了玄海。她若不是知悉鱼梁石的大概,便是认定它无关紧要。」
加明张了张嘴,或许还想蹦出什么没营养的调笑,温文率先翻起白眼,将她的话堵回去。
「我听义姐提过,三十年前天鹅坪内乱除了长老会元老院发疯,还被一群苗疆人关注过。顿葛死后,拜翎主持长老会,而后也抓着蛛丝马迹找到他们,发生过不小的冲突。到了六年前,天鹅坪再次内乱,拜翎与那些苗疆人全部消失——也是同一年,沙疫爆发,汝南遇到了妙雪和失心疯的阿婆。」
他端着双臂靠在光明神的石基上,圣光洒下来时固然是为他镀上一层金韵,但更多时候,石像如果有意识,大概更像一脚把他踢开。加明肖想着光明神像突然抬脚的场景,盯着温文的眼神有些不自然。
温文被她看得浑身都疼,蹙眉闷声道:「干嘛,有问题吗?」妙雪在尊老爱幼方面可比你个兔崽子正常多了。
他想念起自己的药酒来,几年前中原时兴将红枣枸杞浸在烈酒里酿造,他捉摸着也埋了一坛下去。好不容易等了岁月累计,昨儿晚上刨土挖坑从圣医院角挖出来,正打开了没尝一口,谁知道哪里跑出个风风火火的臭丫头,撞飞了坛子白洒了心血。
温文脸色泛青,那都是心疼的。
加明火急火燎地跟他打招呼,被揪住后领之后提到了角落。
『对不住对不住,我错了——』
『道歉有用的话要检察团干嘛?等等,你这个方向……不是往生塔吧?』
温文那双眉头锁得越来越紧,直至加明不老实的腿晃得快要提到他的脸上,这才气冲冲地将它按下去。
他听加明夸张地叫道:「这问题可太大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天鹅坪跨过光明殿参与萨陀与多利亚的冲突诶!洛殊你知道六年前的行情,那就很明显了!有心人引诱萨陀与天鹅坪抢多利亚的‘鱼梁石’,而这有心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们口中的——苗疆人。顺道补一句,他们的目标保不定也是抢石头,不过是聪明一点知道渔翁得利。」
洛殊深思熟虑之后,颓然道:「我不知鱼梁石的作用,不知为何要抢夺鱼梁石,也不知妙雪与幼莉圣使为何孤身参与……」
加明斟酌了顷刻,发出思考的声音:「两人组队呢……不算‘孤身’吧?」
温文果不其然又翻了个天大的白眼,「谁知道她们在不在一起。更何况两个有病的凑一块儿,还不如孤身呢。」他可真不觉得幼莉能遭住那个臭丫头的疑问,说不定这会儿连刀都挖出来了。
加明捂住嘴,身体不由往后倾去,一副‘离我远些’的模样。
「哇塞温文医师你敢再大声点让她们听到吗?」
温文鄙夷地看着她:「你也有病啊。」
这边闹得鸡飞狗跳,另一边,洛殊规规矩矩地坐在椅上,双手交叠、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手背,微微颦蹙,浅色的睫羽垂落两片阴霾。
她细微地自言自语:「如果幼莉是为了拜翎,妙雪又是为了什么……」
策师颇有深意地出声道:「小姐会希望看到第二个‘洛殊’吗?」
洛殊猛然一颤,似乎方从噩梦中惊醒。她坚决道:「当然不会——我不想还有一个人,在失望与绝望的边际等待那么久!」
她眨眨眼睛,慢慢镇静下来,扬起娇小的面孔,带着若有似无的浅笑:「多谢你将我带离那个边际,暄和。如你一般的女子,应当活得很骄傲吧?」
策师怔了会儿,才又笑道:「哪有人能活得骄傲,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她扫了圈大殿,接着对洛殊说:「汝南圣女倒下,各部落皆有打算。圣教如要平定暗流,就不得不接近暗流啊。」
她的声音轻柔无害,在空旷的殿内更显得轻飘飘的抓不到实在。为数不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止住了各自的心思,不约而同看向她们。
洛殊附和着点点头,目光扫向靠在边角看书的青年,诚恳道:「云彻,劳烦你与温文医师一同去布图多遗迹,我担心妙雪与圣使遇上麻烦。」
青年翻书的手停顿下来,在反应几秒后立即合上书,规规矩矩地朝她鞠下躬。
温文懵了许久,待青年退下准备,才回过神来:「你们每个人都欺负我老实就对了!」
不敢不敢,毕竟您是拿酒坛子砸人脑袋的暴力医师——加明暗搓搓地评价。
‘未知’本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当云彻察觉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暗探时,他便这样认定。
两人默契无比地退到一株老树之后,背脊贴着树身,放轻了呼吸。四目交错刹那,各自从对方眼中看出迷惑来。
云彻探出半个脑袋,粗略的地扫了一眼暗哨的排布,低声说道:「不知道是哪方人,堵死了去遗迹的路。只在外围潜伏,暂时不会直面天鹅坪兵卫。避免打草惊蛇,我们绕道。」
温文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跟上云彻压低的身段往南边又走了不少路。待彻底远离原地,才神思恍惚地猜道:「戈林,萨陀,苗疆……你说是哪个?」
云彻问:「排除多利亚?」
温文摆摆手,掐着腰笃定道:「与萨陀的冲突中,多利亚处于弱势,要防范进攻,肯定死守防线,哪有闲工夫管宣称中立的天鹅坪?再者多利亚要看天鹅坪的兵卫,应该伏在前边的沙丘上,视野更好,何必跑来这里。」